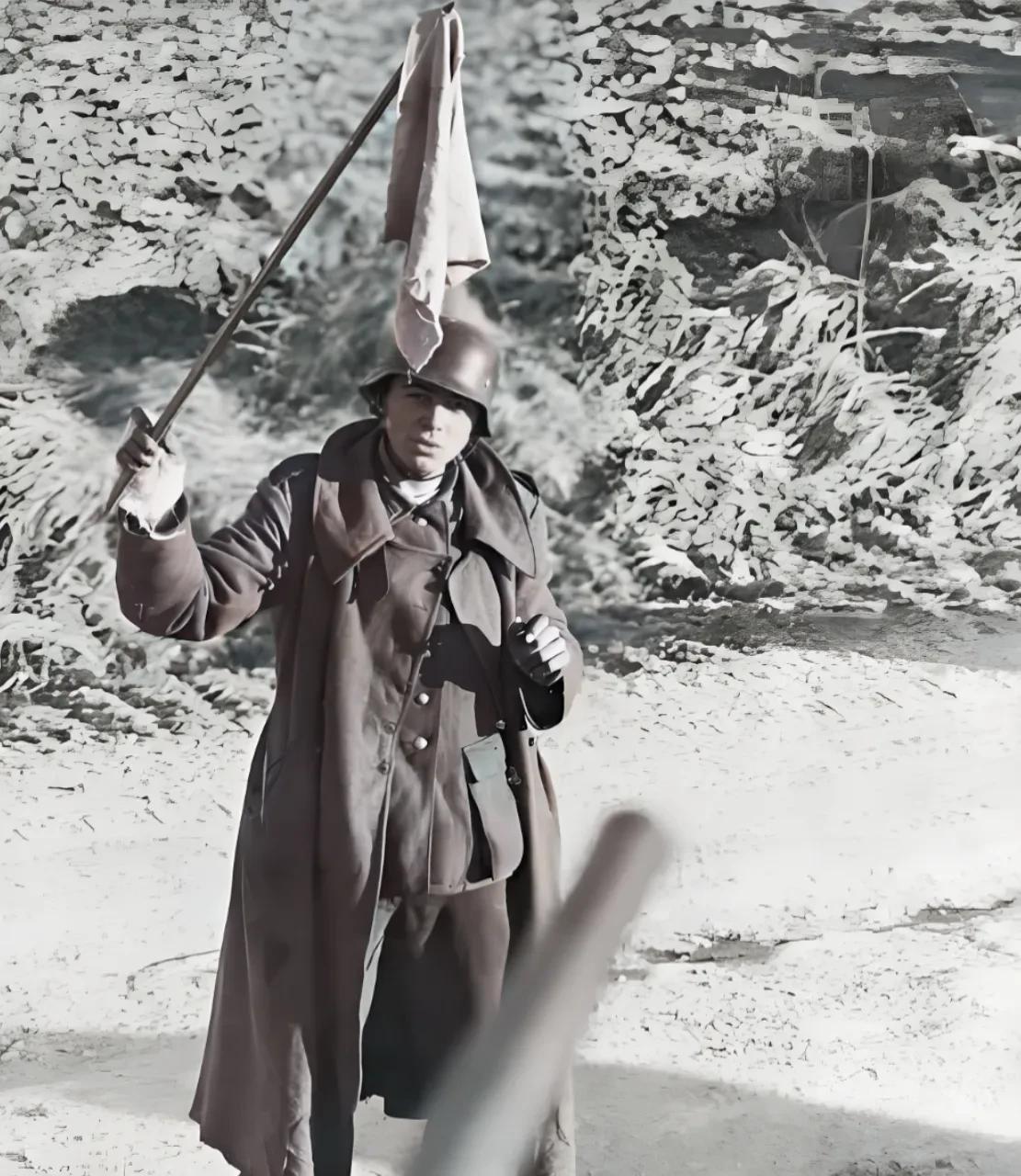1968年1月,四架美军战机闯进我国领空,上级下令击落敌机,但导弹营长陈辉亭敢抗命不打,谁知战后,军长不仅没追责,反倒登门道谢。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68年1月23日,在广西宁明,地空导弹阵地的雷达屏幕上,四个光点毫无征兆地跳了出来,目标直指北部湾,雷达操纵员李建国嗓音发紧:“营长!四个高速目标,高度8000,航向315度!” 而坐镇指挥所的,是二营营长陈辉亭,这位老兵出名,不只因为胸前挂着毛主席接见时给的纪念章,更是因为那个“用竹竿捅下U-2”的传奇。 那次,他就是靠着异乎寻常的冷静,硬是等来了最佳战机,可这一次,情况似乎更棘手。 只是空七军指挥部的命令来得又快又急:击落入侵敌机!整个阵地闻令而动,四枚萨姆-2导弹昂首待命,通电声嗡嗡作响,只等陈辉亭按下那个红色按钮。 然而,他迟迟没有动作,雷达兵李建国再次报告,语气里带着困惑:“回波稳定,四机编队,间距不到50米!” 这句话让指挥所里瞬间安静下来,谁都清楚,能飞出这种“肩并肩”的密集队形,要么是自家空军里配合默契的王牌,要么是不要命的疯子。 而美军的F-4“鬼怪”战机,出了名的狡猾,向来是分散渗透,怎么可能像仪仗队一样,四架挤在一起,直愣愣地往枪口上撞? 这太反常了,陈辉亭的眉头皱起,三天前,军长刘玉堤那句“北部湾的天空就靠你了”还在耳边,这份信任,让他不敢有丝毫的赌博成分,他抓起电话,直通空七军指挥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飞机有没有在活动?” 但电话那头几乎是吼过来的:“陈营长,雷达都判定是F-4了!你想抗命?” 抗命,这顶帽子太重了,但透过窗户,那四枚蓄势待发的导弹,仿佛随时会喷火而去,陈辉亭的手指悬在发射按钮上,一厘米的距离,隔着的就是生与死,他对自己人说了一句:“再等等。” 这一等,雷达光点从50公里逼近到30公里,指挥部的催战电话一个接一个,口气一次比一次严厉,一连催了七次:“开炮,别废话!” 这时陈辉亭的后背已经湿透,他忽然想起,早上有四架歼-6战斗机起飞,会不会是它们,他立刻又抓起另一部电话,打给空七军航修厂:“今天有没有歼-6试飞?” 当厂长在那头说:“有一架在北部湾试飞,不过已经落地了……” 在话没说完,陈辉亭心里“咯噔”一下,如果试飞的警报没解除,系统会不会把正在正常巡逻的歼-6也当成了敌机? 此时,目标已经冲入20公里,这是萨姆-2导弹的最佳射程,副营长王建军带着哭腔喊:“营长,再不开火,我们都要上军事法庭了!” 陈辉亭猛地回过头,盯着指挥所里一张张年轻而紧张的脸,沉声问了一句:“如果真是我们自己的飞机,这扳机,谁扣得下去?” 这一句话,问住了所有人,三个月前那次夜间演习误伤友军的惨剧,血的教训还历历在目。 新中国的空军家底薄,每一个飞行员都是用黄金堆出来的宝贝,打错了,毁掉的不只是几架飞机,更是几个家庭和国家的未来。 但一边是抗命的巨大风险,一边是保护战友的责任,陈辉亭下意识地,把手从发射钮上松开了。 在光点逼近到17公里,这已经是极限,再近,导弹就可能失去最佳拦截机会,就在陈辉亭准备下达最后指令的瞬间,那部红色的电话机再次尖叫起来,他扑过去一把抓起,听筒里传来空七军参谋长带着劫后余生的怒吼:“别打!是我们的歼-6!” 瞬间指挥所里一片死寂,随即是压抑不住的喘息声,陈辉亭紧盯着屏幕,只见那四个光点瞬间打开加力,喷出橘红色的尾焰,在天空中拉出四道优美的弧线,他这才感到,后背的冷汗已经冰凉。 这次乌龙的原因很简单:一架歼-6试飞降落后,雷达监控系统出了故障,没有解除警报,结果把后续巡逻的四架友机当成了入侵者,一套先进的自动化系统,差一点就导演了一场自相残杀的悲剧。 在几小时后,宁明机场,领头的歼-6飞行员李卫国摘下头盔,冲过来一把抱住陈辉亭,激动得说不出话:“老陈,多亏了你,不然我们四个今天就报销了!”巧的是,两人还是航校同学。 傍晚,空七军军长刘玉堤亲自赶到二营,握着陈辉亭的手久久不放,感慨道:“你这一‘等’,救了我们空军四架飞机,救了四个家庭啊!”这次事件,后来被写入战例教材,命名为“1·23生死17公里”。 但军令如山,但军人的天职不只是服从,更是基于战场的独立判断和对生命的敬畏,在那个生死关头,“抗命不打”看似是违反纪律,但它恰恰守护了纪律背后最核心的东西——保护自己的战友。 并且陈辉亭后来在回忆录《天网》中写道:“军人得听命令,但更得护住自己人,打仗的时候看不清情况,手里的家伙绝不能对着自己兄弟。” 这句话,后来被刻在了空军指挥学院的石碑上,这或许就是对那个终极问题的最好回答:战场上,死板的纪律有时通向灾难,而清醒的头脑和敢于担当的“抗命”,才是对战友和国家最深刻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