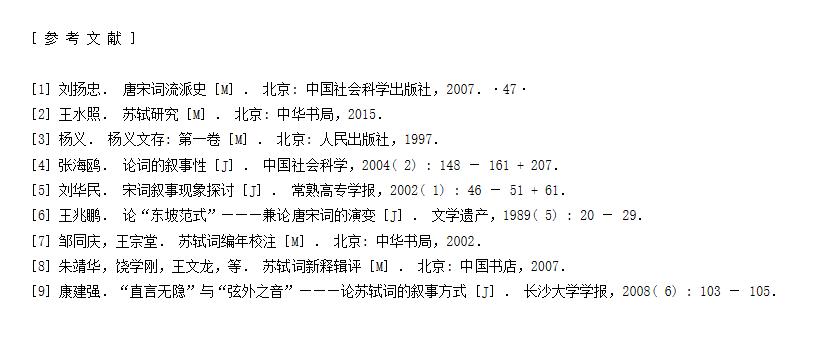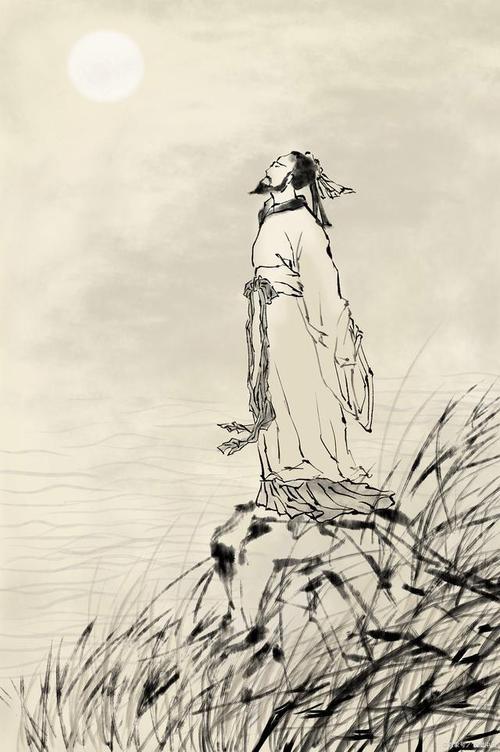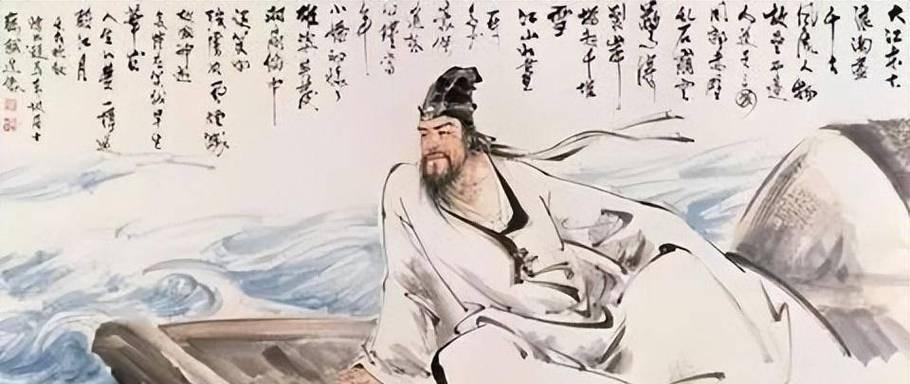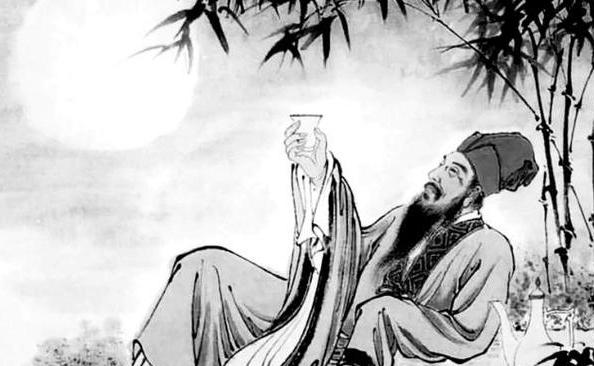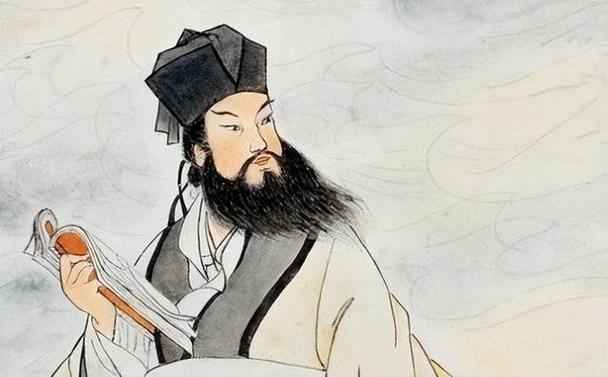苏轼是怎样借词抒情言志的?从他的诗词中,探寻其创作灵感 在借词抒情言志的创作中,东坡词在形式与内容方面的叙事介入均有迥异于前人之处。 正文文本之外的词序与正文的虚实相生、文本之内的用典隐喻叙事,以及借意境塑造而实现的诗意叙事等创作手段,共同构成了东坡词独特的叙事艺术,在开启宋词叙事新形式的同时,对“诗化之词”的叙事发展具有范式意义。 词中用序,最早始于北宋张先,及至苏轼发扬光大。词序的主要功能是叙事,当词人觉得词调或词题之叙事尚不尽意时,便将词题延展为词序,以交代、说明有关这首词的一些本事或写作缘起、背景、体例、方法等等。 苏轼的很多词作都有词序,他“以诗为词”的一个重要美学特征,便是使词如诗歌一般,可以创造出雄浑高健的抒情境界,这种境界的塑造如果能在正文之前有所铺垫,正文情感的抒发便能更为顺畅,有所依托。 词序与正文在虚实相生间完成对事件的勾勒,词序既能对正文所涉事件起到补充说明的效果,从自身文体特征来看,亦有提前向读者暗示词作情感指向,为抒情造势的作用。 词体因受文本长度、抒情需要等诸多限制,想要完整展现叙事要素,必然会削弱词境的创造与词心的抒写。正因如此,词中正文叙事与传统叙事类文体的叙事不同,而词序的使用很好地弥补了词体在叙事方面的这一局限。 纵观东坡词词序,很多词序带有明显的散文特质。由于词序长度灵活,不受押韵限制,故而在对正文文本中不易牵扯到的叙事要素进行补充说明时,便显得更加灵活自如。词序的使用是苏轼“以诗为词”创作理念的一次伟大实践。 宋代以前,唐代诗歌中的序文已经发展的相当完备,序文与正文的韵散结合使抒情与叙事呈现出既融合又分离的趋势。其融合在于序文的插入增加了诗歌的抒情强度,为诗人表情达意做下充足铺垫,其分离在于很多诗歌的序文更像是一篇独立的散文,承担独立叙事功能。 序文与诗歌互为观照的写作方式被苏轼借鉴到词作中,形成了东坡词借序文叙事而辅助正文抒情的艺术风貌,这也是宋词叙事艺术的一大突破。 东坡词词序中部分内容带有客观叙事的特点,词人在词序中或是交代创作缘由,或是介绍词作的时间、地点及有关人物,不带任何情感色彩,但却与正文虚实相生,互为照应。 词序只是单纯介绍事件发生背景,并未掺杂任何情感色彩,是典型的实写。而正文中,景中有事,一虚一实,意为还未准备好乐曲迎接太守的到来,而两位县令的游船已经飘在水上,与词序“太守未来,两县令先在”呼应,是对词序的进一步深化。 但与词序相比,同述一事,正文中两句则带有鲜明的游戏、调侃意味,比词序的单纯叙述情感色彩更加浓郁。“双凫”为借汉代王乔为县令时化作野鸭定期飞到京都朝见天子之典,在此比喻两位县令,便使词人与同僚相得甚欢的场面跃然纸上。 此词中,词序既是正文叙事的补充、铺垫,同时又与正文相互映照,让这一叙事片段画面感极强,为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也使此番游赏别具一格。 纵观东坡词词序,大多起到交代作品创作缘起以及词作主题、内容的作用,词序强烈的叙事意味对读者深入了解词作起到重要的指引、提示作用。 东坡词序有长有短,内容或复杂或简单,这种散文式的写作方式与词之正文相互配合。 词序的使用既没有冲淡词体正文的抒情性,反而进一步开拓了正文的抒情空间,对正文的情感指向有重要的暗示作用。 东坡词词序中有很多看似不带任何情感色彩,单纯记叙说明创作缘起的序文,实际却对正文创作起到重要补充,并暗示着词作的情感指向。 如名作《定风波》此段词序虽然简短,但叙事容量却十分充足,不仅包含时间、地点、人物等基本叙事要素,且因雨而导致同行狼狈,唯有词人自己不以为意,最后天气转晴这一创作缘起,词人也用简单的线性结构方式加以介绍。 词序的意义不仅在于补充说明正文叙事内容、交代创作缘起,同时也向读者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有一例外情况,那就是词人自己“独不觉”,这种面对意外状况仍能不以为意的心理状态恰好起到暗示了正文“乐观旷达心态的效果。 再如《虞美人》,词序以叙事口吻,简单交代创作缘起。序中有一值得关注的现象———词人指出,本词作于陈述古任期将满,即将离任之际宴请友人的宴会之上。 有这样一个背景作铺垫,自然会引出参加宴会之人的“别情”,而词作正文,更是直接表现苏轼对与友人即将分别的惋惜与惆怅。词序的叙事性质与正文抒情互为照应,也就是说词序叙事暗含正文情感主题,并为抒情张本。 总结: 词序与正文韵散结合、虚实相生的创作手段最大限度地扩展了词体的叙事张力。 若无词序存在,宋词中很多作品叙事特征并不明显,而词序与词作正文的结合有效地增强了正文所涉本事,对读者更好理解作品本身的思想内涵起到一定辅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