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太太蹲在鱼贩子水池前望着鱼,蹲了一下午。 鱼贩子好奇地问:“你看了一下午了,要买还是不要买? ”
老太太说:“买。 ”
鱼贩子说:“那你为啥光是看呢? ”
老太太指了指旁边的牌子说:“活鱼6块一斤,死鱼2块一斤。 ” 老太太又指了指鱼说:“我在等你这鱼断气。
这就是著名的“等鱼死”现象。它也是某种生存策略的隐喻:当大环境不好时,企业或个人往往会选择"苟活",同时等待其他竞争对手因为资金链断裂、经营不善等原因先出局,这样自己就可以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获得更多的利益。“
而其实,“等鱼死”的策略不仅出现在商战中,也出现在权力的竞技场上。苏联的权力竞争与官员晋升就充满了“等鱼死”的意味。为了让竞争者出局,苏联的官员们练就了一身“等鱼死”的本领,熬资历、熬年限,是其中最直观的体现。在这场充满算计的“持久战”中,有人靠“熬” 字诀一点点耗掉竞争对手,有人则揣着耐心 “等鱼死”,等权力格局里的“大鱼” 退场,然后自己顺势上位。令人惊诧的是,这套生存策略在苏联体制下普遍而成功:“你不需要比别人强,你只需要活得比别人久”。

“熬出来”的总书记:体制晋升的显性“潜规则”
1985年3月10日,73岁的契尔年科停止了呼吸,此时距他上任苏共总书记才13个月。这位苏联历史上最年迈虚弱的总书记,有缘最高权力,与其资历关联甚深。而契尔年科的职业生涯,是苏联官员“熬资历”晋升模式的极致体现。
契尔年科不是革命元老,也不是战时英雄,更与理论旗手身份无关。斯大林的铁腕、赫鲁晓夫的胆识,甚至勃列日涅夫的地方背景,契尔年科统统没有。但与同时代的竞争者相比,契尔年科却有非同一般的“资历”:他是“最老的候补委员”,且“服务时间最长”。
1911年,契尔年科出生于西伯利亚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做过农技员、地方报纸编辑。1930年代加入联共(布)后,他始终在体制的中下层缓慢爬行。二战期间,契尔年科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负责宣传工作,既未上前线,也未参与重大决策。战后,他兼任摩尔达维亚宣传鼓动部的工作。直到这个时候,契尔年科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重要政策文件的署名栏,更不用说在工业、军事或外交领域建立过突出功绩。
然而,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契尔年科的职务却像钟表一样精准地逐年上升。1956年,契尔年科调往莫斯科党中央工作,这是契尔年科人生中的重要一步。在这里,契尔年科远离公众视线,不需承担具体政策后果,只需按时出席例会、起草文件、记录决议。可以说,这是一个“熬资历”的理想位置。也是在这里,契尔年科一待就是二十年,期间职位虽不断上升,但他的工作内容仍然极少被公开。有档案显示,契尔年科经手的文件从不越界,从不提出独立意见,却总能“准确领会领导意图”。
这种“不越界”的风格,正是苏式体制最被欣赏的品质。1964 年,赫鲁晓夫被赶下台,权力重新洗牌。而契尔年科因为“资历够老、没敌人”,反倒受到提拔(总务部部长)。当时和契尔年科竞争这个职位的,还有波诺马廖夫。而波诺马廖夫不仅懂外语,更去过多国考察,能力远在契尔年科之上。不过,波诺马廖夫却曾公开支持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被勃列日涅夫视为 “不稳定因素”。而契尔年科抓住这一点,在勃列日涅夫面前从不提“改革” 二字,只强调“维护党的团结”。结果,契尔年科顺利上位。
1965年,勃列日涅夫汲取赫鲁晓夫的教训,推行“干部稳定化”政策,明确反对频繁调动和破格提拔:“我们需要的是可靠的干部,而不是‘天才’。天才容易出问题。”于是,在这样政策下,地方党委书记平均任职时间从4年延长到12年。
契尔年科作为“可靠的干部”,于1971年进入苏共中央书记处。他从不参与派系斗争,也不在公开场合表达立场。他的工作哲学极为简单:上级说什么,他就记什么;上级批什么,他就办什么。曾经有人形容契尔年科“就像一台精密的复印机,从不走样”。
1978年,67岁的契尔年科被正式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此时他已身体虚弱,常年吸烟让肺功能严重受损。但没人质疑契尔年科的资格:39年党龄,经历了五任总书记,参加过21次党代会,是党内“活化石”级的人物。
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去世,接班问题浮现。时任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申、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等都是更年轻、更有能力的候选人。但最终,政治局投票选择了契尔年科。原因很简单:他是“最老的候补委员”,且“服务时间最长”。这让葛罗米柯不无牢骚式地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不是在选最强的人,而是在确认谁该轮到了。”
葛罗米柯的牢骚抱怨不无道理,但契尔年科的地位却也是“合法”存在。在契尔年科身后,是一整套支撑这种晋升逻辑的机制,而“熬资历”无疑是其中最为显性的“潜规则”。契尔年科“等到了鱼死”。

“熬出来”的地方干部:苏联体制的平庸者依赖
苏联的官员晋升,党龄与职务年限具有刚性权重,是量化考核的重要指标。如,地方干部晋升到州级,通常需至少15年党龄与10年管理经验。而进入中央,往往需25年以上资历。至于能力评估,则可以“政治可靠”“群众关系好”等套话来代替,并没有人真正细究。与此同时,在同一梯队中,谁先谁后,往往按进入名单的时间排序。
于是,在缺乏公开竞争和问责机制的体制下,上级提拔下属,首要考虑的不是“能力”,而是“安全不惹事”。而能“熬资历”的老干部,其政治立场固化,人际关系稳定,是安全提拔的最优选择。相反,能力强但资历浅的人,被视为“不确定因素”。
这种“资历”上位规则并非明文规定,却在实践中被严格执行。地方干部对此心知肚明。一位曾在摩尔多瓦共产党组织部工作过的退休官员回忆:“我们每年年底都要填一张‘干部成长表’,列明大家的入党几年、任副职几年、正职几年、受过几次表彰。升迁不是看你干了什么,而是看‘时间到了没有’”。
库纳耶夫是“熬资历”的典范。他于1912年生,1936 年毕业后进入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工矿企业工作,入党后逐步晋升为总工程师、矿长和矿务局局长。1942 年,年仅 30 岁的库纳耶夫当上了哈萨克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在这个岗位上他一干就是十年。1952 年,库纳耶夫转任哈萨克共和国科学院院长,在此期间他积累了学术领域的威望。1955 年,库纳耶夫升任哈萨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64 年 12 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库纳耶夫任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此后他主政哈萨克斯坦长达二十年,直到1986年被戈尔巴乔夫撤换。
在库纳耶夫的治下,阿拉木图工业结构老化,农业依赖国家补贴,民族矛盾暗流涌动。但库纳耶夫却深谙体制规则:每年准时赴莫斯科参加党代会,从不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勃列日涅夫极为恭顺,甚至在公开讲话中称其为“我们时代的列宁”。库纳耶夫还擅长经营关系。每逢政治局委员生日,必派人送特产;而对中央干部巡视团,接待规格从不低于“国宾级”。
正因如此,尽管他年过七旬、行动迟缓,却始终稳坐第一把交椅。1984年,苏共曾考虑调他回莫斯科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副职),但他以“健康尚可,愿继续为边疆建设服务”为由婉拒,实则是不愿降级。之后,库纳耶夫在地方一把手位置上“熬”到了最后一刻。
而除了党政机关外,在苏联的国营企业、科研院所中,“熬资历”同样是晋升的主轴。一位莫斯科机械厂的老工人曾回忆:“我们厂长换了五任,每一任都是从副职‘熬’上来的。谁最有本事?谁最能喝酒、最会写汇报、最听党委书记的话,谁就升得快”。苏联著名的物理学家卡皮察曾抱怨:“我提名一位35岁的青年学者当研究所所长,上级回复说,‘他连副所长都没当过,怎么直接升正职?’可问题是,副所长位置一直被一个68岁的老同志占着,他连最新期刊都不看”。
在1980年代的苏联,类似的“熬资历”式干部遍布各州。他们未必腐败,也未必懒惰,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规避风险、服从程序、重视关系、轻视创新。他们不推动改革,因为改革意味着变动;他们不提拔新人,因为新人可能威胁自己的位置。

当“熬死竞争者” 成生存法则
如今看来,“熬资历”“等鱼死”,这种 “熬死竞争者” 的晋升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在高压政治环境下衍生出的生存策略。而这种体制的根源,深植于苏联的政治结构。苏联从列宁时期开始,就没有为领导人更替留下清晰的规则,导致每次权力交接时,都没有明确的依据来确定接班人选。
一方面,“干部名册制” 让官员们只能 “熬资历”。“干部名册制”,其实就是“上级圈定名单,下级排队等待”。比如一个官员要想进政治局,必须先在地方党委任职 5 年以上,再进中央部门当副手 3 年,还要得到至少两位政治局委员的推荐。这种制度下,“时间” 成了硬标杆。哪怕你能力再强,只要资历不够,就只能等着。而那些能力一般但资历够老的人,反而能 “熬” 走年轻的竞争对手。
另一方面,对“政治忠诚”的强调,让官员们往往“熬”待时机。于是,“会不会做事” 不重要,“会不会站队” 才重要。安德罗波夫如果不是靠“帮勃列日涅夫维稳” 赢得信任,根本不可能从克格勃主席升任总书记;契尔年科如果不是靠“对勃列日涅夫绝对服从”,也不可能熬到政治局委员。相反,那些有能力但 “不会站队” 的官员,比如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派官员,大多被 “熬” 出了权力圈。
毫无疑问,这样的机制虽然保障了短期稳定,但却也牺牲了长期活力。一位曾在苏联外贸部工作的官员回忆:“我们讨论计算机管理系统时,一位副部长说,‘列宁时代没有电脑,不也把国家建设好了?’这种思维,正是长期‘熬资历’培养出的保守主义。”
而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曾试图打破这一局面,推行“干部更新”,但阻力巨大。1987年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阿巴尔金被戈尔巴乔夫任命为经济改革顾问,却遭到政治局利加乔夫等多数成员以“资历不足”为由抵制,导致阿巴尔金无法参与核心决策,建议常被搁置。
这种“熬资历”文化,也最终导致整个官僚体系陷入“逆向淘汰”。有能力者因急于表现而被视为“不安分”,被边缘化;平庸者因循规蹈矩而稳步上升。不过,真正危险的,却是那种“无功无过”的普遍状态。一位在苏联国家计委工作的经济学家曾写道:“我们开会时,最怕有人提新方案。因为一旦试行失败,提方案的人倒霉;但若成功,功劳归上级。久而久之,大家只做两件事:抄文件,等退休”。

而“等鱼死”“熬资历”其实也最终成为苏联体制的慢性毒药。当干部的晋升之路极少由能力或业绩决定,那么大家就开启一场漫长、沉默、按部就班的“排队”。在漫长的排队中,只有把对手一个个熬走,才能轮到自己。这种静默的淘汰术,是体制默许的生存策略,也是比阴谋更有效、比腐败更普遍的上升路径。它保障了表面稳定,只是却扼杀了新陈代谢。当整个官僚体系都按年头排队时,创新被视作冒进,批评被视作不忠,变革被视作风险。于是,体制也终于走向了自己的僵化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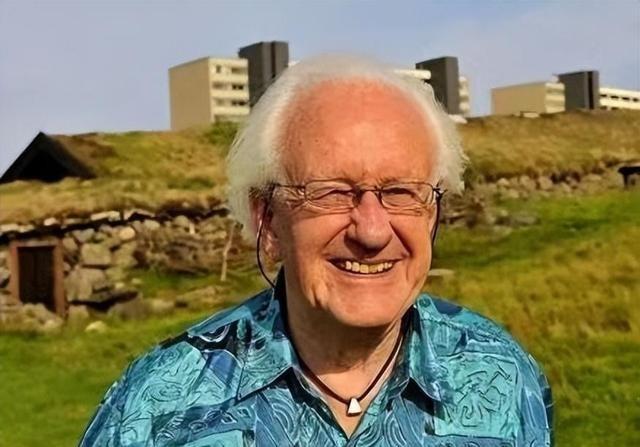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