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北京的初冬寒意渐浓。北洋政府在首都举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阅兵仪式——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首次由中央政府组织的正式阅兵。这场阅兵,不仅是一次军事展示,更像是一场在派系纷争与民族情绪夹缝中艰难推进的国家仪式表演。它试图用整齐的队列、轰鸣的炮车和激昂的口号,掩盖一个四分五裂的现实。
这次阅兵无疑短暂点燃了民族情绪。但却无法解决一个基本问题:中国有跻身“列强”的野心,却无实力争取权益的现实。
这场阅兵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究竟需要怎样的仪式,才能真正凝聚其人民?是枪炮的轰鸣,还是制度的坚实?是外在的威仪,还是内在的尊严?

风雨飘摇中的“胜利”时刻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胜利告终。中国作为协约国成员之一,于1917年8月14日由北洋政府对德奥宣战,虽未派兵赴欧,但派遣了约14万华工赴欧洲战场从事后勤、工事修建等任务。战争结束,中国被列为“战胜国”之一,举国上下一度沉浸在“扬眉吐气”的喜悦之中。北京太和殿广场连夜竖起“公理战胜强权”的巨幅木质标语,作为战败国象征的克林德碑被人用绳索拉倒,碑体碎石尚未清理完毕,工程局已开始在原址搭建四柱三间的“公理战胜”汉白玉牌坊。让人诧异的是,甚至有前清遗老在茶楼即兴创作《战胜赋》。
为彰显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地位及提升国际形象,段祺瑞政府在英法等国敦促下,紧急调集部队,制定了阅兵流程。然而,尽管仓促,这场阅兵式却具有复杂的政治考量。
彼时,巴黎和会尚未召开,列强对中国的轻视早已显露无遗。日本借《二十一条》扩大在华势力,山东权益问题悬而未决。而国内军阀割据,皖系、直系、奉系明争暗斗。南方更有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南北对峙加剧。
在此背景下,段祺瑞政府亟需一场“胜利庆典”,以凝聚民心、巩固权威、彰显“中央政府”的合法性。阅兵,便成为这一政治意图的具象化表达。

仓促中的宏大构想
段祺瑞授意陆军部着手筹备阅兵后,仪式原定于11月11日(停战日)举行,后因天气与准备不足推迟至11月16日。地点定于天安门前,自中华门至端门,长约一公里的御道成为阅兵主轴。
当时,实际参与部队包括皖系精锐徐树铮指挥的西北边防军,这支装备德式武器的部队被视为段祺瑞的嫡系力量,其受阅方阵特意展示新式机枪等先进装备。而直系代表曹锟第三师则仅携带老式“汉阳造”步枪参阅,士兵制服也明显陈旧。当然,参与阅兵的还有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巡洋舰海军“海容”舰编队,其水兵方阵的整齐度获得外国观察员称赞。此外,英属印度也派出了300人的锡克族部队,其鲜明的民族服饰成为阅兵式独特风景。
筹备过程中,经费问题一度成为大难题。财政部拨款20万元,实到账不足10万。军需官不得不向外国银行借贷,甚至动用军饷预支。服装、器械临时调配,部分士兵仍着旧式号衣,靴子破旧,引发了舆论讥讽。《申报》为此刊文:“观其军容,似胜于清末,实则外强中干”。
同时,派系矛盾也是非常突出的问题。段祺瑞坚持由皖系部队担任主力,不仅调集最精良装备,还安排西北军占据检阅台正前方位置。直系将领则以“军需不足”为由消极应对。最终参阅的直系部队不仅武器落后,受训程度也明显不足,与皖系部队形成鲜明对比。

盛装下的裂痕
1918年11月16日,阅兵式正式开始,天安门聚集了数万民众。东西三座门悬挂“庆祝欧战胜利”“弘扬国威”等横幅。各国使节、外交官、记者云集观礼台,日本公使林权助、美国公使芮恩施、英国公使朱尔典等均到场。
总统徐世昌乘马车抵达后,段祺瑞率内阁成员迎候。徐世昌登上午门城楼,宣读《告将士书》,称“我中华以弱胜强,跻身列强之林,实赖将士用命,国民同心”。随后,阅兵正式开始。
参阅的步兵第9师士兵均佩戴铜制“胜利”徽章,该徽章由北京造币厂特别铸造,直径2.1厘米,含纯铜量达92%。海军陆战队方阵采用德式“鹅步”行进,每分钟116步,步幅75厘米,靴跟落地声震彻广场。
当骑兵第1师通过时,一匹战马突然受惊,士兵张德贵立即用左臂勒马同时右手鸣枪示警,未影响后续方阵行进。
然而,情绪的高潮出现在“海参崴护侨部队”方阵通过时。这支由陆军第7师抽调组成的部队,身着厚呢军大衣,佩戴“远东”臂章,他们高唱《国耻歌》:“山河破碎,国将不国,同胞流离,谁为拯救?”。一名《晨报》记者记述:“当护侨官兵列队而过,市民纷纷脱帽致敬。”这一幕被日本记者记录,登载于《东京朝日新闻》,题为《中国军民之觉醒》。
尽管表面庄严,阅兵过程中派系矛盾却是暗流汹涌。
直系将领冯国璋虽已卸任总统,但其影响力仍在。直系部队仅象征性派出一个连,且故意迟到,导致阅兵序列出现断档。段祺瑞怒斥“不识大体”,直系回应称“军务繁忙,未能克期”。而奉系张作霖虽派兵参加,但所部骑兵故意在行进中加速,冲乱步兵队列,被段祺瑞视为“挑衅”。事后,奉系辩称“马惊失控”,实则不满段祺瑞独揽外交与军事决策权。
更严重的是,阅兵指挥权之争。段祺瑞欲由其亲信、陆军总长段芝贵指挥,但徐世昌坚持由总统名义统辖。最终妥协为“总统检阅,总理监军”,但段芝贵在台上频频越权发令,引发徐世昌幕僚不满。

民族主义的短暂高潮
此次阅兵特别突出“海参崴护侨部队”,实为北洋政府一次精心策划的外交宣示。
1918年春,俄国十月革命后,远东陷入混乱,白军与红军交战,大量华侨生命财产受威胁。北洋政府在英美支持下,北洋政府决定出兵西伯利亚,保护侨民。8月,陆军第7师登陆海参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海外用兵行动。其后,北洋政府通过海陆双通道累计运输侨民20余万人,其中海军护航招商局商船运输7.2万人,陆军武装押运专列运输3.1万人。
北洋政府的举动在国内引发强烈反响。政府宣传称“中国首次以战胜国身份派兵海外,彰显国威”。阅兵中特设护侨部队方阵,正是为了强化这一叙事。
也因此,阅兵当天,北京城陷入一种混合着自豪与悲情的复杂情绪。市民普遍将阅兵视为“洗刷国耻”的象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战屡败,甲午之耻、庚子之辱历历在目。如今以“战胜国”身份举行阅兵,许多人视之为“百年未有之荣光”。
阅兵通过电报、报纸迅速传播全国。上海、天津、汉口等地举行庆祝游行。上海《申报》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报纸,以头版显著位置刊发北洋政府阅兵系列照片。不过,英国《泰晤士报》却认为:“中国试图以仪式重建权威,但其内部裂痕显而易见”。
北洋政府借此短暂提升了威望。段祺瑞声望回升,安福系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然而,这种提升极为脆弱。1919年,当巴黎和会拒绝中国诉求的消息传回国内,段祺瑞政府声望一落千丈,民众此前通过《申报》等媒体渲染的阅兵盛况所积累的“强国期待”骤然崩塌。
而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曾专题报道的徐树铮边防军,这支配备德式装备、接受过外籍教官训练的“模范部队”,在1920年7月爆发的直皖战争中竟不堪一击,短短数日便全线崩溃。其溃败速度之快,连日本军事观察员都在报告中惊叹“与阅兵时的精锐形象判若两军”。

虽然如此,但从某个侧面来看,1918年阅兵仍为中国近代国家仪式的一次重要尝试。它首次将“国家”概念通过视觉化、仪式化的方式呈现给民众,开启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某种雏形。当然,其内在的虚弱,如军事不统一、财政拮据、外交依附、派系倾轧,也暴露无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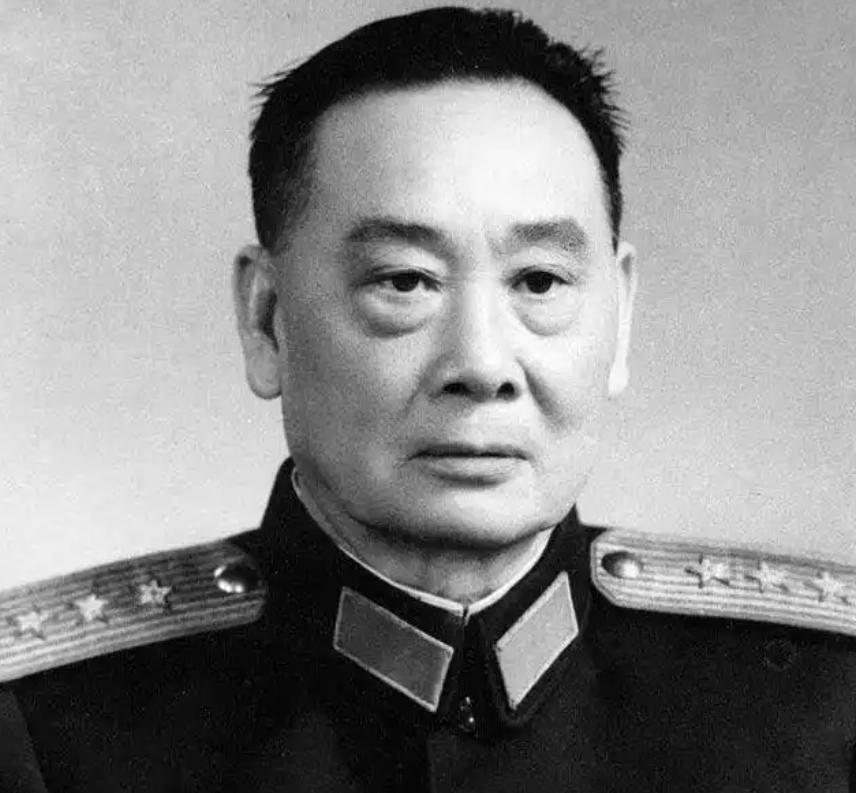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