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妾除了满足丈夫的生理需求和生孩子以外,还有另一个变态的作用,是后来有人无意间听长辈说漏嘴才知道的,说那时候小妾有时候是可以被“送出去”的,怎么说呢,像是一种交换。 大伙儿都知道苏轼吧,苏东坡,豪放派大词人,“大江东去浪淘尽”,多有气魄。可就是这么一位文化大神,干过一件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事。那年他被贬官,日子过得紧巴巴,在给朋友的信里,他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说自己把一个叫春娘的侍妾送人了,换了什么呢?换了一匹马,好继续赶路。 看到这儿你可能说了,苏轼怎么能这样?其实,这在当时的上流社会,真不算什么稀罕事。别说苏轼,写“在天愿作比翼鸟”的白居易,对小妾的态度也差不多。他家里养着很多年轻貌美的妾,还给她们起了个名叫“樊素”和“小蛮”。听着挺浪漫,可他自己诗里写:“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啥意思?就是养了十年,嫌人家老了丑了,就换一批新的。他还写过,“买妾三年,未得一子,遣之。”买了三年没生儿子,就打发走了。 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小妾在古代,到底算个啥? 她肯定不是妻子。正妻,叫“娶”,讲究“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有“三书六礼”,是八抬大轿从正门抬进来的,是家族的女主人。而妾呢,叫“纳”,就是收进来的意思。多数是从侧门悄悄进府,没有复杂的仪式,有时甚至就是一张买卖契约。 她们的出身,五花八门。有的是正妻带来的陪嫁丫鬟,叫“媵妾”;有的是家里穷,被父母卖掉换钱的可怜女孩,像《红楼梦》里的香菱;还有的,是战利品,或者是上级、朋友之间送来送去的“礼物”。 对,你没看错,小妾是一种流通的“社交货币”。 这才是她们那个“变态”作用的核心。当一个男人需要巴结上司、疏通关系,或者跟朋友搞好关系时,送金银珠宝显得俗气,送一个善解人意、年轻貌美的妾室,就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雅贿”。对方收下了,既满足了虚荣心,也欠了你一份人情。 更夸张的是,妾还能用来“交换”。除了苏轼换马,唐代的曹彰也干过用美妾换宝马的“壮举”。在他们眼里,这跟等价交换没啥两样。南唐有个高官叫孙晟,冬天嫌冷,不出门,干了件什么事呢?他让一群小妾脱了衣服,手拉手围成一圈,给他挡风,美其名曰“肉屏风”。 你看,在这些人眼里,妾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她们是工具,是财产,是摆设,唯独不是需要被尊重的伴侣。她们存在的最大价值,一是给家族开枝散叶,也就是生孩子,特别是生儿子。二就是成为男主人彰显财力和地位的附属品,以及在必要时,可以被当成“资源”处置掉。 她们在家里过得怎么样?一句话:在夹缝中求生存。 首先,她们得绝对服从正妻。正妻是后院的“大老板”,对所有妾室有生杀予夺的大权。电视剧里演的妾室跟正妻斗得你死我活,那都是极少数,而且多半下场凄惨。大部分情况下,妾见了正妻,得毕恭毕敬地站着回话,正妻坐着她绝不能坐。她生的孩子,法律意义上的母亲是正妻,孩子得管正妻叫“妈”,管自己亲妈叫“姨娘”。《红楼梦》里的探春,那么有才干有心气的一个姑娘,就因为是赵姨娘生的庶女,一辈子都活在这个身份的阴影里。 其次,她们的人生几乎没有任何保障。丈夫高兴了,多看你两眼,赏你点东西。不高兴了,随时可以把你转送给别人,或者卖掉。你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因为你的身契,也就是“劳动合同”,是签的卖身契,你的人身自由早就没了。 当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说所有小妾都过着地狱般的生活。也有极少数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手腕,在复杂的家庭关系里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甚至在正妻去世后被扶正的。但那样的概率,比我们今天中彩票头奖还低。绝大多数的她们,就像水里的浮萍,风一吹,就不知道飘到哪儿去了。 这种畸形的制度,直到近代才慢慢开始瓦解。随着西方“一夫一妻”思想的传入,以及后来法律的明文规定,纳妾才被正式废除。1950年我们国家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就彻底从法律上终结了这种延续几千年的不平等关系。 但制度的废除,不代表观念的瞬间扭转。直到现在,一些人的思想里还残留着那种物化女性的渣滓。 说到底,小妾制度,不是某一个男人的坏,而是那个时代整个社会结构的必然产物。在一个以男性为绝对中心、以家族传承为最高目标的社会里,女性,特别是底层女性的价值,就被压缩到了生育和附属这两点上。她们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





![乾隆真是职业皇帝名不虚传[吃瓜]](http://image.uczzd.cn/5141156089266685545.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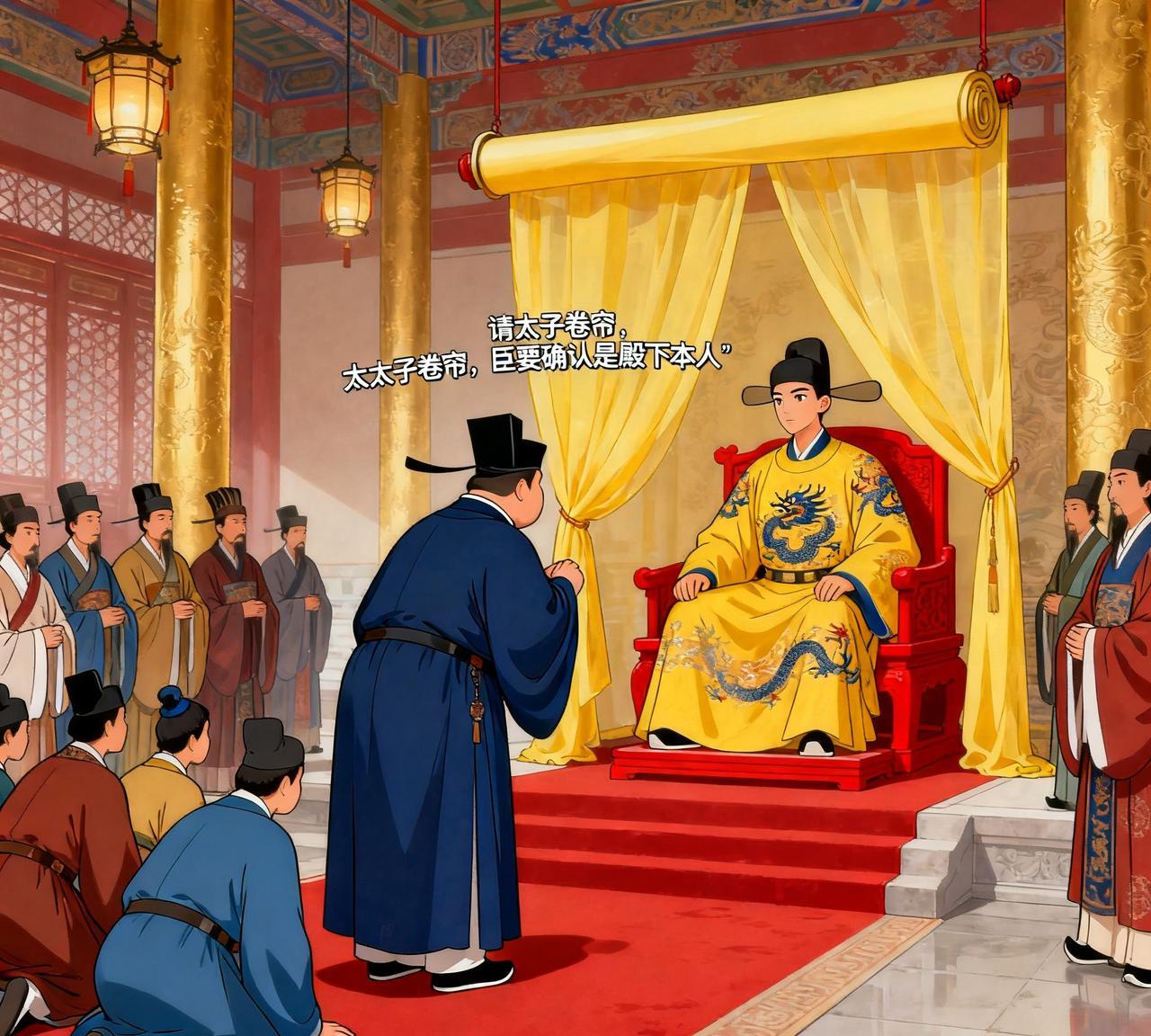

![最近爆火的乾隆和叶二帖,别说还挺合理的!![吃瓜][吃瓜]](http://image.uczzd.cn/1233988244968954052.jpg?id=0)

用户89xxx06
这年月想当妾的人多了
用户47xxx39
还是古代男人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