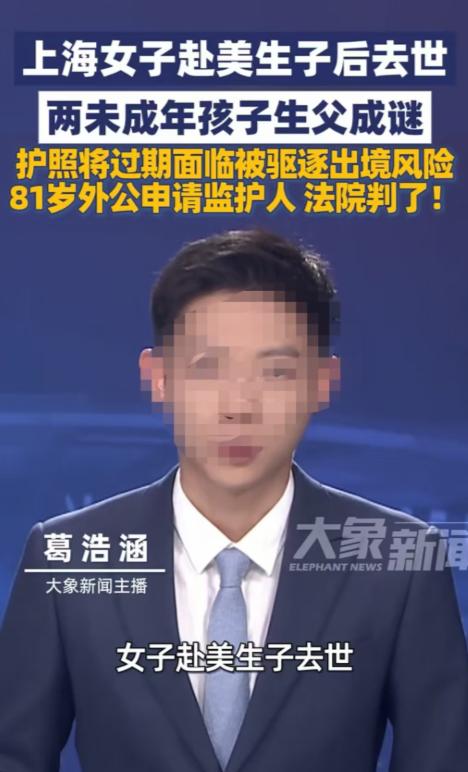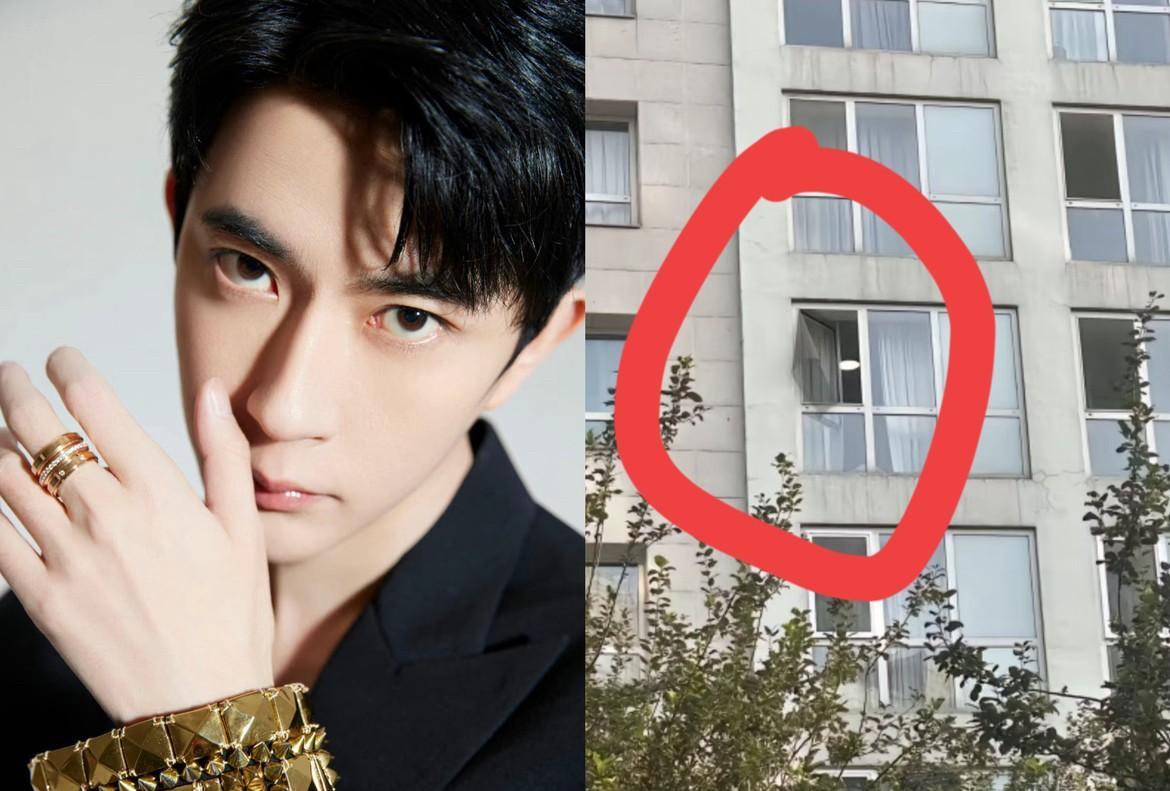上海,陈女士被聋哑邻居洪先生折磨得苦不堪言,洪先生搬来后,为发泄母亲去世的郁闷,用铁榔头敲墙、砸门,还在楼道裸 奔、扔排泄物袋子,居委会和民警多次劝阻无效,直到今年9月2日,在多方协调下,洪先生被去接受救治。
在密不透风的城市里,家本该是每个人最后的喘息之地,一个隔绝外界喧嚣的港湾。然而,当邻居的行为失控,这层薄薄的墙壁,有时连最基本的安宁都守护不了。
上海静安区柳营路319弄的一场邻里冲突,就残忍地撕开了这道口子。事件的主角,是陈女士一家,和她隔壁那位聋哑邻居洪先生。这场风波的起点,是一个人的悲伤,终点,却是一整个社区的疲惫与反思。
对陈女士来说,那柄铁榔头就是挥之不去的噩梦。自从2021年洪先生搬来隔壁,那面薄薄的共用墙体,就成了他发泄情绪的鼓面。持续的敲击声带来剧烈震动,墙灰簌簌掉落,仿佛整个家都在摇晃。
更让人胆寒的,是他会毫无征兆地猛砸陈女士家的防盗门,厚实的门板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凹痕,每一次撞击都像砸在全家人的心上。这种直接的侵犯,让家不再是安全的代名词。
恐惧很快就从门内蔓延到了门外。社区的公共楼道里,近来出现了反常的一幕:洪先生时常不着寸缕地穿梭其间。这般举动让楼里的女性住户满心不安,就连日常出门都得先在门口犹豫片刻,生怕与他撞见。更糟糕的是,楼道里时常出现装有排泄物的袋子,刺鼻的气味让邻居们每次经过都得捂鼻绕行。
私人空间被侵扰,公共秩序被破坏。陈女士的母亲已是九旬高龄,本就受心脏病困扰多年,而接二连三的惊吓,更是让她数次濒临发病的边缘,每次都让人捏一把汗。家里的保姆也被吓得直哭,嚷嚷着要辞职回老家。整个家庭,几乎被逼到了崩溃的边缘。
居委会和民警不是没来过,甚至多次把洪先生带到派出所训诫。每次他都点头哈腰,态度诚恳,可没过几天,榔头声和怪异行为又会卷土重来。这种周而复始的折磨,让所有常规的调解手段都显得苍白无力。
真正的困境在于,洪先生虽然行为失常,却并非在册的精神疾病患者,法律上他有民事行为能力,谁也无法强制他去接受鉴定。更棘手的是,他没有直系亲属,社区和警方一度连个能商量的家人都找不到。
当然,我们知道洪先生的异常行为,始于他母亲去世后的巨大悲痛。但聋哑的身份和个人的不幸,从来都不是侵犯他人权益的“免罪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情不能替代责任。
他的行为,不仅制造了《噪声污染防治法》所禁止的噪音,更实实在在地侵犯了《民法典》赋予陈女士的相邻权。无论是砸坏的门,还是被污染的楼道,都足以构成要求他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理由。
这场拉锯战的转机,出现在多方不懈的努力下。派出所和居委会反复协调,最终联系上了洪先生的远房表姐和表妹。亲属的到来,终于打开了僵局。她们也对洪先生的行为感到过分,并最终同意介入。
就在今年9月2日,洪先生被送往了静安区精神卫生中心接受治疗。楼道终于恢复了安静和清洁,但留下的思考远未结束。这次事件的解决,靠的是一次艰难的多方联动,而不是一个成熟的长效机制。
这起上海的邻里风波,与其说是一个极端个案,不如说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城市共生关系中的脆弱与挑战。它拷问着我们,当社区中出现难以被现有规则定义的“麻烦”时,我们该如何平衡关怀、法律与公共秩序,如何才能真正守护好每一个家庭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