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澳大利亚一位104岁的科学家,前往瑞士接受安乐死,当药物注射到他的体内后,他却突然开口说话,说出的话更是逗笑在场的所有人......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从1914年出生到那个春日的午后,大卫走过了一个世纪,这个名字在科学圈并不陌生,他曾在帝国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在澳大利亚投身植物学和生态学研究,他不是那种在办公室坐等退休的学者,30卷《世界生态系统》的主编工作,就像他用一生写下的学术履历,工作之余,他打网球、看莎士比亚、参加京剧团的演出,即使到了九十五岁,依然在实验室忙得不亦乐乎。 可人终归会老,大卫的身体开始发出警告,视力模糊,网球拍拿不稳,舞台灯光变得刺眼,他的工作和生活逐渐被限制,最严重的一次是摔倒在家,整整两天没人发现,那段时间,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当生活像一座空壳,只剩呼吸和等待,还有必要继续吗? 2016年,珀斯的伊迪斯考恩大学以安全为由,劝他离开,他并不接受善意的告别,他反复强调自己还具备工作能力,觉得这根本是年龄歧视,虽然校方安排了一个离家较近的新办公室,但那种孤立感却挥之不去,原来真正让他热爱的,不只是研究本身,还有那些午间讨论、会议里的争论、年轻学生的提问,换了地方,换了氛围,换不回曾经的热情。 大卫并没有疾病缠身,他没有癌症,没有中风,也没有任何医生会用“不可逆”来形容的病情,他甚至还可以自己吃饭、说话、写字,可他自己知道,那些曾经让他兴奋的事物已经失去了颜色,他不再能独自出门,不再能看清文字,不再能享受一个人自由地生活,他说过,早上醒来吃完早餐,只是为了等午饭;等完午饭,就又开始等晚餐,这种生活,在他看来,比死亡更空洞。 澳大利亚的法律并没有为他这种情况留出选择,维多利亚州虽然通过了安乐死法案,但生效时间还要等上好几个月,而且只针对病情严重、剩余寿命不足六个月的患者,他所在的西澳州,仍然完全禁止任何形式的协助死亡,大卫不是没试过争取,他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加入了“退出国际”组织,支持安乐死合法化,但法律的车轮转得太慢,他已经等不下去了。 瑞士成了他的目的地,这个中立国是为数不多允许外国人自愿结束生命的地方,他通过众筹平台募集了所需的费用,并在2018年5月初启程,旅途中还顺道拜访了法国的亲戚,这次出行,他穿上了那件藏蓝色的旧西装,是三十年前女儿送的,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穿它。 到达巴塞尔后,他接受了诊所的标准流程,两位独立医生评估他的情况,确认他在神志清醒、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做出了决定,他告诉医生,自己没有生病,只是对生活不再感兴趣,没有犹豫,也没有悲愤,他觉得自己像一本书,已经翻到了最后一页,不需要再加注脚,也不想硬撑着写一章番外。 这不是冲动,而是一种有计划、有节奏的结束,他知道这件事可能会引发争议,也明白自己正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他不是想成为谁的榜样,也不是要挑战什么制度,他只是想为自己争取一个体面的结局。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过得很有仪式感,他吃了炸鱼薯条和芝士蛋糕,是他最喜欢的一顿饭,他选择播放贝多芬的《欢乐颂》,因为那首曲子象征着自由与生命的张力,他躺在床上,听着音乐,亲手启动了注射设备,几秒钟后,他睁开眼睛,说药效似乎慢了些,这句轻描淡写的话,像他一生的缩影:幽默、不慌张、坚持清醒。 几分钟后,一切归于平静,他的呼吸停止,医生确认了时间,窗外的街道还在运行,自行车铃声照旧响起,阳光照进病房,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但对于陪在他身边的家人来说,那一刻,是一段旅程的终结。 大卫的决定在澳大利亚引发了不小的波澜,有人称赞他为老年人争取了选择权,也有人担忧这是否会鼓励社会对老年群体的排斥,人们开始重新讨论一个古老又敏感的问题:人有没有权利在没有致命疾病的情况下,选择结束生命? 他的选择没有答案,却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提醒:寿命的延长并不等于生活的质量,当科技不断延长人的生理极限,是否也该让人有权利说“不”?尤其是当一个人已经无法独立生活,已经失去了与世界互动的能力,他是否有资格选择体面地告别? 这不是关于生或死的问题,而是关于尊严的议题,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一个人最需要的或许不是药物和机器的维持,而是被认真倾听,被真诚理解的自由。 大卫·古道尔没有轰轰烈烈地谢幕,他像他研究了一辈子的植物那样,安静地凋谢,他没有等到法律的改变,但他用那场清醒的离开,让世界重新思考了一个问题:尊严,是不是比多活几年更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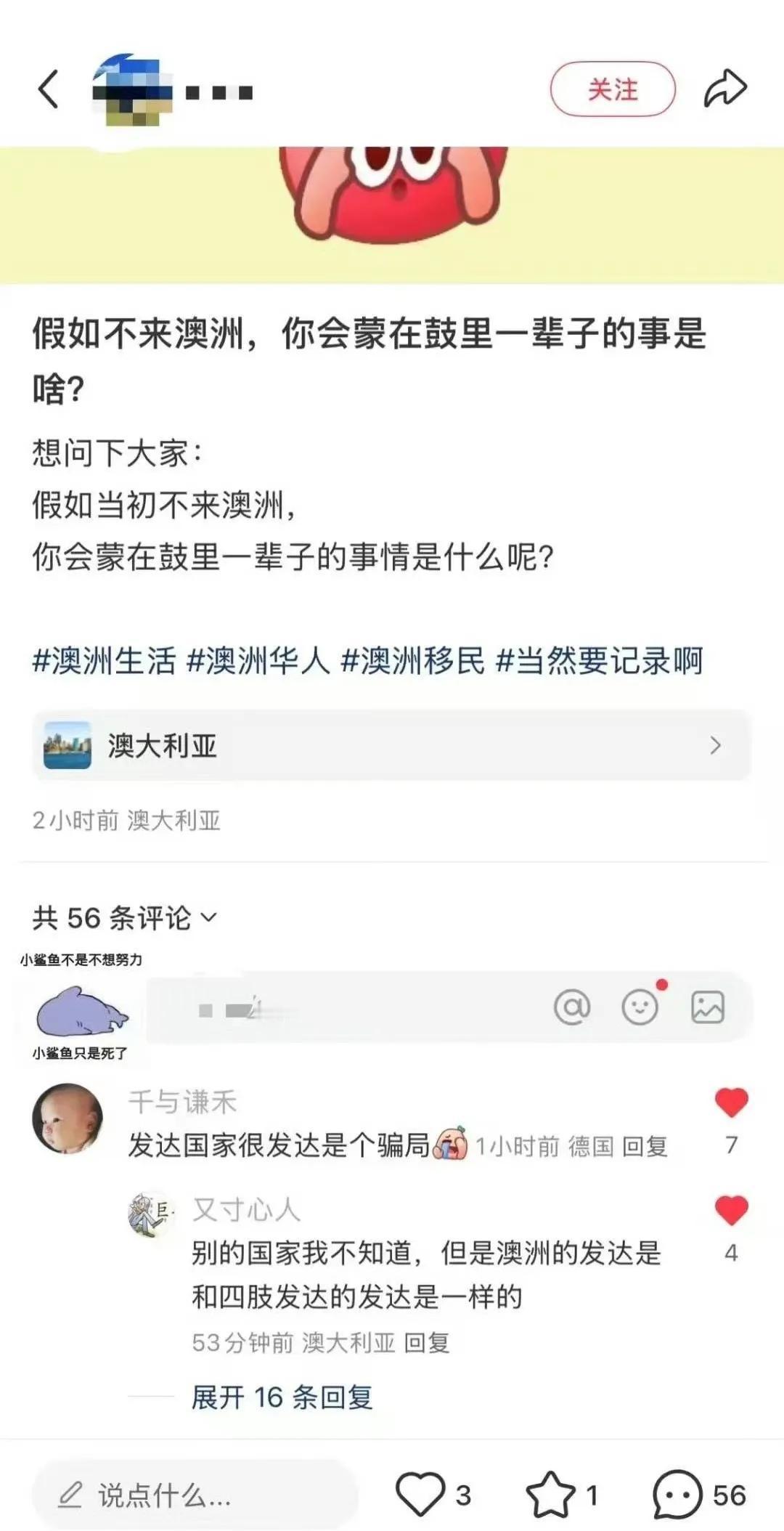





龙舞
翁帆给这篇文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