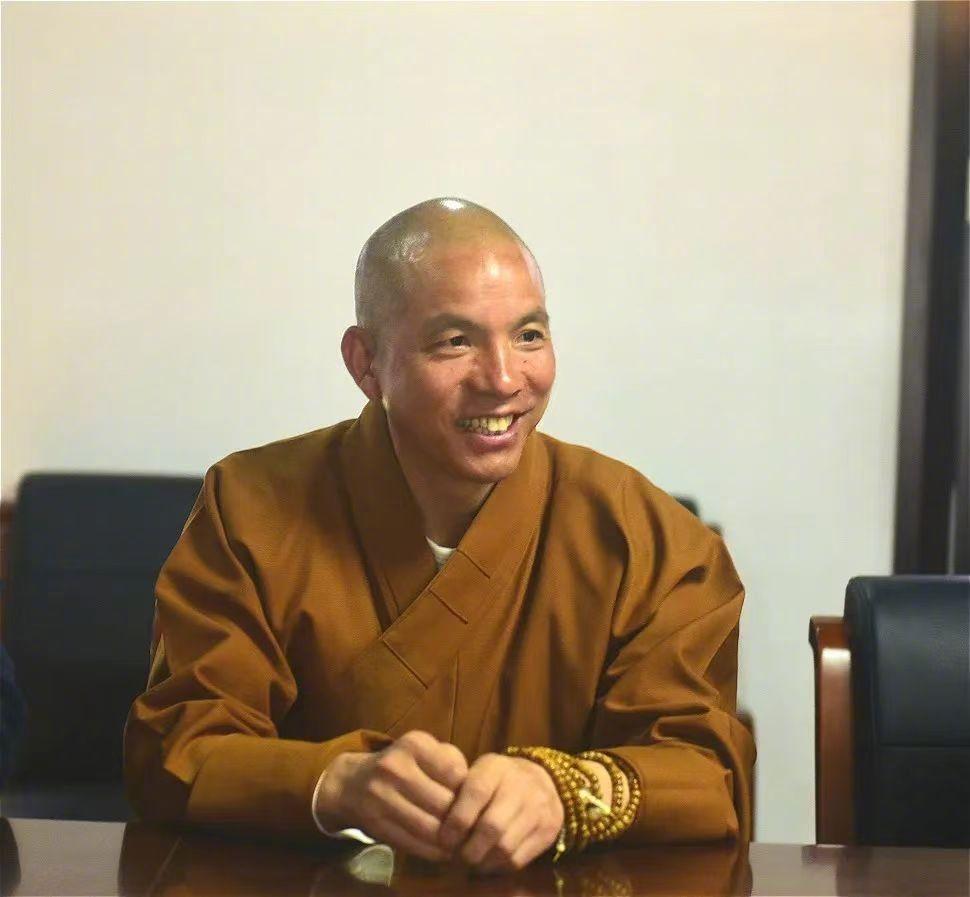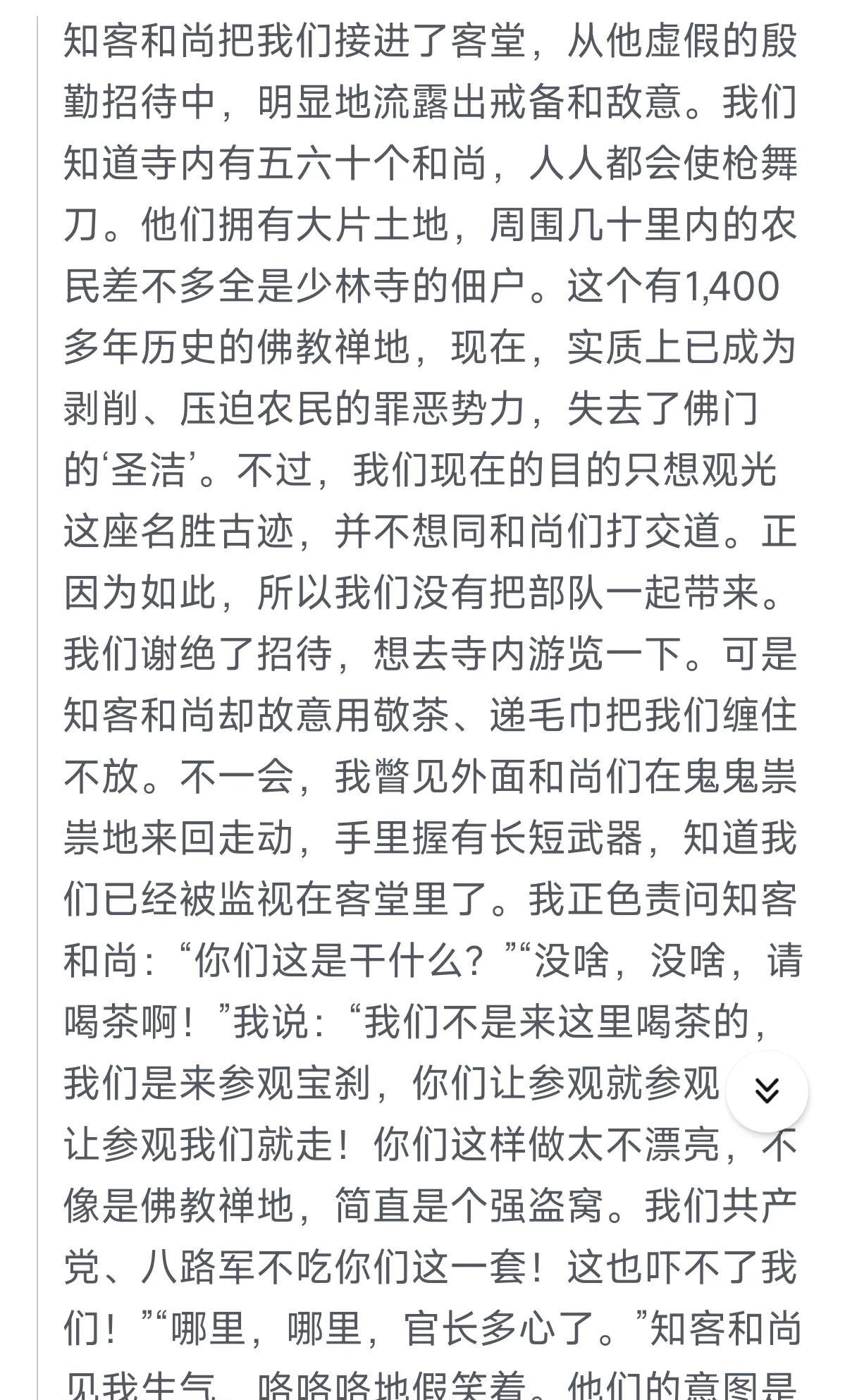蒋介石孙子召开发布会,申请"两蒋"移灵大陆, 说了两句话令人唏嘘! 台北的秋天总带着点湿冷,1996 年的这场发布会,连空气里都飘着沉郁。 蒋孝勇坐在轮椅上被推上台,领口显得空荡荡的,食道癌把他熬得只剩一把骨头。 台下的闪光灯噼里啪啦响,他却没看镜头,只望着前方的虚空,开口时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爷爷和爹想回家,这事儿,我得做。 蒋家后人,别指望别的,得自己站直了。 这两句话,后来在台湾的茶馆里被念叨了很久。 有人说听得心头发酸,也有人说,这不过是蒋家想翻局的由头。 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两句话的分量,是蒋孝勇用半条命托着的。 往回数到 1975 年,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断了气。 弥留那几天,他总抓着蒋经国的手嘟囔,说紫金山的松树该长得更密了,溪口老家的竹篱笆怕是得修修。 最后留了话:要么葬在南京,跟孙中山作伴;要么回奉化,守着老娘的坟。 那会儿两岸连封信都难通,灵柩只能先搁在桃园慈湖,棺木底下垫着砖块,离地三寸 —— 这是奉化的老规矩,“客死在外,暂不落地,等着归乡”。 13 年后,蒋经国也走了。 他没那么多嘱咐,只对蒋孝勇说:“我跟你爷爷一样,想回溪口。” 灵柩又被挪到了大溪头寮,离慈湖不远,却同样悬着,没沾土。 蒋孝勇是看着这两口棺木长大的。 小时候,爷爷常把他架在肩上,指着地图上的 “浙江” 两个字,说那里的水是甜的;父亲则爱在深夜翻老家的相册,指着一张桂花树的照片,说 “这树开的花,香得能醉倒人”。 这些零碎的片段,后来成了他揣在怀里的念想。 1996 年开春,蒋孝勇咳得直不起腰,医生把诊断书递给他 —— 食道癌晚期。 他没告诉家人,偷偷填了去大陆的申请表,理由是 “赴北京就医”。 批文下来那天,他把药瓶揣进兜里,盯着窗外的雨看了很久。 到了北京,他先去医院抽了胸水,然后瞒着医生,坐火车转汽车,往奉化赶。 溪口的蒋家老宅还在,红漆木门上的铜环被摸得发亮。 院里的桂花树比照片里粗了两圈,守宅的老人说:“这树啊,年年开花,就跟等着谁似的。” 他往后山爬,蒋母的坟前摆着新换的供品,墓碑被雨水洗得发白。 旁边留着两块平整的空地,老人叹口气:“早年间就备好的,说是给蒋先生和他儿子留的。” 那天他没说话,对着坟磕了三个头,起身时膝盖都麻了。 回到台北,他就定了开发布会的日子。 可路早被堵死了,那会儿李登辉正忙着在国民党里 “换血”,亲蒋的人要么被调去闲职,要么干脆被赶下台。 街头的 “中正路” 牌子一个个被换掉,学校里的蒋介石铜像,今天被泼漆,明天被推倒。 蒋孝勇这时候提移灵,无异于往火坑里跳。 申请递上去,石沉大海,他找了当年父亲的老部下,人家闭门不见;托人给台湾当局传话,得到的回复就四个字:“时机未到”。 他又去了趟美国,见了宋美龄,老太太摸着他的手掉眼泪:“移灵的事,若实在难,就先搁着。 等两岸成了一家人,总会成的,可蒋孝勇等不起了。 12 月的一个清晨,他在医院里咽了气,才 48 岁。 临终前,他让儿子把爷爷和父亲的遗愿抄在纸上,塞进了贴身的口袋。 这些年,慈湖和头寮的棺木还悬着。 有游客去参观,导游会指着那离地三寸的棺木说:“这里面的人,到死都想着回家。” 有人说,这事儿就是蒋家的执念,没必要当真。 也有人说,不管生前做过啥,想回故土总是真的 —— 就像那些漂洋过海的老华侨,临终前总得念叨着,把骨灰撒回老家的河里。 前阵子去溪口,见蒋家老宅的桂花又开了,香得能飘半条街。 守宅的老人说,常有蒋家的后人托人来看看,问能不能在旁边栽棵小树苗,“万一哪天回来了,好认家门”。 至于蒋孝勇那两句话,偶尔还会被人提起。 有人说,“回家” 这两个字,从来就不只是家事。 也有人说,“自己站直”,或许才是蒋家后人最该走的路。 那么你们怎么看呢? 如果各位看官老爷们已经选择阅读了此文,麻烦您点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各位看官老爷们的支持! #夏日旅行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