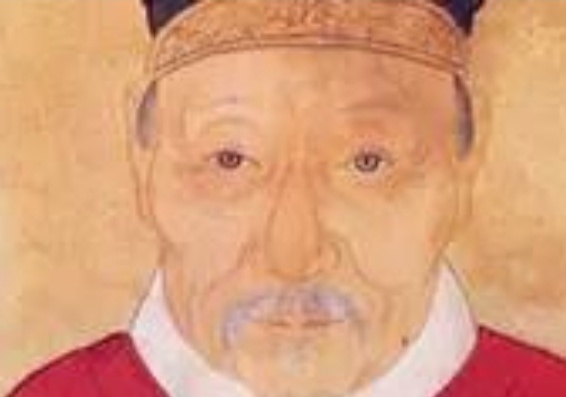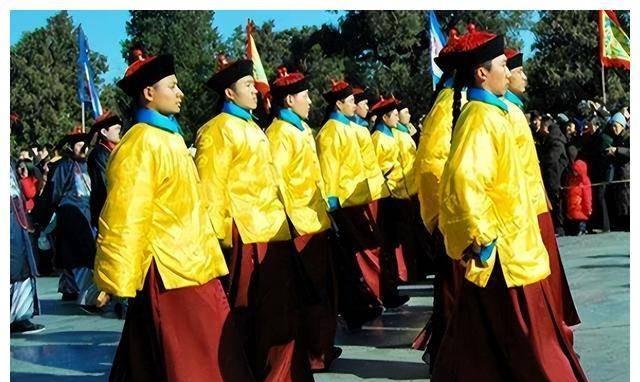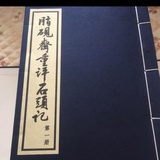晴雨风说史[超话]晴雨风说史
1403年秋,官员刘固全家被押赴法场处决,当刽子手的鬼头刀斩下八十岁刘母头颅时,她十五岁的孙儿刘超突然挣断绳索,夺过染血的铡刀。这个青州教谕家的少年如同困兽爆发,刀锋所向血浪翻涌,十三名官兵瞬间毙命。
监斩官的官帽滚落血泊,他颤抖着嘶吼拦住那疯崽子,但是他却不知自己正见证瓜蔓抄暴政的第一道裂痕。
话说在1399年的山东青州,教谕刘固正为老母袁氏的病容忧心。而这位以清廉闻名的地方学官,在辞官奉母的奏疏里写道,臣母风烛残年,乞骸骨归乡奉汤药。
当奏疏辗转至南京御史大夫景清案头,这位爱才如命的老臣提笔回信,若得迎母南来,既全孝道,更可效力朝廷。
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封寻常举荐信,将刘家拖入深渊。那时候的南京城表面风平浪静实则背地里暗流汹涌,因为燕王朱棣的靖难大军已破长江。
当景清怀揣利刃刺杀新帝未遂,被朱棣下令悬于长安门时,锦衣卫翻查旧信的手,已悄然扼住青州刘氏的咽喉。
凡有与其交往、推荐、同窗、甚至议论,都能被纳入瓜蔓抄名单,一人获罪,十家遭殃。
而瓜蔓抄的罗网撒下时毫无预兆。建文四年深冬,官兵踹开刘家木门,将正在喂药的刘固拖下病榻。
刑部大牢里,刘固看着隔壁监舍啼哭的幼子,突然明白景清信中效力朝廷四字,竟成了催命符。
恶朱棣的清洗逻辑简单而残酷,凡与景清有书信往来者皆属逆党。方孝孺被诛十族的血腥尚未散去,刘家三代入狱的消息已震悚青州。
最讽刺的是,刘固与景清素未谋面,那封改变命运的信里,连句寒暄都未曾有过。
在1403年秋决日的晨雾中,刘家三代被缚于刑台。刽子手特意调换行刑顺序,先斩八十岁的刘母以慑余孽。
当鬼头刀划破老妇干瘦的脖颈,热血喷溅在少年刘超脸上。这个由祖母一手带大的孩子,突然发出野兽般的嘶吼。
绳索吱嘎断裂声惊得刽子手回头,只见黑影扑来,事后幸存的狱卒回忆。刘超自幼习武的膂力此刻爆发,夺刀后直劈刽子手颈项。
吓得监斩官跌坐在地,这时候已有五颗人头滚落脚边。少年囚衣被血染成绛红,刀锋专斩官兵咽喉,像在割断勒死祖母的绞索。
当三十名官兵终于将力竭的刘超压倒在地,他咬碎的牙齿混着血沫喷向监斩官,朱棣老贼!此时的刑场一片死寂,而这句嘶吼如同惊雷劈开永乐元年的阴云。
得知此事之后的朱棣震怒,原本这种“瓜蔓抄”案子,是他亲自定调的政治清洗法。但这起冲突太过激烈,影响太大。刘超的举动虽已被镇压,但流言已经四起。
于是便下旨将刘超凌迟三千六百刀,但刽子手发现行刑时异常艰难,少年始终怒目圆睁,直到最后一片血肉离身才咽气。
更诡异的是,此后半月南京连降血雨,市井传言天公泣刘郎。
而这场反抗撬动了铁幕统治。次年春,朱棣默许刑部修改瓜蔓抄条例,新增查实证连"条款。青州百姓偷建衣冠冢,每逢清明,总有不知谁放的带露野花。
六百年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泛黄卷宗上,关于刘超的记载仅剩冷硬的两行:刘固孙,刑场夺刀戕官兵十三,诏磔之。
但当年刑场三里外的茶肆账本里,却夹着茶客的涂鸦,是日见赤虹贯日,疑有壮士殁。
少年染血的身躯早已化尘,但他斩裂的绳索仍悬在历史高空,当山东琅琊台出土明代"禁连坐碑时,学者在碑阴发现一行小字,永乐三年诏,罪止本身。
这九个字,是用多少个刘超们的热血浇铸而成?
刑场青石板的血痕早被雨水冲净,唯有那柄重十八斤的鬼头刀,至今在博物馆展柜里泛着幽光。
刀身映出参观者年轻的脸庞,与六百年前少年愤怒的眉眼重叠。当讲解员轻叹他死时比你们还小呢,总有少年攥紧拳头,仿佛听见血脉里传来绳索崩断的铮鸣。
都说乱世出英雄但也不是每个乱世里都有英雄。但是总有人,会用命去喊出那个被压制的声音,哪怕只有一瞬,也要咆哮。哪怕下一刻就死,也不沉默,这,就是十五岁刘超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