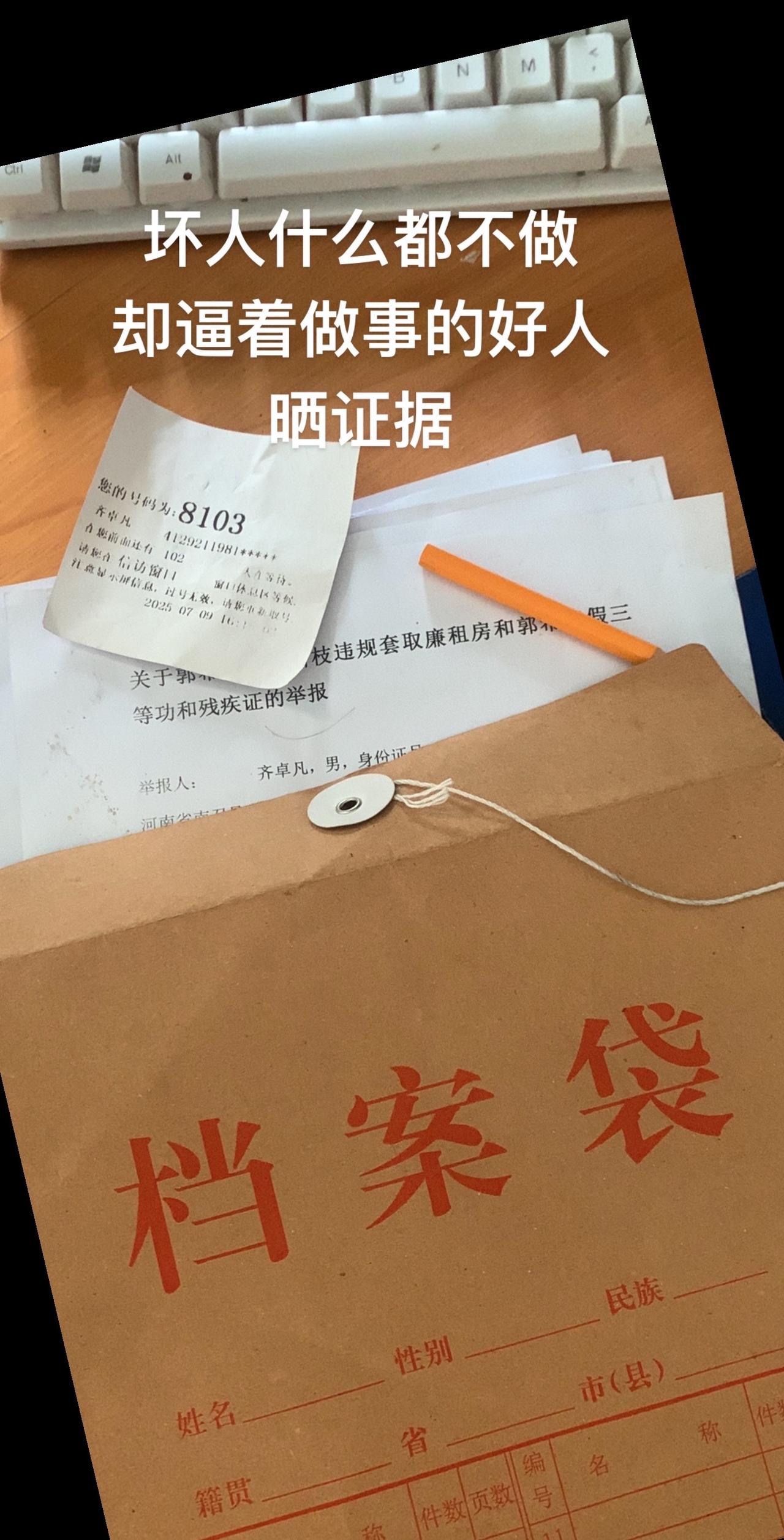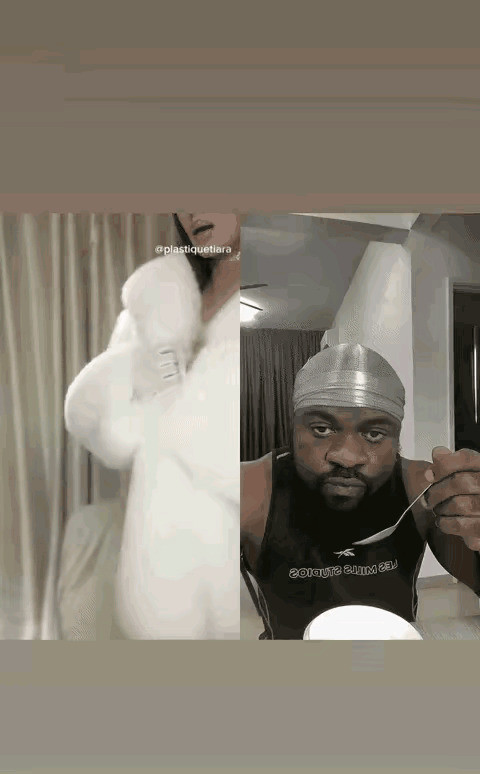东北野鸡泛滥成灾,为何很少有人吃?当地农民直言:“别说吃了,我们甚至都不敢招惹它! (信源:中华网热点新闻——东北野鸡泛滥成灾,野鸡多到撞墙无人吃,为何无人敢动?) 在东北的广袤田野间,张老汉叼着烟卷,望着远处那群扑棱棱飞过的野鸡,嘴里不住地抱怨:“都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可如今这满地乱窜的山鸡,咋就成了烫手山芋?”这些曾被视为美味的“香饽饽”,转眼成了当地农民最挠头的“祸害”。 回溯往昔,东北的生态远非今天这般模样。彼时,“野鸡飞进饭锅里”不是传说,而是寻常景象。 除了雉鸡(俗称山鸡),就连更为珍稀的花尾榛鸡,也就是俗称的“飞龙”,也偶有现身。那时的东北,一派“天苍苍野茫茫”的立体生态图景,人与自然看似和谐。 然而,这份野趣并非一成不变。百年来人类活动的深刻烙印,让这片土地上的野鸡种群经历了一场剧变。从清末开始,大规模的“闯关东”移民潮打破了朝廷的封禁。 为了生存,无数林地草场被开垦,人口从七百多万激增至上亿,野鸡的家园被急剧压缩。紧接着,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黑土地,对森林、矿产的疯狂掠夺,给东北生态带来了毁灭性破坏,无数野生动物就此流离失所。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作为重工业和粮食基地,高强度的开发建设持续挤压着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栖息地破坏、无序猎捕,再加上与人工品种的杂交,野鸡的身影一度变得越来越稀罕。 不过,历史的车轮滚入21世纪,风向变了。国家开始算生态这本大账,大规模的生态修复工程在东北启动。 持续推进的“封山育林”、全面禁猎以及保护级别的提升,让野鸡(三有保护动物)和飞龙(二级保护动物)的种群数量得到了显著恢复,甚至可以说,它们正以惊人的速度卷土重来。 谁知,这份来之不易的成功,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在缺少天敌制约的环境下,野鸡的繁殖速度简直像坐了火箭,数量爆炸式增长,反倒成了新的麻烦制造者。 这些扁毛畜生胆子越来越肥,不再见人就跑,而是大摇大摆地闯入农田,把庄稼地当成了“自助餐厅”。张老汉跺着脚下的冻土抱怨,春播的种子,十粒有八粒进了野鸡肚子。 村民们曾尝试过扎稻草人、挂光盘等方法,但这些手段很快就失去了作用。野鸡不仅未被吓退,反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甚至学会了站在假人头顶拉屎以示挑衅。 更让人窝火的是法律与现实的脱节。谁家想拉道网保护庄稼,第二天准保接到林业部门的电话;放狗追几声,立马有人举报虐待动物。有村民气不过朝天上扔石子吓唬,结果被批评教育半天。 用他们的话说:“感情这年头,连扔石头都得看黄历。”这种“光堵不疏”的治理方式,就像憋洪水,让农民们叫苦不迭。 更何况,防疫站的技术员还私下透露,野鸡携带的寄生虫可能传染给人畜,去年邻村就有孩子吃了被野鸡粪便污染的野果闹肚子住院。可这话,谁又敢公开拿到台面上说? 面对困境,仍需脑筋急转弯。村里的年轻人开始探索新策略,例如在田边种植野鸡厌恶的艾草,或在播种后迅速覆土以作掩护。而乡政府近期也透露出积极态度,表示正在探讨“限量调控”的方案,这无疑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 生态政策本就该动态调整,而非一成不变。就像许多地方泛滥成灾的野猪一样,国家也已适时调整政策,允许对部分区域进行科学捕猎。 正如张老汉说的,家里养猪,光喂不宰,早晚得把圈撑破。生态这杆秤,两头都得挂着砣才稳当。 从“飞进饭锅”的寻常,到一度难觅踪影,再到如今的泛滥成灾,一只小小的野鸡,折射出的是东北百年来的历史变迁与发展阵痛。 它身上既有殖民掠夺的惨痛记忆,也展现了国家在生态修复上的决心与成果。说到底,所有生态保护的努力,根本上都是为了人能生活得更好。 那么,面对这种“保护过当”催生的新矛盾,我们又该如何找到那条既能守护自然,又能保障民生的平衡之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