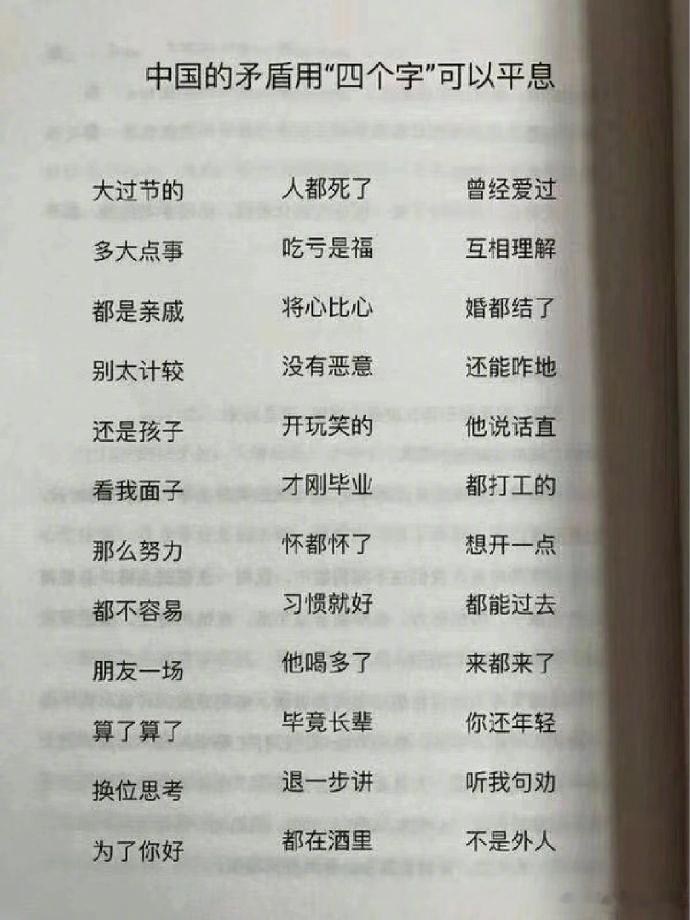#我的宝藏兴趣# 今天,接到伊春峰岩山寨景区,厨师小东的电话时,窗外正飘着春雨。他说,景区老总留了几斤林蛙母豹子,要等我回去时提前知会一声,好再下几张网捕些湖里带籽的鲜鱼:“老板说了,开春的鱼蒸着最鲜,山野菜也冒头了,准保让你尝个新。”这带着松香的惦记撞进耳膜时,伊春的雪忽然就漫上了心头——漫过峰岩山寨的瓦檐,漫过柴火灶前添柴的大哥,漫过我们在这片白桦林里沉淀的四年光阴。 初见大哥时,他正站在木栈道上给游客指认 蚂蚁包。东北人的豪爽在他身上拧成了股绳:“瞅见那堆包没?蚂蚁昨儿刚搬的家!”转头见我和妻子背着相机发愣,立刻扯着嗓子喊后厨:“把东头那间带观景的别墅拾掇出来!” 那几年我们长住山寨,大哥总把最好的屋子留给我们。雪松木雕的窗棂上凝着霜花时,大床上的羽绒被暖融融,床头摆放着那瓶晶莹的桦树汁,通透的阳光从窗外射入。他常说:“住得舒坦,心才稳当。”有次我见他踩着梯子给我们换窗纸,零下二十度的天,鼻尖冻得通红,却非要把窗角裁出个梅花形:“透光性好,看着也乐呵。” 山寨的烟火气藏在大哥的菜谱里。野猪二代的肉在铁锅里咕嘟作响时,他总爱往我碗里多夹两块肥瘦相间的:“尝尝这火候,筋膜炖得比你写的文章还软和。”最难忘那年雪后,他非要露一手“雪地蒸肉”——五花肉码在青瓷盘里,撒上葱花、辣椒面,搁在松木蒸笼里蒸得酥烂。蒸汽漫过他眯起的眼,“这味儿,能勾得神仙下凡尘。” 更绝的是雪地烧烤。大哥开着雪地摩托载我冲进白桦林,雪粒子打在护目镜上沙沙响。归来时,冰包上早支起了烤架,羊肉串在炭火上滋啦冒油,他摸出用棉套裹着的散篓子:“咱东北人喝酒,就得对着漫天雪片子才得劲儿!”酒液滑进喉咙时,远处的雪松林正簌簌落着碎琼乱玉,分不清是酒香醉了人,还是这冰天雪地醉了心。 疫情那年的冬夜,广东客人突发高热。大哥的手电筒光柱在雪地里划出急促的弧线:“别急,咱这儿离医院二十分钟车程。”他裹着羊皮袄坐在驾驶座上,车轮碾过积雪的声音像炒豆子般噼里啪啦。急诊室的白炽灯下,他攥着我袖口的手全是冷汗:“可别是那啥病啊,咱得对客人负责。”直到医生说只是普通风寒,他才蹲在走廊里猛抽了根烟,烟灰簌簌落在棉鞋上:“吓煞我也。” 返程时,东方已泛起鱼肚白。他突然把车停在结冰的湖畔,指着远处说:“你瞧,雪停了,松针上挂着的冰溜子像不像水晶串?”我望着晨光里他染霜的鬓角,忽然懂了——这山里人不会说漂亮话,却把“仗义”二字,刻进了每一片雪花里。 恍惚间又看见那年大哥在雪地里比划的手势,说下网要挑清晨三点,“鱼刚醒,懵头懵脑就撞进网里”。原来有些惦记,早像山里的根系般盘根错节——不是血缘胜似血缘,不用开口却早已懂得。此刻我摸着案头大哥送我的圆润的核桃,忽然明白这十年光阴为何这般沉甸:不是因为山水如画,而是有人把日子过成了诗,把情谊酿成了酒,让每一个平凡的晨昏,都有了心跳般的温度。 山风掠过窗棂时,我听见远处的林海在低吟。待归期至,定要再与大哥对坐火塘边,就着新捕的湖鱼,把这些年的霜雪与星光,下酒慢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