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像白纸,没有被污染。他们是革命最纯洁的武器”。作为“纯洁社会”的中重要环节,波尔布特在屠杀人民时,没有忘记系统性将儿童改造为自己的杀人工具。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5到1978年,红色高棉大约征召了3万至5万名8–16岁的儿童。这群儿童在红色高棉的高强度系统化训练中,成为了凶残的暴力执行者。
安吉丽娜·朱莉在执导的影片《他们先杀了我父亲》中,以5岁女孩的视角呈现了童子军的训练场景。虽然,她已经刻意弱化血腥,但通过儿童机械重复口号、麻木执行命令的细节,人们仍然可以感受到那个“去人性化”的时代。

从“孤儿”到“革命之子”
“安卡是你们的新父母,革命是你们的家”。在“建立纯洁社会”的行动大纲下,家庭被红色高棉视作“旧社会的毒瘤”,被强制拆散。夫妻、父母与子女被分送到不同的劳动营。而儿童则被彻底切断与原生家庭的情感纽带,集中到“少年营”,接受军事化管理和意识形态灌输。
西哈努克在其1980年的著作《战争与希望:柬埔寨现状》中表示,一旦这些儿童被招募进了革命队伍,那么就会与亲族分开。红色高棉会授予他们普遍认为的最大荣誉头衔,称作“Oppakar phdach kar robas pak”,翻译过来其实就是“党的专用工具”。
在儿童兵的选择上,红色高棉优先招募8–12岁儿童。因这个阶段的儿童认知不成熟、道德判断未形成、服从性强。前儿童兵Hun Nareth在回忆中说:“他们给我米饭和一把枪,说我是‘安卡的眼睛’。我那时11岁,觉得比当农民的儿子光荣”。
红色高棉的研究者卡尔·杰克逊于1989年写成的《柬埔寨1975-1978:与死亡会合》中谈到,儿童兵被红色高棉灌输的教育只有铁一般的纪律和仇恨心态。在内部,谁批评和反对红色高棉,谁就是吃里扒外的国家敌人和柬奸。在外部,谁批评红色高棉,谁就是干涉内政,抹黑柬埔寨,不想让柬埔寨强大。
当然,要达成对红色高棉的“令行禁止”,儿童兵必须从多个层面进行改造。
首先,语言即世界。将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用到此处,不知他会作何感想。然而,红色高棉确确实实地对儿童兵进行了语言重构。儿童兵们每日需要背诵充满波尔布特语录的“安卡教导”,代替祈祷。他们也被禁止使用“爸爸”“妈妈”这样的词汇,而改称“男同志”“女同志”。同时,将“杀人”称为“完成任务”,“哭泣”称为“软弱”。在这样的词汇描述中,儿童兵们的行动基本不会超越他们所能接触到的语言体系。
其次,红色高棉也对儿童兵进行暴力的脱敏训练。从强迫儿童亲手宰杀鸡、狗、牛,到旁观处决,再到亲手执行,用锄头、镰刀、木棍处决曾经的老师、长辈等“叛徒”,儿童兵在这其中逐步成长为红色高棉的杀人工具。前儿童兵Kosal Khiev回忆红色高棉的干部们如此威胁他们:“如果你不打,你就是叛徒。我闭着眼打下去……那个人是我小学老师”。

行为异化:儿童如何成为高效杀手?
“孩子们最可怕。他们不犹豫,不谈判,不收贿赂。命令一下,锄头就落”。
在红色高棉体系中,儿童兵常比成年士兵更“可靠”。因为,儿童兵尚未形成独立批判思维,更少质疑;害怕被送回饥饿的劳改营,更易被恐吓;为证明“忠诚”而过度表现暴力,从而更残忍;而其儿童身份更易降低受害者戒心,也更隐蔽。
于是,我们看到,无数的儿童兵在村庄“揭发”父母藏匿食物,在监狱担任看守、记录员、行刑助手,在边境巡逻中射杀逃亡者,在执行“内部清洗”中处决“动摇”的成年干部……
Him Huy(化名),1976年时,他12岁,他在自己的家乡磅士卑省某集体农庄,担任村庄“净化小组”成员,负责监督、举报、处决“思想不纯者”。
1976年,村庄粮食短缺,一名老教师被举报“私藏一捧米”。村“安卡代表”立即命令Him Huy及其两名同龄伙伴“执行教育任务”。三人被告知:“旧社会的虫必须用新社会的工具打出来。”
于是,老教师被绑在木桩上,Him Huy第一个挥锄,击中其左肩。老教师未叫喊,只低声说:“孩子,你妈妈知道吗?”三人轮流击打约15分钟,直至其死亡。尸体被丢入稻田作肥料。事后,三人各得半碗米饭和一小块腌鱼作为“革命奖励”。
Him Huy在1979年越军攻入后逃亡,隐姓埋名务农。2008年,他在非政府组织首次公开证词,痛哭失声:“我杀的是教我写字的人……他给我吃过糖。”2012年,他自愿前往受害者家属村庄下跪道歉,被石块驱逐,额头缝7针。

创伤后遗:杀人儿童的终身诅咒
“我30岁才第一次哭。梦见老师跪着求我别打。我醒来抱着头撞墙,但我知道,那怕撞破头,也唤不回老师的死”。
红色高棉倒台后,很多儿童兵回归村庄。然而,他们常被视为“恶魔余孽”,遭到昔日受害者家属排斥:“你杀了我父亲,你还敢回来?”他们中的很多人因此出现自残、酗酒、暴力倾向。
1975年,10岁的Keo(化名)举报和参与处决了自己的亲哥哥。起因是,哥哥在劳改营时偷吃了生稻谷。指导员召见和哥哥同在一个监狱的Keo,试图说服她:“你不是旧家庭的妹妹,举报叛徒是革命女儿的最高忠诚”。为了增强说服力,指导员同时允诺Keo,如果她指证哥哥,并可以获得象征荣誉与权力的红袖章以及额外配给的半勺粥。Keo最终没有抵抗过诱惑。她在批斗会上高喊:“我哥哥偷吃人民的粮食,他心里有虫!”当晚,她的哥哥被绑在木架上,Keo被命令用竹签刺穿他的腹部“驱虫”。哥哥临死前看着Keo,没有说出一句话。隔天,哥哥的尸体就被丢入沼泽。
1979年,红色高棉倒台后,Keo被自己姑姑收养,但家人都拒绝和她同桌吃饭。1995年,Keo试图在哥哥死亡沼泽边立木牌纪念哥哥,被村民们阻止:“你没资格纪念他”。2003年,她在金边当街头小贩,她拒绝生育,因为她认为自己的血是肮脏的。2020年,她在纪录片《血亲》中露面,镜头前反复陈述:“红袖章……粥……很香”。

现代神经科学揭示,由于儿童前额叶皮质未成熟,其负责道德判断、冲动控制、共情的脑区尚未发育完全。因此,用恐惧与奖励可强化他们的“服从回路”;用重复暴力可以削弱他们的“共情基础”;用语言可以剥夺抑制他们的“自我反思”。在这样的步骤之后,高服从性、低共情力、高攻击性的“社会化武器”就被制造了出来。
而这也是红色高棉儿童兵区别于全球其他地方儿童兵的独特之处。他们在被系统性“教育改造”的同时,仍然怀有“神圣使命感”,相信无神论乌托邦、阶级净化,可以做到对自己的父母、老师、邻居暴力相向。而实质上,他们其实是被“制造”的国家暴力机器。
既然,儿童可以被塑造成“杀人机器”,那么谁才是最该为此负责的人?
儿童的可塑性,是文明的希望,也是专制暴政的漏洞,教育者不可不深重警示。
档案来源:
DC-Cam(柬埔寨文献中心)档案编号:KR-00478-12
·纪录片《红色高棉:我杀过老师》(2013),导演:Sothana Srun
·马德望省地方志,1998年版,“劳改营儿童行为记录”
·纪录片《血亲》(Blood Relative),导演:Rithy Panh,2020
·口述历史项目:柬埔寨妇女创伤记忆库,编号WTC-0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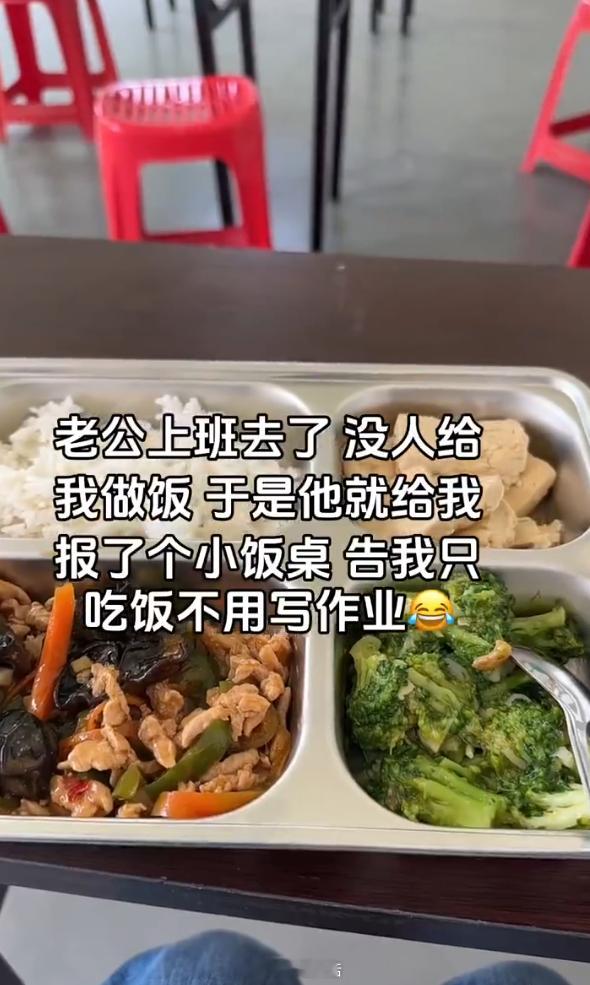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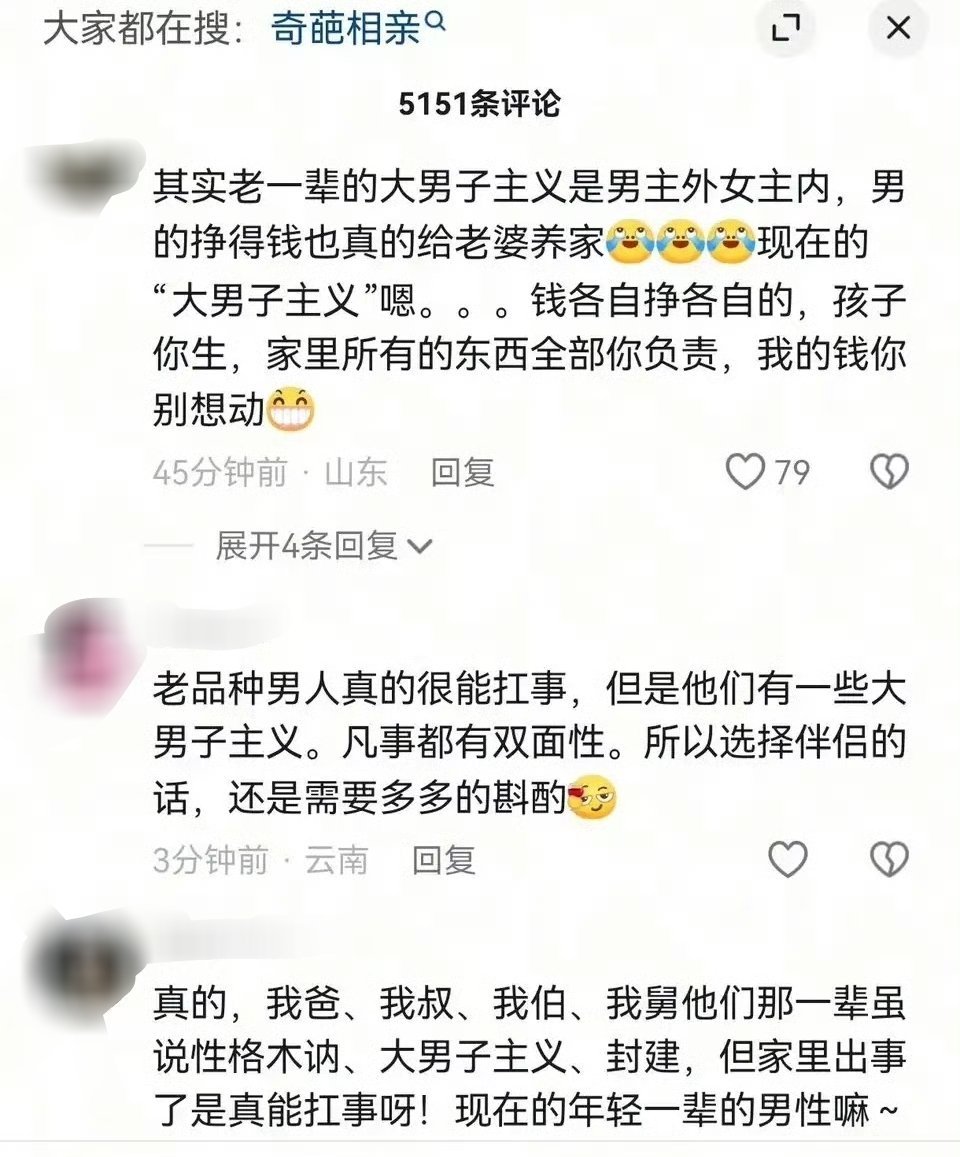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