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境到史境
——一位时代歌者的“三部曲”嬗变与精神远征

在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叙事画卷中,总有一些独特的笔触,它们并非高踞于庙堂之上,而是深深扎根于时代的脉搏,以个体的敏锐感知,记录着民族复兴的宏大交响。文友评述经典:你跨越近三十年的光阴,从澎湃激越的万行长诗“三部曲”,到沉郁厚重的百万余字非虚构“三部曲”,这一创作轨迹的嬗变,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从文学青年到高级记者的身份转型,更是一部微缩的精神史,映照出一代知识分子如何将个人才情融入时代洪流,从抒写“诗”的意象,转向构筑“史”的基石。
第一部曲:长诗时代的浪漫主义咏叹——为时代巨变赋形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新世纪初,是中国社会积蓄力量、即将喷薄而出的关键时期。我的创作起点,正源于此。1998年的重庆九龙坡广场,一句关于“九条龙”的古老童谣,成为了引爆诗情的导火索。这并非偶然。童谣是民间记忆的活化石,而“龙”则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文化图腾。我伏案疾书,昼夜创作,写就《九龙吟》,其意义远超于对一地来历的考据与诗化,它是一次从民间土壤中汲取灵感的寻根之旅,是用浪漫主义的诗行,为一座城市、一个区域的精神底蕴进行文学奠基。也许,此时的我,算得上一位行吟诗人,用耳朵捕捉着来自历史深处与市井巷陌的回响。

这种对时代律动的捕捉,在随后的《天路吟》与《动脉吟》中达到了高潮。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这不仅是工程奇迹,更是人类意志对地球之巅的征服。当火车在“天路”上呼啸而过,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时空压缩感与民族自豪感。诗歌,这种最古老也最富激情的文体,成为了为这一震撼性事件“赋形”的最佳载体。《天路吟》吟诵的,是雪域高原与现代文明的交响,是“速度”对“极限”的超越。

紧接着,2009年,京津城际铁路以350公里的时速,重新定义了中国的“距离”。我坐上列车,体验到的“感动”,其内核是又一次深刻的速度冲击与发展震撼。《动脉吟》的标题本身,就精准地把握了高速铁路作为国家经济“毛细血管”与“大动脉”的核心隐喻。这三部长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象群:从盘踞大地的“龙”(《九龙吟》),到通往天堂的“路”(《天路吟》),再到奔涌活力的“脉”(《动脉吟》)。它们共同完成了对一个狂飙突进时代的浪漫主义咏叹,是文学对“中国速度”最直接、最炽热的情感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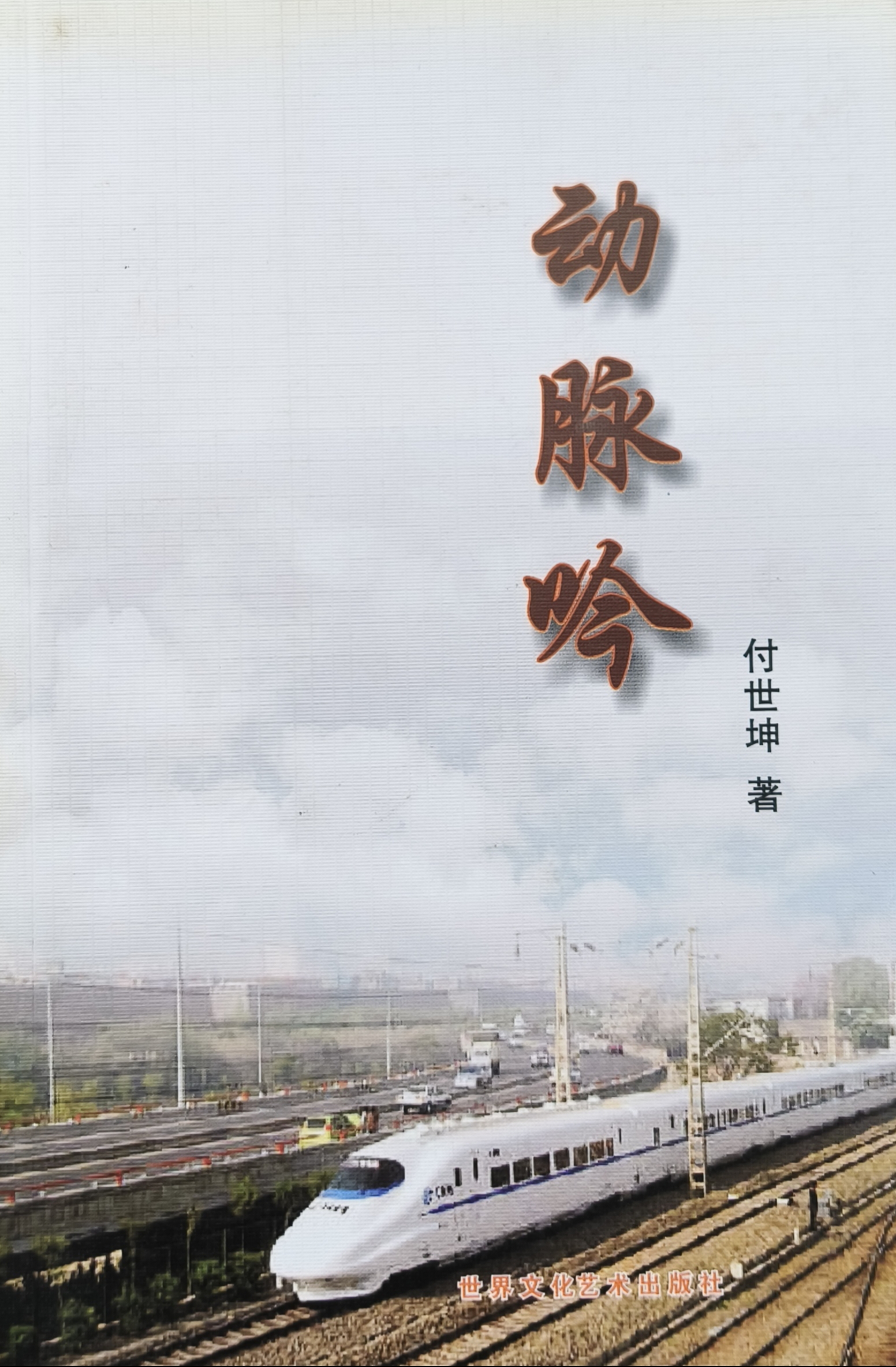
第二部曲:非虚构写作的史诗构建——为复兴历程立传

然而,激情的咏叹之后,必然是深沉的思考。随着记者身份的深化,视野的拓宽,我不再满足于用诗歌的意象去“感受”时代,而是渴望用更坚实、更详尽的笔触去“记录”时代,去探究奇迹背后的血肉与灵魂。这一转变,标志着自己从一位时代的歌者,成长为一位历史的书记官。非虚构写作“三部曲”的诞生,便是这一自觉的产物。
《脉动长轨》是这一转型的基石。它将散见于报刊的关于劳动模范、英雄人物的报道集结成册,这看似是一次简单的整理,实则是一种深刻的再创造。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系统性、集中性地呈现一个行业(铁路)的英雄谱系,其本身就是一种宏大叙事。它回答了“中国名片”何以炼成的问题——不是冰冷的钢铁与水泥,而是无数个有名字、有故事、有温度的个体,用他们的智慧、汗水与奉献,共同铸就了从“跟跑”到“领跑”的传奇。这本书,是为中国制造业脊梁立下的一部“集体传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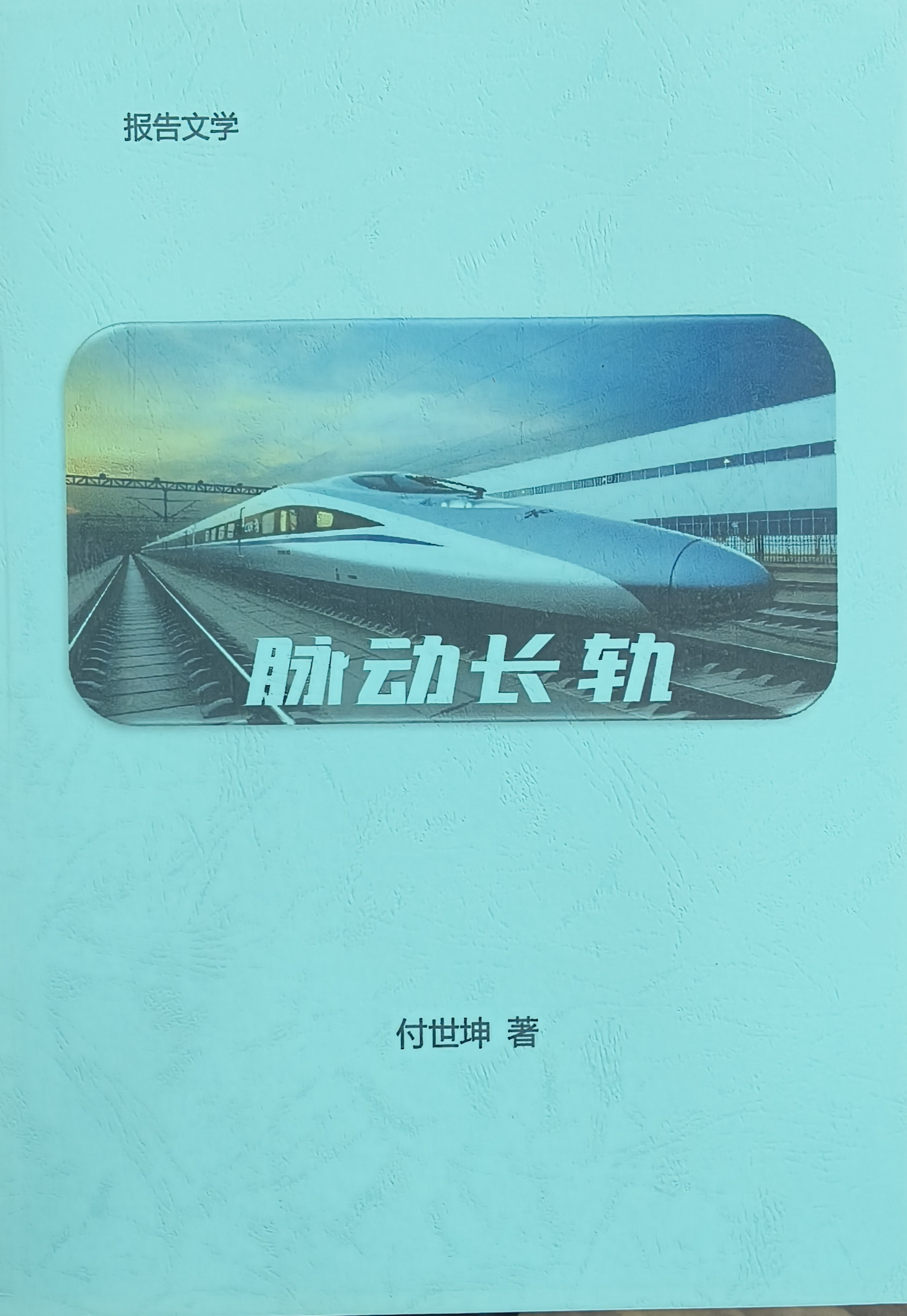
如果说《脉动长轨》聚焦于和平建设的英雄,那么《铁血长歌》则回溯了民族危亡时刻的英雄。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从对陈绍富这位夜袭阳明堡英雄的个案采访,扩展到对一段壮阔历史的书写,这体现了自己作为记录者的历史敏感性与责任感。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让教科书上的战役变成了可触摸的个人史诗。亲手炸毁两架日机的排长,他的恐惧、勇敢、智慧与胜利,构成了历史最鲜活的肌理。《铁血长歌》是对一段正在远去的民族记忆进行抢救性打捞,是以文字为牺牲者与奋斗者树立的丰碑,它与《脉动长轨》一脉相承,共同勾勒出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精神谱系。

而《警笛长鸣》的诞生,则将非虚构写作推向了思想的巅峰。由新华社重磅文章《思想殖民》生发开去,创作出60篇文章、30余万字的解析,这已然不是简单的评论,而是一场系统性的、建立在长期新闻斗争实践之上的理论构建。作为在意识形态领域一线战斗的记者,对“认知战”、“心战”有着切肤之感。这部作品,将多年观察、思考与斗争经验的一次总爆发。它如同一座精神的瞭望塔,清晰地指出了民族复兴之路上,除了有形的“卡脖子”技术,更有无形的“卡脑子”的思想殖民风险。它为自己的前两部非虚构作品提供了深邃的时代注脚:经济的腾飞与国防的强大,必须配以思想上的清醒与坚定,否则一切繁荣都可能成为沙上之塔。

嬗变与交响:从“我”的感动到“我们”的证言

纵观这跨越三十年的两个“三部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嬗变的主线:
视角上,从“我”的抒情到“我们”的叙事。 长诗三部曲中,充满了“诗兴大发”、“情不自禁”、“非常感动”等个人化的情感喷涌。而非虚构三部曲中,作者的身影退居幕后, 劳模的事迹、英雄的战功、思想的辨析,写作者成为了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冷静的分析者和时代的代言人。
文体上,从“诗”的凝练到“史”的丰赡。 诗歌以意象和节奏取胜,追求的是艺术的真实与情感的浓度;非虚构以事实和逻辑为骨架,追求的是历史的真实与思想的深度。这一转变,是创作主体对表现对象复杂性、深刻性认识的必然结果。
功能上,从“审美”的咏叹到“立言”的担当。 长诗旨在感动人心,激发豪情;非虚构旨在记录真相、启迪民智、警示未来。后者更直接地承袭了中国文人“文以载道”、“为天地立心”的传统,体现了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然而,二者并非割裂,而是一场深刻的交响。长诗时期的浪漫主义情怀与宏大视野,为非虚构写作注入了磅礴的气势与温暖的底色;而非虚构写作的严谨求实与深刻思辨,又反过来为早期的诗歌赋予了历史的纵深感。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创作生态系统。
结语:给时代一个交代

万行叙事长诗三部曲、百万余字的非虚构写作三部曲,是想“给这个时代,给我们所见证的伟大的民族复兴,给自己一个交代,给社会一个交代,给时代一个交代。”这掷地有声的话语,想道出的,是一位时代亲历者与记录者的全部初衷。
从聆听九龙坡的童谣,到解析全球性的思想殖民,其笔触跟随国家的脚步,从地方走向全国,从历史走向当下,从经济基础走向上层建筑。“三部曲”嬗变,正是中国从积贫积弱到伟大复兴的历程在个人精神世界中的深刻投影。用诗歌为巨变的年代定格了情感的标高,又用非虚构为奋进的民族雕刻了精神的群像与思想的盾牌。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创作总结,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献给时代的“证言”。它告诉我们,民族的复兴,既需要《脉动长轨》上飞驰的钢铁巨龙,也需要《铁血长歌》中传承的不朽英魂,更需要《警笛长鸣》所呼唤的清醒与睿智。在这条从诗境通往史境的道路上,也许,自己完成了一位歌者与史家的光荣远征。
但愿如此!是为之记。#MCN微头条伙伴计划##认证作者激励计划#(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