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血溅含仁殿!宇文宪跪地求生,亲哥皇帝递来“投名状”
我叫宇文宪,字毗(pí)贺突。
公元572年,含仁殿的血腥味,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我一路小跑,进了殿门,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帽子一甩,头磕(kē)得邦邦响。
“臣,宇文宪,救驾来迟,罪该万死!”

忠诚、谨慎的北周齐公宇文宪
没办法,臣服姿态得做足。
我那四哥皇帝,宇文邕(yōng),刚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把权倾朝野十五年、废立过三位皇帝的堂兄宇文护给宰了。
这事儿办得那叫一个干净利落,前一秒宇文邕还在怂恿堂兄宇文护念叨《酒诰(gào)》,劝太后少喝酒,后一秒四哥就抄起玉珽(tǐng),往宇文护后脑勺上招呼。
我估摸着,这会儿殿里除了血腥味,应该还有点脑浆的味道。
我趴在地上,大气不敢喘,心里却在疯狂盘算。
宇文护,我名义上的领导,实际上的大老板,就这么没了。

被宇文邕杀掉的北周权臣宇文护
这对我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按理说,我一直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干将,他要搞什么动作,基本都派我出马。
可以说,我是他权力版图里最重要的一块拼图。
现在他倒了,我这个“护党”头号干将,会不会被我那皇帝四哥顺手一波带走?
“老五,起来吧。”
头顶上传来一个平静的声音,是我四哥宇文邕。
我哆哆嗦(duō suo)嗦地抬起头,正好对上他那张波澜(lán)不惊的脸。
他身上还穿着常服,看样子刚动完手,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我心里咯噔(gē dēng)一下,这哥们儿心理素质也太强了,刚亲手干掉一个权臣,现在跟没事人一样。
“地上凉,别跪着了。”他又说了一句。
我赶紧爬起来,但腰还是弓着,头也不敢抬,活像个受了惊的鹌鹑(ān chún)。
“四哥……不,陛(bì)下,臣弟……”我结结巴巴,不知道该说啥。
“天下,是太祖(宇文泰)的天下。”
宇文邕缓缓开口,声音低沉,却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我不过是代为看管这份家业,每天都怕把它给弄丢了。”
他顿了顿,向前踱(duó)了两步,绕到我跟前。
“宇文护那家伙,眼里没有君王,心里没有社稷(jì),迟早要谋反。
我杀他,是为了保住咱们宇文家的江山,是为了天下太平。
你我兄弟同气连枝,荣辱与共,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谢什么罪?”
我听着这话,心里稍微松了口气。
看样子,暂时是安全的。
不过,混迹朝堂这么多年,我早就练就了一身听话听音的本事。
我四哥这话,表面上是安抚我,实际上是在敲打我。
“你我兄弟同气连枝”,潜台词是:你最好拎(līn)得清,咱俩才是亲兄弟,宇文护那是外人。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潜台词是:以前你跟他混,我可以既往不咎(jiù),但从今天起,你得站对队。
我脑子飞速运转,立刻摆出最诚恳的表情:“陛下圣明!臣愚钝,只知为大周效力,全凭陛下差遣(qiǎn)!”

亲政后乾纲独断的北周武帝宇文邕
四哥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扔给我一个重磅(bàng)炸弹。
“行了,别在这儿杵(chǔ)着了。你去趟晋国公(宇文护)府,把他的兵符、印信、账本、文书什么的,都给收回来。”
我一愣,去抄宇文护的家?
这活儿可不好干。
宇文护党羽众多,府里更是戒备森严,我这么大摇大摆地去,万一他那些死忠粉脑子一热,把我给剁(duò)了,我找谁说理去?
但转念一想,这又是四哥给我的一个考验。
他这是在看,我敢不敢跟宇文护彻底划清界限。
也是在向朝野上下宣告:看,宇文宪已经是我的人了。
我深吸一口气,把心一横。
干了!
富贵险中求!
“臣,遵旨!”
2.致命抄家行动:宇文宪孤身闯龙潭,心跳飙到嗓子眼!
从皇宫出来,我直奔宇文护的晋国公府。
一路上,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我甚至在想,要不要先回家写封遗书,万一真交代在那儿了,也好让我家那几口子知道我的银行卡密码……哦不,是家产藏(cáng)在哪儿。
到了晋国公府门口,果然,黑压压的甲士们,把大门堵得水泄不通,一个个凶神恶煞(shà),刀枪出鞘(qiào),那架势,活像要跟谁拼命。
领头的是宇文护的心腹大将,瞅(chǒu)见我来了,横刀立马就把我拦下了。
“齐公,晋国公府乃禁地,无晋公手令,任何人不得擅(shàn)入!”
我勒(lè)个去,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晋公手令?
你家晋公的脑袋都快被我四哥当夜壶了。
我清了清嗓子,从怀里掏出我四哥刚给我的手谕(yù),往前一递。

心存社稷的齐公宇文宪
“奉陛下旨意,前来查收晋国公府兵符文书,尔等还不速速让开?”
那将军接过手谕,扫了一眼,脸上露出不屑的冷笑:“陛下?我等只认晋公,不知陛下!”
嗬,真跋扈(bá hù),真是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才!
看来这是要造反啊!
我心里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脸上却还得保持镇定。
“大胆!
晋国公宇文护图谋不轨,已被陛下就地正法!
尔等身为大周将士,食君之禄,竟敢抗旨不遵,是想跟着他一起陪葬(zàng)吗?”
我这番话义正言辞,斩钉截铁。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luǎn)用。
那帮甲士非但没退,反而“唰(shuā)”的一声,刀剑全都对准了我。
气氛瞬(shùn)间降到了冰点。
我感觉我的后背已经湿透了。
完犊(dú)子了,今天真要交代在这儿了。
我那还没出生的娃,怕是见不到他英明神武的爹了。
就在这千钧(jūn)一发之际,我灵机一动,想起了我四哥的性格。
他这个人,隐忍十二年,将宇文护一击必杀,说明他谋划周密,绝不会打无准备之仗。
他让我来,肯定给我留了后手。
后手在哪儿呢?
我眼珠子一转,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好!很好!你们都是晋公的好走狗!”
那将军被我笑得一愣(lèng):“你笑什么?”
我止住笑,指着他,一脸“我看穿你了”的表情。
“我笑你们死到临头,还不自知!
你们以为,陛下会没料到你们会抗旨吗?
你们以为,就凭你们这几百号人,就能翻了天?”
我一边说,一边往后退了两步,扯着嗓子对着周围的街巷(xiàng)大喊:“埋伏在四周的禁军兄弟们,都出来吧!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天罗地网!”
我喊得那叫一个气沉丹田,声震四野。
其实,我哪儿知道有没有禁军。
我这就是在赌(dǔ),赌我四哥办事靠谱。
然而,周围却静悄悄的,连个鬼影都没有。
我心里凉了半截(jié)。
四哥,你玩我啊!
那将军脸上的嘲讽更浓了:“齐公,别演了,就你一个人,还想诈唬(hǔ)我们?”
我额头的冷汗都快流到下巴了。
就在我准备破罐(guàn)子破摔,跟他们拼了的时候,异变突生!
只听“嗖嗖嗖”几声,从街对面的屋顶上,射下来几支箭,正好钉在那将军脚前。
紧接着,四面八方的房顶上、巷子口,冒出来无数个弓箭手,张弓搭箭,箭头闪着寒光,齐刷刷地对准了府门口的甲士。
我当时激动得差点哭出来。
四哥!你果然是我亲哥!
府门口的甲士们瞬间傻眼了,一个个脸色苍白,手里的刀都快握不住了。
我趁热打铁,再次大喝一声:“放下武器,跪地投降,可免一死!否则,格杀勿论!”
“哐(kuāng)当”、“哐当”……
兵器落地的声音此起彼伏。
刚才还嚣(xiāo)张得不可一世的将军,第一个跪了下来,把头埋得比我膝盖还低。
我长舒一口气,整了整衣冠,昂首挺胸地走进了晋国公府。
哈哈,当反派的感觉,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
3.百官之首?烫手山芋!宇文宪喜提“空壳”大冢宰,秒变高级传声筒
抄家的过程,远比我想象的要顺利。
兵符、印信、官防、簿(bù)册……我一样一样清点,装箱,贴上封条。
整个晋国公府,除了哭哭啼啼(tí)的家眷(juàn),再没人敢出来放个屁。
忙活了大半天,总算把事情办妥了。
我带着人,拉着几大车的“战利品”,浩浩荡荡地回宫复命。
一进殿,我就看见我四哥正坐在那儿批阅奏章。
他换了身龙袍,看起来神清气爽,仿佛刚才那场血腥政变只是一场无关紧要的下午茶。
“办妥了?”他头也没抬地问。
“回陛下,幸不辱命。”我躬身答道。
“嗯。”他应了一声,然后提笔在奏章上写了几个字,这才抬起头看我。
“从今日起,你就是大冢宰(zhǒng zǎi)了。”
“啊?”我当时就惊呆了。
大冢宰,那可是百官之首,相当于丞相。
宇文护之前就坐在这个位置上,总领全国军政大权。
我四哥这是什么操作?
刚拔了一棵(kē)萝卜,就把我这个萝卜苗栽进了同一个坑里?
他就不怕我步宇文护的后尘,成为下一个权臣?
我连忙推辞:“陛下,万万不可!臣才疏学浅,德不配位,恐难当此大任!”
这不是谦虚,这是真心话。
这位置太烫屁股了,谁坐谁倒霉(méi)。
“我说你行,你就行。”宇文邕的语气不容置疑,“朕相信你。”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再推辞就是不识抬举了。
“臣……谢陛下隆恩!”我只能硬着头皮接下这个烫手山芋(yù)。
然而,我很快就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这个大冢宰,当得那叫一个憋屈。
四哥自从亲政之后,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
以前宇文护当政的时候,朝廷大事基本都是我们几个核心成员开个小会就定了。
现在倒好,我这个大冢宰,每天的工作就是把我四哥的决定,原封不动地传达下去。
说白了,我就是个高级传声筒。
不仅如此,我四哥对我这个亲弟弟,也开始变得“刻薄”起来。
以前我跟宇文护关系好,他有什么事想跟我四哥说,又怕我四哥不高兴,就经常让我去传话。
我呢,为了不让他们俩起冲突,每次都得绞尽脑汁,把宇文护那些不着四六的话,包装得冠冕(miǎn)堂皇,听起来像是那么回事。
比如,宇文护想给自己加封,原话可能是:“老子功劳这么大,也该当个王了吧?”
我把话传到我四哥那儿,就变成了:“晋公体恤(xù)圣躬,愿为陛下分忧,镇抚四方,以安社稷,恳请陛下恩准,以便行事。”
我自以为我这和事佬当得不错,两边都不得罪。
可我四哥心里跟明镜似的,他早就看穿了我的小把戏。
现在宇文护倒了,他开始跟我算旧账了。
虽然他嘴上没说,但行动上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给了我大冢宰的虚名,却把我手里的实权一点点收了回去。
我感觉自己就像个被架在火上烤的傀儡(kuǐ lěi),名头响亮,实际上啥也不是。
唉,伴君如伴虎,古人诚不欺我。
尤其这只老虎,还是你亲哥。
4.隔空刀光!皇帝借他人之口警告宇文宪:君臣有别,莫念兄弟情
就在我每天顶着“大冢宰”的名头,干着秘书的活,郁闷得快要怀才不遇的时候,我四哥又出招了。
他把我府上的侍读,开府裴文举,给叫到宫里去了。
裴文举是我的人,专门负责给我讲经读史,顺便帮我分析分析朝堂局势。
我四哥召见他,这信号可不一般。
裴文举从宫里回来,脸都白了,一进门就拉着我,神神秘秘地把我拖到书房。
“公爷,陛下他……”
“他怎么了?是不是要削我的爵位了?”我心里一紧。
“那倒没有。”裴文举咽了口唾沫,把宇文邕对他说的话,原原本本地复述了一遍。
我四哥的原话,翻译过来大概是这个意思:
“小裴啊,宇文护那小子想造反,这事儿满朝文武都知道。我哭着杀他,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你懂的吧?”
“想当年,我们老宇文家帮着西魏元家打天下,后来取而代之,宇文护又学着我爹的样子,把持朝政。
这都成惯例了,好像皇帝就该是个摆设。
开什么玩笑?
我今年都三十岁了,还能让人当提线木偶吗?”
“还有个坏毛病,得改!
就是某些人啊,给谁当过几天手下,就跟认了个爹似的,主子奴才分得比谁都清。
这是乱世的规矩,不是治国的道理。
《诗经》里说了,‘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这‘一人’,指的就是我,天子!不是你家齐公!”
“我爹生了十个儿子,难道个个都能当皇帝吗?
你回去好好劝劝你家主子,让他摆正自己的位置,懂点规矩,咱们兄弟俩好好过日子,别一天到晚让我猜忌他。”

开创北周的太祖宇文泰
听完裴文举的转述,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出话来。
我四哥这番话,简直就是把刀子捅到我心窝子里了。
句句不提我,又句句都在说我。
什么“暂经隶属,便即礼若君臣”,不就是在敲打我以前跟宇文护走得太近吗?
什么“太祖十儿,宁可悉为天子”,不就是在警告我,别以为你也是宇文泰的儿子,就有什么非分之想吗?
什么“辑睦(jí mù)我君臣,协和我骨肉”,这哪里是君臣骨肉?
这分明是让我老老实实当他的臣子,别总拿骨肉亲情说事儿!
我后背一阵发凉。
我这个四哥,太可怕了。
他不仅杀伐果决,心机更是深沉如海。
他这是在通过敲打裴文举,来警告我啊!
裴文举看我脸色不对,小心翼翼地问:“公爷,您……”
我抬起手,指了指自己的心口,然后又拍了拍面前的桌案,长叹一口气。
“我的心,难道你还不清楚吗?除了尽忠报国,我还能说什么呢?”
还能说什么?
我什么都不能说。
在绝对的皇权面前,任何解释都是苍白的,任何辩解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夹起尾巴做人,当一个让他放心的“忠臣”。
只是,这君臣兄弟的滋味,怎么就这么不是个味儿呢?
我看着窗外,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心里却比这夜色还要沉。
我这位皇帝哥哥,他的猜忌,真的会因为我的“忠心”而停止吗?
还是说,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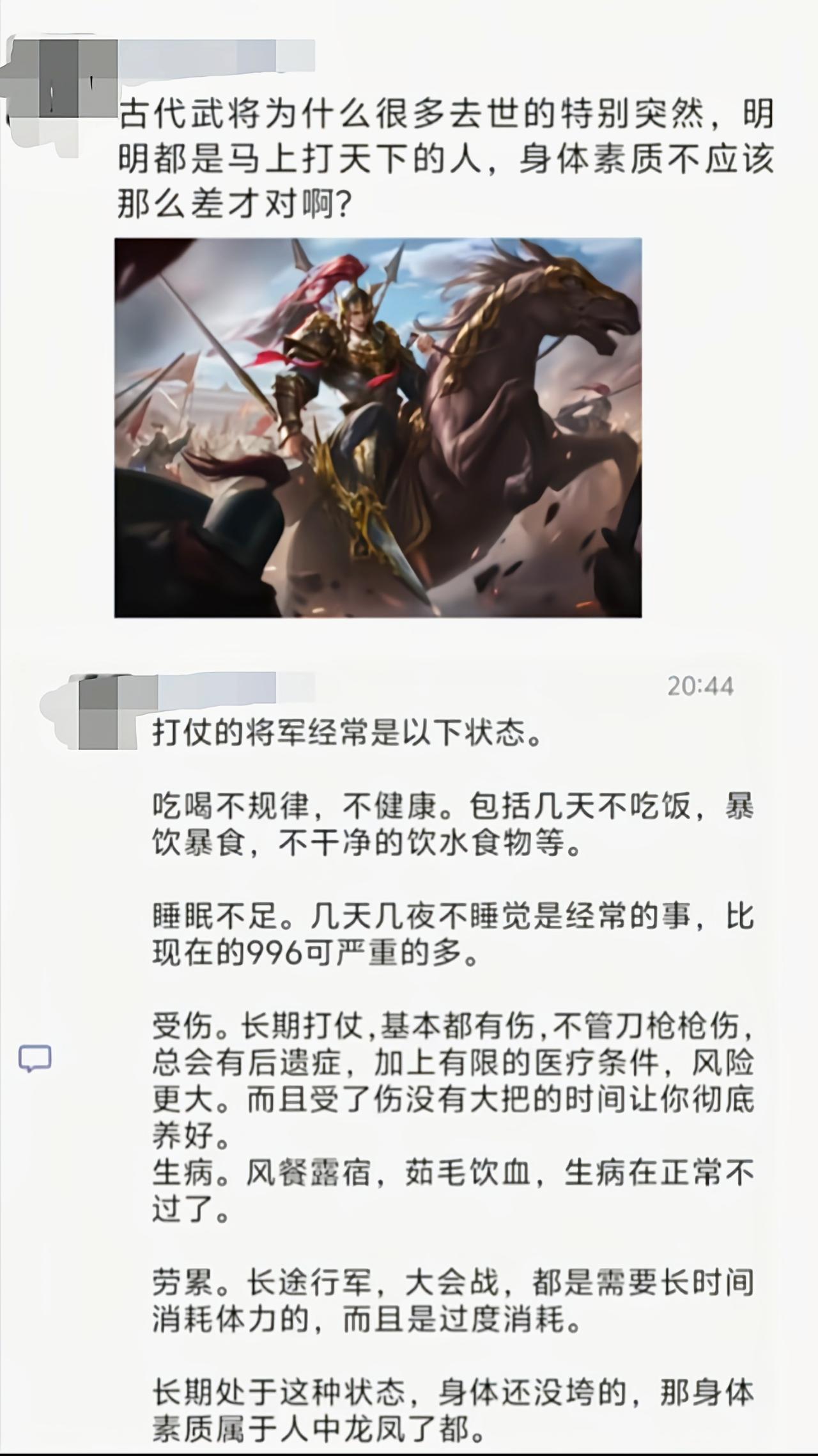



![司马懿要是死前说这种话的话,手下人应该会怀疑他是诈死,边上埋伏了刀斧手。[捂脸哭]](http://image.uczzd.cn/9431401115458828965.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