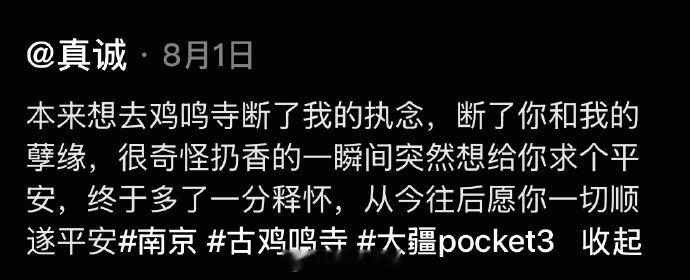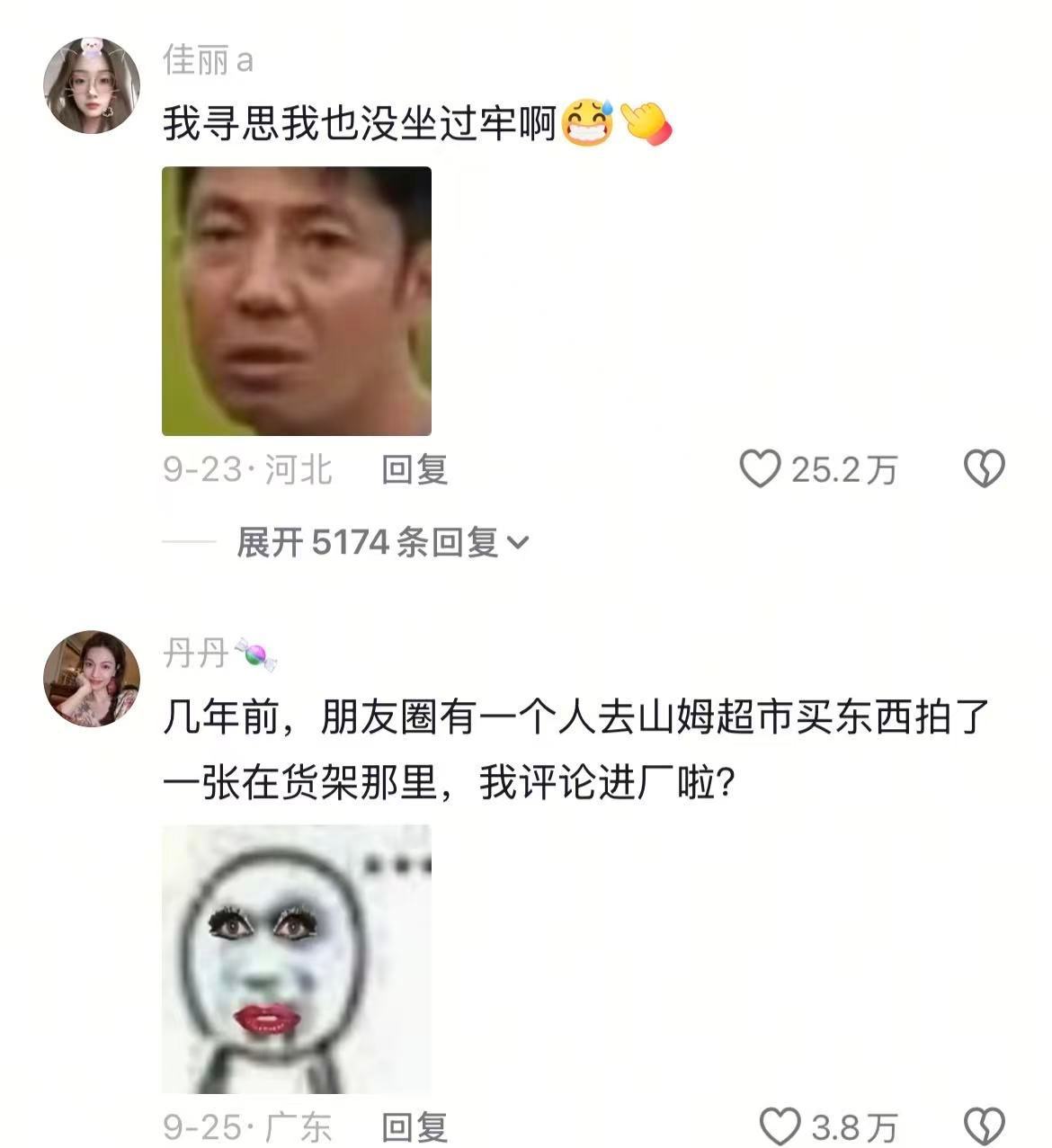1914年暮春的东京,上野公园的樱花正落得细碎。二十出头的郭沫若穿着洗得发白的学生服,手里攥着一封从四川乐山寄来的家书,信纸边缘被反复折叠磨出了毛边,上面有弟弟歪歪扭扭的字迹:“哥,今年春汛大,咱家两亩水田淹了,娘夜里总起来看天。”风裹着樱花瓣贴在他的袖口,他抬手去拂,指腹却蹭到了信纸上火烫的墨迹——那是母亲补写的一句“勿念家,先把书念好”。他望着远处东京塔模糊的轮廓,喉结动了动,把家书塞进怀里贴紧胸口,像是要接住千里之外母亲的叹息。身后传来留学生们讨论“实业救国”的声音,他却忽然觉得,这满树樱花再美,也盖不住心里那点空落落的慌。

1914年秋,郭沫若踏进东京帝国大学医科的课堂,书包里除了医学课本,还塞着一本手抄的《离骚》。彼时的中国,刚从辛亥革命的浪潮里缓过神,又陷在军阀混战的泥沼里,无数青年像他一样漂洋过海,想把“救国”的希望缝进知识里。他选医学,是因为在乐山老家时,见过太多乡亲因为没钱治病眼睁睁熬死,可第一堂解剖课上,当冰冷的手术刀划开标本时,他却突然想起母亲说的“救人先救心”。夜里他住在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墙上贴满了用毛笔写的诗句,煤油灯的光把那些字迹映在墙上,像跳动的火苗。有次背书到深夜,他手指无意识地抠着墙皮上的裂纹,忽然在日记本上写下:“医人,能治皮肉之痛;医国,要醒千万人之心——这刀,或许该换种用法。”后来他在《我的学生时代》里回忆这段日子,说“那些夜里的煤油灯,烧的不是煤油,是心里没处放的劲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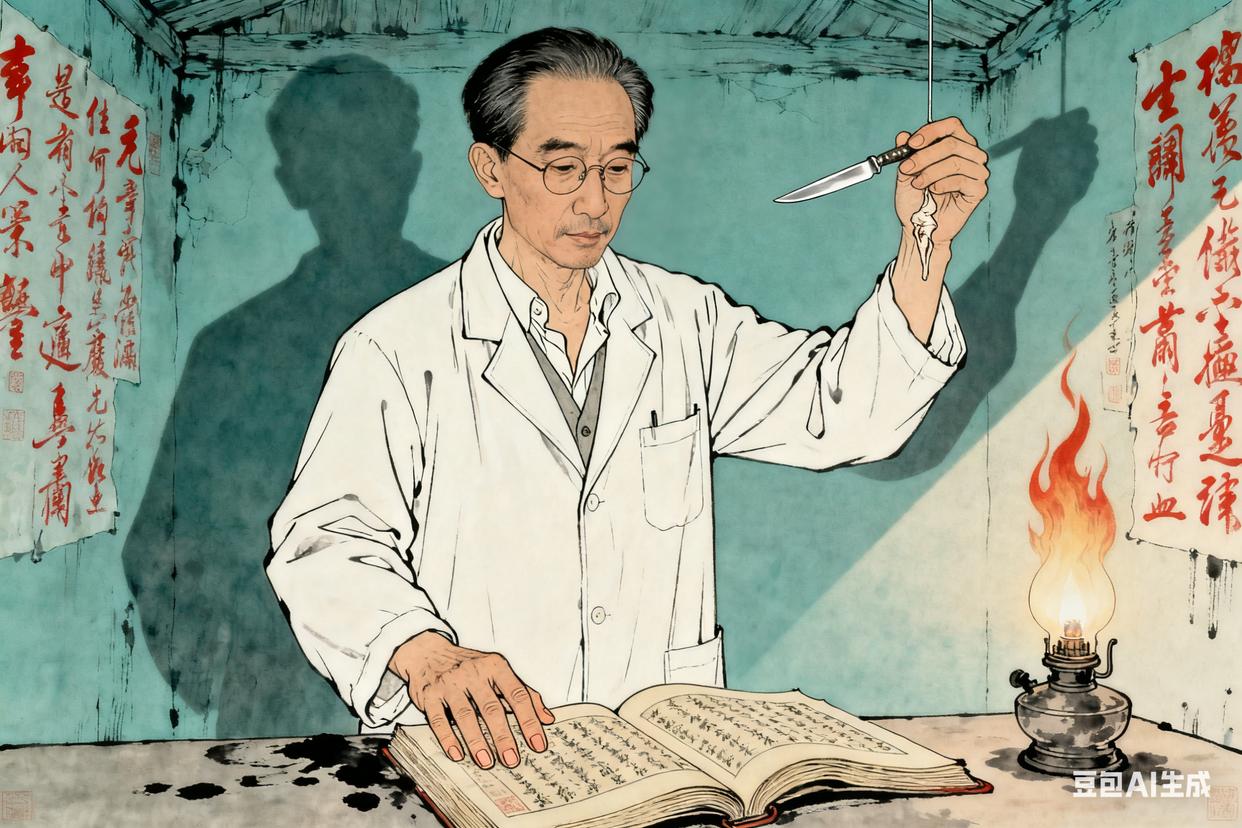
1919年五月,五四运动的消息顺着海底电缆传到东京时,郭沫若正在出租屋里改诗。窗外的蝉鸣聒噪得厉害,他手里的钢笔突然顿住——报纸上“还我青岛”的黑体字像针一样扎眼睛。那天夜里,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桌上摊着几张写满诗句的纸,钢笔没水了就换蘸水笔,墨水溅在稿纸上,晕开一个个深色的圈。他写凤凰自焚,写群鸟乱舞,写“我们生动,我们自由,我们雄浑,我们悠久”,写到激动处,拳头砸在桌角,震得墨水瓶晃了晃。天快亮时,他终于写完《凤凰涅槃》的最后一句,推开窗,看见楼下几个中国留学生举着“废除二十一条”的标语在游行,他们的嗓子已经喊哑了,却还在一遍遍地喊。郭沫若摸着稿纸上未干的墨迹,忽然觉得这些文字不是写出来的,是从心里“烧”出来的——“这诗该像火把,能照亮那些黑沉沉的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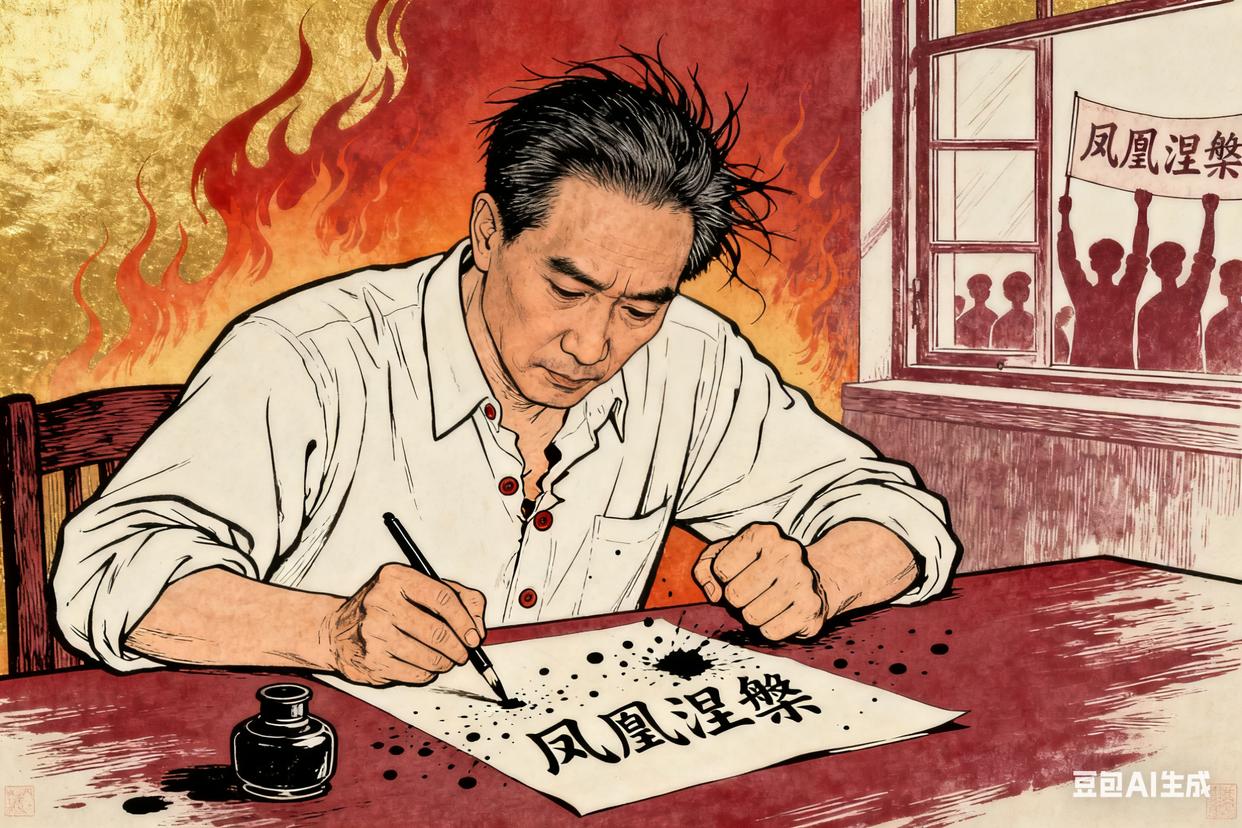
1921年夏天,上海泰东图书局的编辑把一本样书递到郭沫若手里时,他正坐在弄堂口的石阶上吃包子。书的封面是暗红色的,印着“女神”两个字,扉页上有编辑的铅笔批注:“此作当惊世,只是怕读者受不住这股烈劲儿。”他捏着书脊,指尖蹭过粗糙的纸页,突然想起在日本没钱买稿纸的日子,常把商店包东西的牛皮纸裁开写字,那些纸页上还沾着酱油或糖霜的痕迹。有个学生后来写信给他,说“读《女神》时,感觉心里有团火被点着了,想站起来做点什么”,他把信压在书桌玻璃下,旁边放着那支写《凤凰涅槃》时用的蘸水笔,笔杆上还留着他当年咬过的牙印。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这本诗集会成为中国新文学的里程碑,就像他不知道,自己后来会从“写诗的人”,变成“挖历史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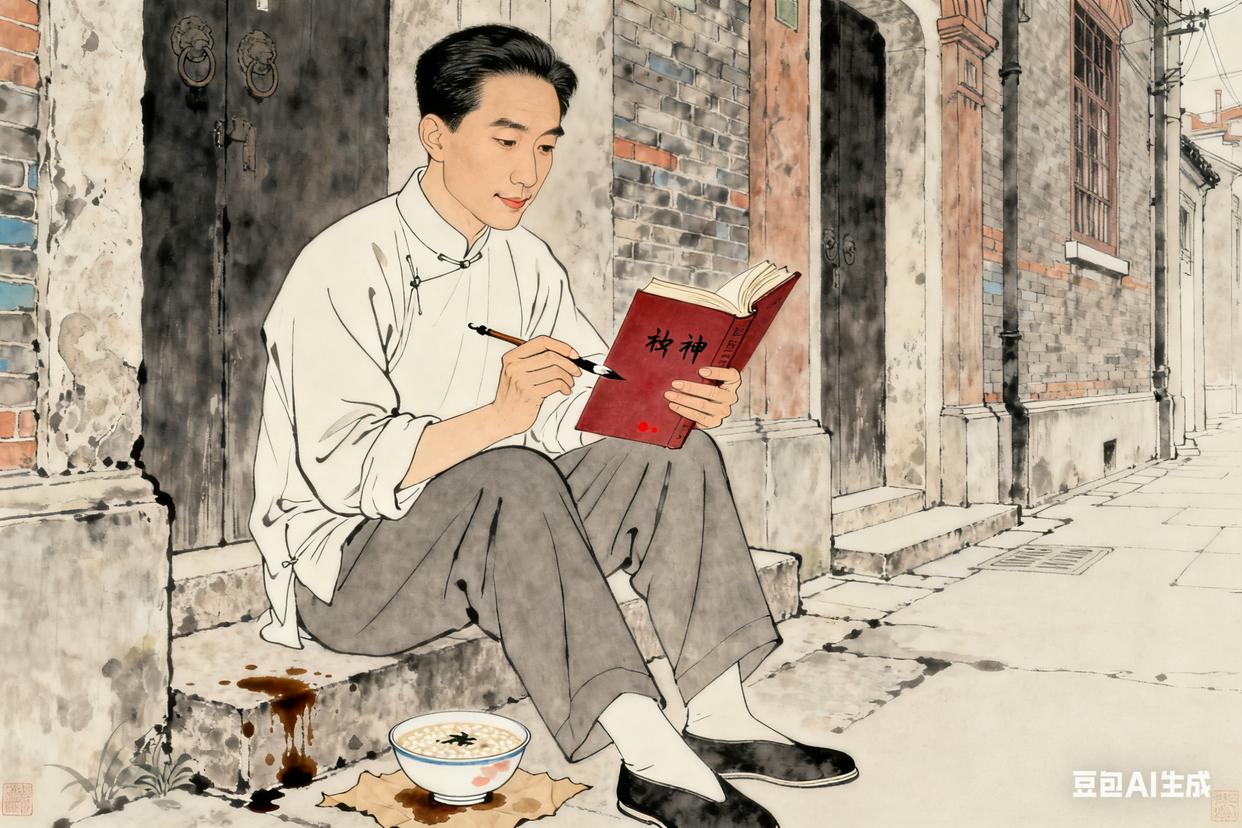
1926年的春天,广州的木棉花正开得热烈。郭沫若穿着国民革命军的制服,坐在颠簸的军车上,手里拿着一张没写完的宣传稿。这一年他放弃了日本的学业回国,担任北伐军政治部秘书长,周恩来笑着拍他的肩膀:“鼎堂(郭沫若字),你的笔可比枪杆子厉害。”行军路上遇到大雨,他把油纸伞偏向怀里的文稿,自己的肩膀被淋得透湿,文稿上的字迹却一点没花。到了宿营地,他坐在篝火边烘干文稿,纸页被烤得皱巴巴的,像波浪一样卷起来。他摸着那些皱痕对身边的士兵说:“这皱痕就是咱们走的路,看着难,一步步踩平了,就通了。”后来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以前写诗歌是为了唤醒人,现在写宣传稿,是为了让士兵们知道,咱们为什么而战——为了那些还没见过春天的孩子,为了那些被欺负的乡亲。”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上海的空气里飘着血腥味。郭沫若躲在法租界的一间小阁楼里,桌上放着一本打开的《甲骨文合集》,旁边是半碗凉透的粥。有天夜里,郑振铎来看他,劝他“先避避风头,别再碰这些‘敏感’的东西”,他却指着甲骨上的刻痕说:“你看这字,是三千年前商王刻的,那时候的人也经历过战乱,也盼着太平。我从这些骨头里找的不是字,是咱们中国人的根——根还在,就不怕倒。”他用放大镜一点点看甲骨上的裂纹,手指轻轻蹭过那些古老的刻痕,像是在跟千年前的人对话。阁楼的窗户很小,月光照进来,在桌上投下一块方方正正的亮,他就借着这点光,把甲骨上的字一个个抄在本子上,本子的封皮上写着“守正”两个字,是他用毛笔写的,笔锋很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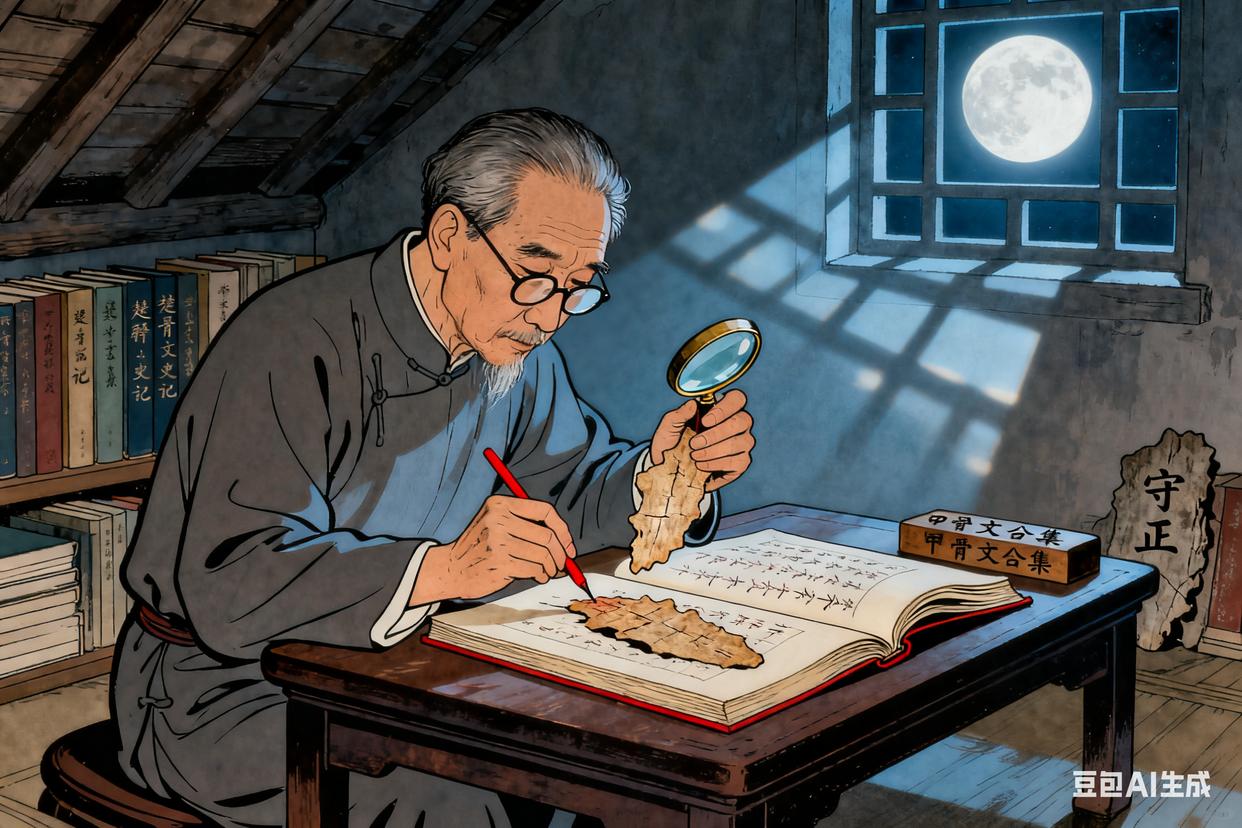
1937年深秋的重庆,防空警报又响了。郭沫若抱着一摞《屈原》的手稿,跟着人群往防空洞跑,跑的时候还在默念台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洞里很暗,有人递给他一支蜡烛,他就坐在冰冷的石头上,膝盖当桌子,继续改稿。铅笔头断了,他就用牙咬尖,墨水不够了,就蘸点自己的唾沫——那时候重庆的物资紧,连墨水都是稀罕物。《屈原》演出那天,台下坐满了流亡学生和工人,当演员念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时,观众们突然鼓起掌来,掌声震得戏台的幕布都晃了晃。郭沫若站在后台,看着台上的灯光,眼眶却有点热——他忽然担心,“这戏里的火,能不能真的烧到外面的黑暗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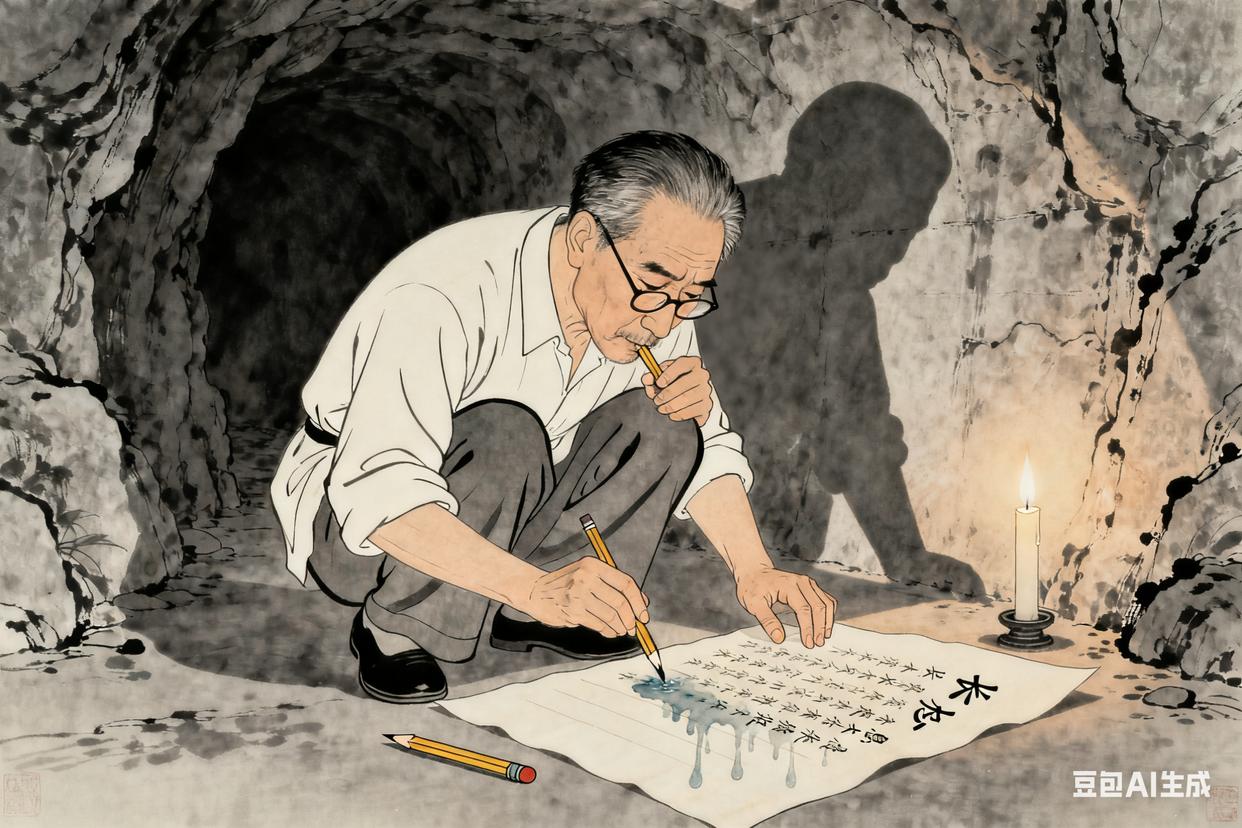
1950年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探方边挤满了考古队员。已经五十多岁的郭沫若蹲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把小刷子,正一点点清理一块甲骨上的泥土。他没戴手套,指甲缝里全是黄褐色的土,队员递给他一块湿巾,他摆手说:“戴着手套没感觉,摸不到老祖宗的温度。”太阳快落山时,有个年轻队员喊:“郭老,您看这个!”他跑过去,看见探方里躺着一块巴掌大的甲骨,上面刻着几个清晰的字——“王亥”。那是商王的名字,是甲骨文里最早记载的商王之一。他蹲下来,用放大镜仔细看,声音都有点发颤:“找着了,咱们找到实证了!这不是传说,是真真切切的历史!”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探方里,和那些三千年前的甲骨叠在一起,像一场跨越时空的握手。

后来有人问郭沫若,这辈子最骄傲的是什么?他没说《女神》的轰动,也没说考古的突破,只说“我没辜负那些日子——樱花树下想家的日子,防空洞里写戏的日子,探方边刷泥土的日子”。现在去中国国家博物馆,还能看到他当年用的那支蘸水笔,笔杆上有他咬过的痕迹,墨水早已干涸,却像还藏着当年的温度;还有他改《屈原》时的手稿,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涂改,有一处甚至被眼泪洇得模糊——那是写“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时,他想起了重庆防空洞里挨饿的孩子。如今的年轻人去安阳殷墟参观,站在玻璃展柜前看那些甲骨时,或许会想起有个老人,曾用一辈子的时间,把诗的火、史的根,种进了华夏的土壤里。就像他当年说的:“咱们中国人的根,不在书里,不在嘴里,在那些能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里——是甲骨上的字,是诗里的火,是心里的那点不服输的劲儿。”这股劲儿,从樱花树下传到甲骨旁,从过去传到现在,还会接着传下去,像一场永远不会熄灭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