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想明白”比“看见”更重要?
我们每天都在“思考”,或者至少我们是这么认为的。我们思考“午饭吃什么”,思考“那个人为什么看了我一眼”,思考“这个季度的报表是不是又要做得令人头秃”。我们的大脑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念头、图像、声音和感觉。这片喧嚣的内心市场,我们称之为“意识”。
然而,“思考”这件事,可能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我们大多数时候所做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思考”,而是“体验”。我们被动地接收着来自世界的各种“信号弹”——这个红灯很刺眼,那杯咖啡很香,隔壁的装修声很烦。这些都是直观的、个体的、扑面而来的东西。
但“思考”是一种更高级、更主动、也更“偷懒”的活动。它是一个打包、分类、贴标签的过程。

这篇文章,就是想带你深入我们大脑中那个很少有人参观的“归档室”。我们将一起探索,我们到底是如何从“看见这一个”转向“理解这一类”的。我们的目标很简单:搞清楚我们是如何“想明白”一个问题的。这比你想象的要复杂,但好消息是,它也比你想象的要有趣得多。
看见一只狗,与“狗”这个概念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
请你现在立刻在脑海中“想”一个东西。随便什么都行。
好了吗?
你“想”到的,很可能是一个具体的东西。也许是你家那只正在掉毛的金色大狗,它叫“土豆”;也许是昨天你吃的那块特定的、有点凉了的酱香饼;也许是你办公桌上那盆快要枯死的绿植。

这些东西,我们称之为“直观”。
“直观”是一种个体的表象。它是“这一个”。它是此时此地、独一无二、细节丰富的。你家“土豆”的某个傻乎乎的眼神,是它专属的,是“直观”的。你无法把这个眼神原封不动地安在邻居家的哈士奇身上。
现在,我们来做第二个实验。
请你“想”一下“狗”。
不要想“土豆”,就只是“狗”。
你“想”到了什么?
你可能会发现,这变得有点困难。你脑海中出现的,很可能又是一只具体的狗(也许是一张示意图般的狗的剪影),但你立刻会意识到,这只“示意图狗”并不能代表所有的狗。它无法代表哈士奇,也无法代表藏獒。
你所把握到的“狗”这个东西,它没有特定的颜色,没有特定的大小,没有特定的叫声。它不是一个“图像”,而是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可以被贴在“土豆”身上,也可以被贴在哈士奇和藏獒身上。

这个“标签”,就是“概念”。
“概念”是一种普遍的表象,是许多客体所共有的表象。
这就是我们心智活动的两条基本轨道:
直观:个体的、直接的、生动的。它是“这一个”。
概念:普遍的、反思的、抽象的。它是“这一类”。
借助于“直观”的知识,是我们体验世界的方式。借助于“概念”的知识,才是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
所以,当我们说“普遍的概念”时,其实是在说一句废话,就像说“潮湿的水”一样。一个概念,如果它不是普遍的,那它就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它只是一个被误认的“直观”而已。我们不能把“土豆”这个词当作一个概念,它只是一个专有名词,一个指向某个特定直观的“代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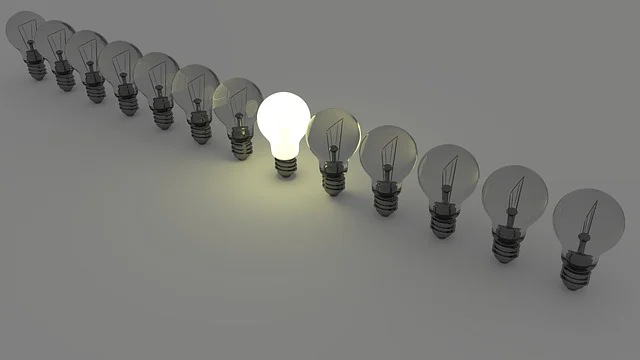
那么,一个概念(比如“狗”)由什么构成呢?
它有两个基本组成部分:
质料:它所指向的对象。也就是那些毛茸茸的、会汪汪叫的动物们。
形式:它的普遍性。也就是它能够作为一个“标签”被到处贴的这个属性。
搞清楚这个区别至关重要。
经验的,还是“脑子自带的”?
我们已经知道了“概念”是普遍的标签。那么,这些标签是哪儿来的?是我们自己印的,还是买来就有的?
这就涉及到了概念的“产地”问题。
经验概念
这是最常见的一类。这类概念的内容,是从经验中“引来”的。
你这辈子是怎么得到“树”这个概念的?
你不可能一出生就知道什么是“树”。你先是看到了一个“直观”(比如你家院子里的那棵大杨树),然后你又看到了另一个“直观”(比如公园里那棵松树),你爸妈指着它们说:“树”。

你看得多了,你的大脑就开始了它的“归档”工作。它发现这些东西虽然长得不一样,但好像都有“根”、“干”、“枝”、“叶”(松树的叶子比较别致,但我们先不管它)。于是,你的知性就把这些共同点提取出来,赋予它们“普遍性”的形式,然后“啪”地一下,盖上一个标签,上面写着:“树”。
这就是一个经验概念的诞生。它的“质料”(内容)来自感官经验,它的“形式”(普遍性)来自你的知性加工。
所以,经验概念的“实在性”,必须以实际经验为基础。你不能凭空“发明”一个经验概念。
纯粹概念
好了,现在问题来了。
“树”、“狗”、“红色”、“桌子”,这些概念的产地都很清楚。
那么,“原因”、“结果”、“实体”、“统一性”、“可能性”……这些概念呢?
请你试着回忆一下,你上一次“看见”“原因”是什么时候?
你可能会说:“我看见了啊!我看见我的手(原因)推动了杯子(结果)。”
不。你“看见”的,是一个“直观”(你的手),紧接着,你“看见”了第二个“直观”(杯子倒了)。你并没有“看见”那个叫做“原因”的、连接在手和杯子之间的神秘力量。

“原因”这个概念,不是你从经验中“抽”出来的,而是你的知性“带”过去,用来“解释”你所看到的直观的。
这类概念,它们的“质料”(内容)并非从经验引来,而是源于知性本身。它们是“纯粹概念”。它们就像是你大脑归档室里预先准备好的一套“文件夹”,专门用来整理那些扑面而来的“直观”文件。没有这些文件夹,你的经验对你来说就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混乱纸片。
理念
还有一类更特殊的概念。它们是“理性”(Reason)的产物,我们称之为“理念”。
“理念”的特点是:它的对象绝不能在经验中遇到。
你永远、永远、永远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直观”到一个“理念”。
比如:
“自由”:你能看见一个人在投票,或者一个人在辞职。但你看不见“自由”本身。
“世界整体”:你可以看见星星、看见地球、看见你邻居。但你永远不可能“看见”——我是说,像看见一个杯子那样——看见“所有事物的总和”。你总能再往外多想一点。
“绝对的完善”:你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好”的人,或者一个“很好吃”的馅饼。但你永远遇不到“绝对完美”的馅饼。

这些“理念”有什么用呢?
它们的作用不是“构成性”的(用来搭建我们对现实的认知),而是“调节性”的(用来引导我们的知性)。
“理念”就像是挂在驴子面前的那根胡萝卜。
“世界整体”这个理念,驱使着科学家不断地去探索更广阔的宇宙,试图把所有经验“联系”起来,达到最完备的统一。
“自由”这个理念,是一切道德法则的基础。它的实在性(虽然无法被“看见”)必须被当作一个公理,否则“责任”、“选择”就都失去了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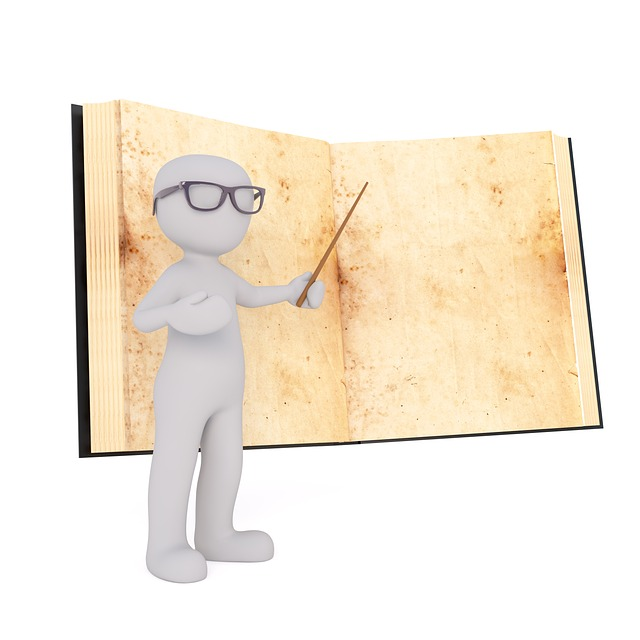
所以,很多人其实并没有关于他们所向往的事物的“理念”。他们只是按照本能和权威在行事。而拥有“理念”,并试图去靠近它,是理性的最高表现。
比较、反思与抽象
好了,我们现在知道了概念有不同的产地。但逻辑学其实不太关心你的原材料是“经验”还是“纯粹知性”。逻辑学关心的是“生产流程”。
它只问一个问题:无论你给我什么表象(直观),你是如何把它加工成一个“概念”(普遍标签)的?
这个加工过程,分为三个核心步骤。这三个步骤,是产生任何一般概念的基本和普遍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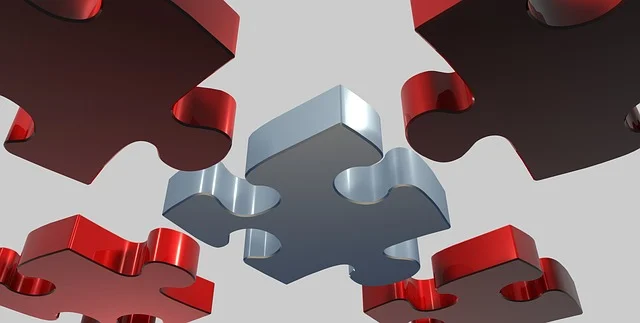
我们来模拟一下这个生产线。
原材料: 假设你是一个原始人,第一次走出山洞,看到了三样东西。
直观A: 一棵松树。(高大、针叶、绿色、摸起来有点刺手)
直观B: 一棵柳树。(柔软、下垂、细长的叶子、在风中摇摆)
直观C: 一棵菩提树。(宽大的心形叶子、夏天很香)
你的大脑现在有三个独立的“直观”文件。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比较
这是第一道工序。知性把这三个“直观”文件A、B、C摆在同一张桌子上。
“嗯,A和B不一样。”
“B和C也不一样。”
“A的叶子是针,C的叶子是片。”
“B的树枝是往下长的,A的树枝是往上长的。”
“它们在干、枝、叶等方面是互不相同的。”

“比较”这个动作,是把诸表象在相互关系中进行比较,目的是为了达到意识的统一(把它们放在“一个”意识里处理)。
反思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在比较了不同之后,知性开始“反思”:“在这些不同之中,我怎样才能把它们把握在一个意识中?”
换句话说:它们有什么共同点?
“虽然A、B、C的‘干’、‘枝’、‘叶’形态各异……但是……”
“它们都有一个‘干’。”
“它们都有‘枝’。”
“它们都有‘叶’(某种形式的)。”
“它们都扎根在土里。”

“反思”就是考虑怎样才能将不同的表象把握在一个意识中。它是在寻找那个“共有的东西”。
抽象
这是最后一道“精加工”工序。知性现在已经找到了“共有的东西”(干、枝、叶本身)。为了制造出“标签”,它必须把所有“多余的”东西都扔掉。
这个工序就是“抽象”。
扔掉松树的“大小”、“形状”、“针叶”这些特殊规定。
扔掉柳树的“下垂”、“柔软”这些特殊规定。
扔掉菩提树的“心形叶”、“香味”这些特殊规定。
知性把所有让它们“互不相同”的东西,统统“抽去”了。

这个过程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我们不能说我们“抽出”了“树干”这个属性。我们只能说,我们“抽去了”所有关于树干的特殊规定(比如“粗糙的”、“光滑的”),只留下了“树干本身”这个普遍特征。
成品出炉:
在经历了“比较”、“反思”和“抽象”之后,你得到了一个全新的东西。这个东西是这三个直观所共有的表象。
这个表象,就是“树”的概念。
“抽象”是概念产生的“消极条件”(它负责扔东西),而“比较”和“反思”是“积极条件”(它们负责找东西)。
现在,你再遇到第四个直观,比如一棵“桦树”。你就不需要再发明一个新词了。你只需把它和你的概念“树”进行比较,发现它也“有干、有枝、有叶”,于是“啪”一声,把“树”这个标签贴上去。

恭喜你,你学会“思考”了。
内涵与外延(本文核心)
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一个强大的工具——概念。但这个工具箱里的工具,规格可大不一样。
比如,“动物”是一个概念。“哺乳动物”是一个概念。“狗”是一个概念。“金毛巡回犬”也是一个概念。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在于,它们所包含的“信息量”和它们能应用的“范围”完全不同。

这就引出了逻辑学中最核心、最美妙、也最实用的一个定律。每一个概念,都有两种“量”:
内涵(Intension):概念“之内”包含的特征。
外延(Extension):概念“之外”能应用的范围。
让我们来详细解剖一下。
内涵
“内涵”是一个概念所包含的“知识的根据”,也就是它的“特征”。简单说,就是这个概念的“定义”。
我们来试着定义几个概念,看看它们的“内涵”:
“物体”的内涵: {可扩展的、有形的、物质的……}
“动物”的内涵: {物体、有生命的、有感觉的、能自主运动的……}
“人”的内涵: {物体、有生命的、有感觉的、能自主运动的、有理性的……}
“哲学家”的内涵: {物体、有生命的、有感觉的、能自主运动的、有理性的、系统性地研究存在与知识的……}

请注意,每往下一步,“内涵”都在增加。
“人”的内涵 = “动物”的内涵 + “有理性的”。
“哲学家”的内涵 = “人”的内涵 + “系统性地研究存在与知识的”。
“内涵”越丰富,这个概念就越“具体”、越“厚实”。
外延
“外延”是一个概念所能“包含于其下”的事物的数量。简单说,就是这个概念能“罩住”多少个体。
我们来看看同样那组概念的“外延”:
“物体”的外延: {石头、桌子、狗、人、星星、水滴……}(一个极其庞大的范围)
“动物”的外延: {狗、人、虫子、鱼、鸟……}(范围缩小了,石头和星星被排除在外)
“人”的外延: {苏格拉底、柏拉图、你、我、隔壁老王……}(范围又大大缩小了,狗和虫子被排除在外)
“哲学家”的外延: {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格尔……}(范围变得非常小)

请注意,每往下一步,“外延”都在减少。
思想的“反比例定律”
现在,把“内涵”和“外延”放在一起看,一个极其优美的“反比例定律”出现了:
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彼此成反比例。
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大,其外延就越小。
反之,一个概念的外延越大,其内涵就越小。
这,就是我们整个思维结构中的“跷跷板”。
“物体”:内涵极小(特征很少),外延极大(能用在几乎所有东西上)。
“哲学家”:内涵极大(特征很多),外延极小(只能用在很少的人身上)。
这个定律解释了我们日常沟通中的许多困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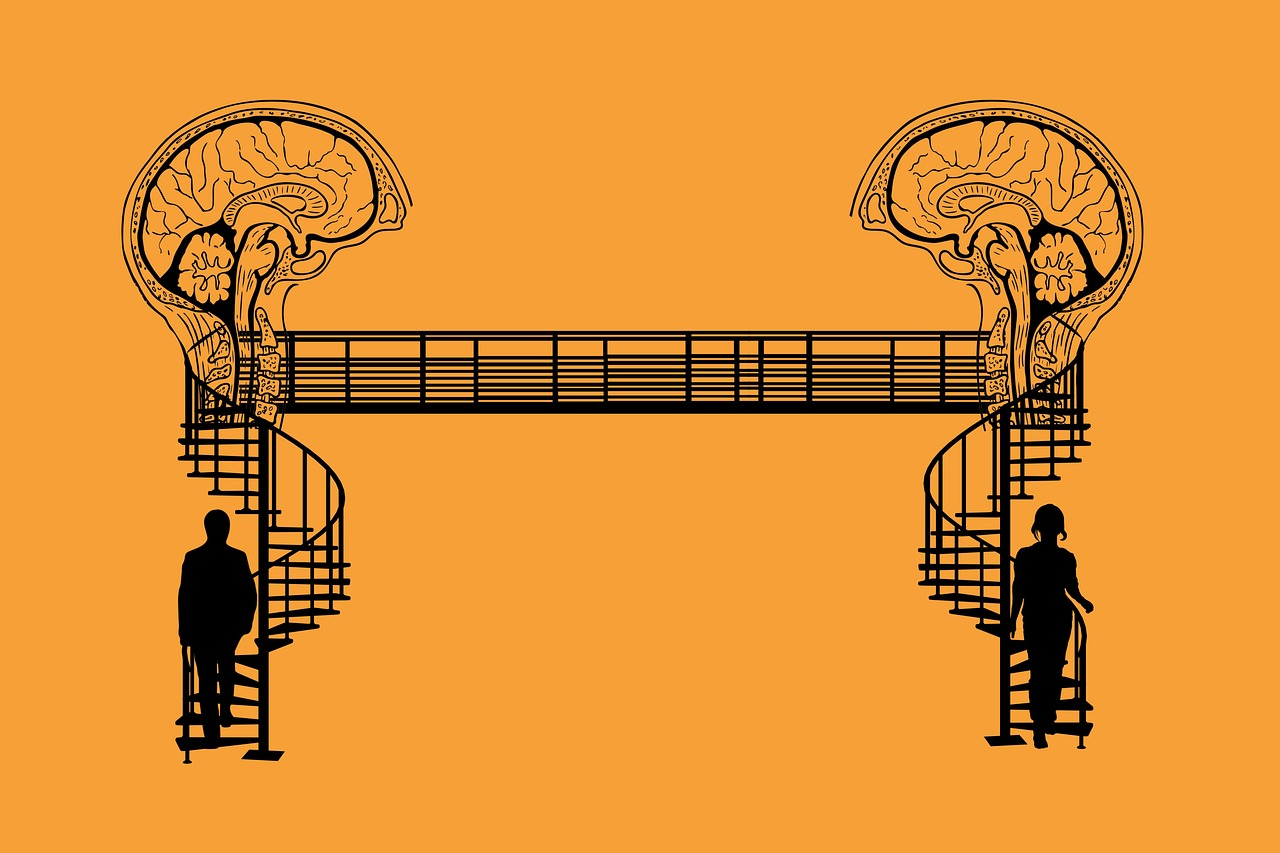
为什么“高谈阔论”总是显得很“空”?
当一个人总是在谈论“存在”、“某物”、“实体”、“精神”、“人民”时,他使用的是“外延”极大,但“内涵”极小的概念。
“某物”这个概念,外延是“一切”,它的内涵是什么?几乎是“零”。与它有区别的东西是“虚无”。
所以,当你用“某物”这个概念时,你“稍知许多事物”(你知道它能用在所有东西上),但你“甚知少数事物”(你对任何一个具体东西的了解,通过这个概念,几乎为零)。
为什么“专家”总是显得很“窄”?
一个研究“15世纪佛罗伦萨特定画派所用蓝色颜料化学成分”的专家,他使用的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极其庞大的概念。
这个概念的“外延”呢?可能小到全世界只有三幅画和一个残片。
他“甚知少数事物”(他对这点东西了如指掌),但他也“稍知许多事物”(你问他关于红色颜料的事,他可能就不知道了)。
我们在一方面得到的,必然在另一方面失去。

这个“内涵/外延反比例定律”,就是我们组织知识、进行分类、建立科学体系的底层架构。
思维的阶梯——属和种
我们现在知道了,概念有大有小(外延),有厚有薄(内涵)。这就自然而然地在我们的思维中,形成了一个“阶梯”或者说“金字塔”结构。
这个结构,就是“属”和“种”的关系。
较高概念称为属。
较低概念称为种。
例如:
“动物”是“人”的属。
“人”是“动物”的种。
这两个词,是逻辑学里最古老、最重要的一对“关系户”。但请注意,它们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一个概念可以在不同的关系中,既是“属”又是“种”。
“人”:相对于“动物”时,它是“种”。
“人”:相对于“学者”时,它又是“属”。
这个阶梯可以一直往上爬,也可以一直往下走。
向上爬:抽象的阶梯
我们来试着往上爬:
“苏格拉底” (这是直观,不是概念)
...
“哲学家” (种)
“学者” (属 / 种)
“人” (属 / 种)
“动物” (属 / 种)
“有机体” (属 / 种)
“物体” (属 / 种)
“实体” (属 / 种)
“某物” (属)
我们不断地进行“逻辑抽象”,扔掉更多的规定,概念的“内涵”越来越少,“外延”越来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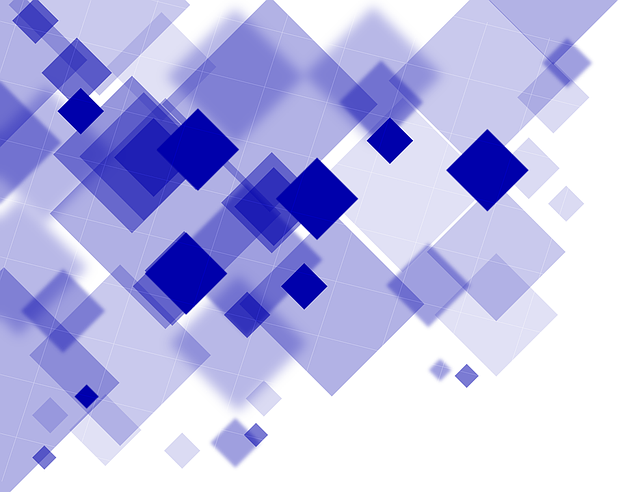
最终,我们会爬到一个“最高的属”。
“最高的属”是那个“再不能是种的属”。比如“某物”(或“存在”、“实体”)。你无法再问:“‘某物’是哪一‘种’?”——它就是一切的“属”。你不能再对它进行“抽象”了,你再“抽去”规定,这个概念本身就消失了(变成了“虚无”)。
向下走:规定的阶梯
我们也可以试着往下走:
“某物” (属)
“物体” (种 / 属)
“有机体” (种 / 属)
“动物” (种 / 属)
“人” (种 / 属)
“欧洲人” (种 / 属)
“希腊人” (种 / 属)
“雅典人” (种 / 属)
“雅典哲学家” (种 / 属)
“苏格拉底” (直观)
我们不断地进行“逻辑规定”,添加更多的特征,概念的“内涵”越来越多,“外延”越来越小。
那么,有没有一个“最低的种”呢?
理论上说,“最低的种”是那个“再不能是属的种”。
但这里有一个奇妙的“连续性法则”:在现实中,我们永远达不到一个“最低的种”。

为什么?
因为你总能再添加更多的规定。
“雅典哲学家”
“长得不好看的雅典哲学家”
“长得不好看、妻子很凶的雅典哲学家”
你总能不断地细分下去。你永远无法通过“概念”来穷尽一个“个体”。
一个个体(比如苏格拉底本人)是“通体规定的”。他包含了无限多的规定(他的身高、体重、他今天早饭吃了什么、他此刻鼻子上有没有灰尘)。
而“概念”永远是“抽象”的。
所以,一个“通体规定的知识”,只能作为“直观”被给予,而不能作为“概念”被思考。我们用“概念”只能无限地“趋近”于个体,但永远无法“抵达”它。
这就像数学上的“渐近线”。
思维阶梯的使用规则(以及如何吵赢一场架)
这个“属/种”阶梯(逻辑学家称之为“从属关系”)不仅仅是一个漂亮的摆设,它有非常严格的使用规则。掌握了这些规则,你就能立刻发现别人(和你自己)思维中的漏洞。
凡适合于“属”的,也适合于“种”
这条规则是“向下”传递的。
前提: 凡适合于“较高概念”(属)的,也适合于包含在它之下的所有“较低概念”(种)。
举例:
如果 “所有动物(属)都是会死的”。
那么 “所有人(种)也都是会死的”。
应用: 这是所有演绎推理的基础。我们把一个普遍的真理,应用到一个具体的种类上。
陷阱:凡适合于“一个种”的,并不适合于“另一个种”
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错误推理:
“人”(种)是“有理性的”。
“马”(种)也是“动物”(和人同属一个属)。
结论: “马”也是“有理性的”。
分析: 这是荒谬的。“有理性”是“人”这个“种”的“种差”,是它和其它“种”不一样的地方。你不能把一个“种”的特殊属性,安在另一个“种”的头上。
应用:
“我认识的那个哲学家(种)人很刻薄。”
“我也是个哲学家(同种)。”
“所以你人也很刻薄。”
——这是错误的。(也许吧)

另一个应用:
“凡是不适合于‘人类’的(比如‘需要长出翅膀才能飞’),也不适合于‘天使’。”
——你不能做出这个断定。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种”(假设它们都属于“有限的理性存在”这个“属”),它们各自的规定是不同的。
我们不能断定:凡适合于一个较低概念的,也适合于(和它同属一个较高概念的)其他较低概念。
诸物在其中“一致”的东西,来自它们共同的“属”(普遍属性)。
诸物在其中“相异”的东西,来自它们各自的“种”(特殊属性)。
混淆了这两者,是世界上90%的糟糕争论的来源。
思维的两个方向——是“飞上天”还是“钻到底”?
最后,我们来谈谈“概念”的两种“使用方式”。
我们已经知道,任何概念都是“抽象概念”(因为它们都是通过“抽象”工序制造出来的)。但“使用”它们的方式,却有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
方向一:抽象地使用
当你“抽象地”使用一个概念时,你是着眼于它的“较高概念”(属)。
例子: 你在思考“人”的时候,不是在想张三李四,而是在想“人”作为“动物”的一种,有什么特点。
过程: 你不断地“去掉”规定,从“人”到“动物”,到“有机体”,到“某物”。
结果: 你达到了“最高的属概念”。
优点: 你的外延极大。你“稍知许多事物”。你的视野非常宏观,你能把握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
缺点: 你的内涵极小。你的认知非常“空洞”。你知道“万物皆为某物”,但这在周一早上对你毫无帮助。

方向二:具体地使用
当你“具体地”使用一个概念时,你是着眼于它的“较低概念”(种)。
例子: 你在思考“人”的时候,不是在想“人”作为“动物”的属性,而是在想“人”可以被分为“男人”、“女人”、“学者”、“工人”……
过程: 你不断地“添加”规定,从“人”到“学者”,到“历史学者”,到“专攻古罗马史的历史学者”。
结果: 你无限地趋近于“个体”(直观)。
优点: 你的内涵极大。你“甚知少数事物”。你的认知非常“扎实”,你是一个专家。
缺点: 你的外延极小。你可能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哪种使用方式更优越?
这是一个伪问题。
一种使用的价值并不比另一种估价较小。
一个只会在“抽象”方向上思考的人,是一个空谈家。
一个只会在“具体”方向上思考的人,是一个事务主义者。
真正的智慧,在于能够自如地在这两个方向上“切换”。
一种通俗易懂、又能真正解决问题的“艺术”,就在于:在同一项知识中,使“抽象表象”(宏观的“属”概念)与“具体表象”(扎实的“种”概念)保持适当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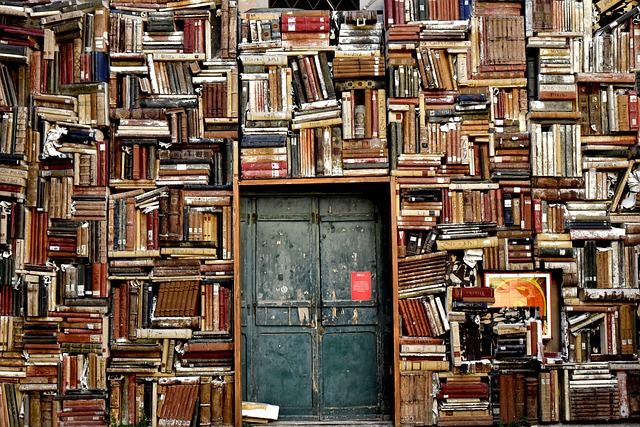
你需要知道你的问题,在“思维阶梯”的哪一个层级上。
当你在进行“战略规划”时,你需要“抽象地使用”概念,跳到“属”的层面,看看全局。
当你在“执行任务”时,你需要“具体地使用”概念,深入到“种”的层面,处理细节。
在本文中,我们从一个非常“具体”的直观(“土豆”那只狗)开始,一路“抽象”到了“某物”这个最高的“属”;然后我们又学会了如何通过“规定”,再一路“具体”地走回来。
这就是“运筹帷幄”的全部秘密。它不是什么神秘的天赋,它就是对“概念”这个工具的熟练掌握。它是一种可以被习得的、关于“思考”本身的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