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的雨丝缠绕着庭前海棠,我坐在朱漆剥落的回廊下,指尖银针起落间,绢面上渐次绽开胭脂色的重瓣。远处笙箫笑语阵阵飘来,夹杂着葡萄酒的醇香——是我的庶妹苏玉茹又在宴请那些追捧她的文人墨客。
"大小姐,二姑娘昨日又支了三千两,说是要引进西域的琉璃蒸器。"老管家苏伯立在阶下,皱纹里嵌着忧虑,"库房里只剩最后两锭官银了..."
针尖刺进指腹,血珠洇上绣绷。我望着那抹嫣红,想起一年前那个飞雪漫天的冬日。边关八百里加急传来噩耗时,父亲和三位兄长的棺椁正停在滴水成冰的庭院里。祖母当场呕血身亡,母亲在停灵第七夜解下腰封悬了梁。是我这个嫡长女亲手为他们阖上双眼,用嫁妆钱买来薄棺,在漫天纸钱中送走了苏家最后的风光。
"由她去罢。"我拆掉染血的绣线,"既然父亲生前允她姨娘掌家,如今自然该由她女儿接手。"
丫鬟碧珠急得绞帕子:"可您才是正经嫡女!这半年您日夜刺绣贴补家用,二姑娘却拿着公中的钱挥霍...连林尚书家都开始传言,说要改聘二姑娘为媳!"
雨声渐密,敲在青瓦上如碎玉迸溅。我望着廊外被雨水打湿的海棠,想起那些重复出现的梦境。总有个声音在耳边泣诉:侯府将倾,金银散尽,仇敌踩着苏家尸骨登临九重。
因此当苏玉茹落水醒来后突然通晓酿酒织锦之术,我默许她夺走掌家权。既然注定要为人作嫁,不如让她绣个最华丽的钱袋——待豺狼嗅着腥味而来时,我早已备好斩狼刀。
"大小姐!不好了!"门房浑身湿透踉跄奔来,"刑部官兵围了府邸,说是要抄家验产!"
绣针倏然刺进檀木框。该来的终于来了。
"二姑娘呢?"
"找遍各处都不见人影!"
我转身穿过风雨飘摇的游廊。苏玉茹的闺房里弥漫着葡萄酒香,梳妆台上放着半杯琥珀色的琼浆。指尖抚过牡丹雕花某处凸起,墙面悄然滑开时,浓烈的金银气扑面而来。
密室内,苏玉茹正瘫坐在满地狼藉中。云锦帐幔被扯得七零八落,她死死抱着一匹流光溢彩的雀金呢,见到我时瞳孔骤缩:"你怎会知道..."
"赵霁骗了我。"她突然尖笑起来,笑声癫狂如寒鸦啼夜,"说什么知己相逢恨晚,原来全是套话的伎俩!"
我皱眉击向她后颈。接住软倒的身躯时,瞥见满室珠光灼目——东墙堆着鎏金嵌宝酒器,西墙列着西域琉璃盏,南边整排紫檀箱笼散落着珍珠玛瑙,北面竟还有尊三尺高的红珊瑚。
是了,梦中那人就是为这些而来。璃亲王,害我父兄战死沙场、夺我家产的仇敌。
怀中玉佩突然发烫。这是半年前循着梦境指引,在城郊荒宅梁上所得。那日不慎被绣针扎破手指,血珠滴落玉佩的刹那,竟见满室泛起青雾——待雾气散尽,我已站在个四壁皆水玉的奇巧房间里。多宝格里摆着从未见过的机械钟表,琉璃罐中装着七彩药丸,正是梦中人所说的"随身之境"。
此刻血珠再次滴落玉佩,密室中青雾翻涌。待雾气散尽,满室珍宝已悄然无踪。
脚步声恰在此时逼近。赵霁带着官兵破门而入,殷勤引着蟒袍玉带的男子:"王爷,苏家财宝就藏在此处。"
我垂首掩饰眼中恨意。璃亲王,果然是你。
当暗门再次开启,众人只见满墙画卷——全是赵霁的画像。月下抚琴的,雪中咏梅的,连衣襟墨渍都栩栩如生。
"赵霁!"苏玉茹适时醒来,泪眼婆娑如雨打芙蕖,"这些画抵得过千金万银,我本想等你生辰..."
璃亲王一脚踹开赵霁,阴鸷目光扫过我们:"将苏家姐妹送入王府别院。"
马车颠簸而行时,苏玉茹突然轻声道:"是我小瞧你了。"她来自异世的秘密,我早从她醉后呓语中知晓。她说那个世界女子可为相为将,却同样遭挚爱背叛,坠崖时见到的最后景象是庶妹与未婚夫交握的手。
"合作罢。"我望向窗外连绵雨幕,"你求滔天富贵,我求一线生机。"
王府别院的重重朱门将我们囚于方寸之地。我注意到那个总是沉默的杂役。他穿着破旧葛布衫,脊背却挺得如青松,搬运假山石时臂肌贲张,脚下滑出的步法暗合九宫八卦。
"那人倒有副好筋骨。"苏玉茹顺着我目光看去,"可惜是个锯嘴葫芦。"
我端着新蒸的莲蓉糕走近时,他正在劈柴。斧刃落处木屑纷飞,每道裂痕都深浅一致。
"尝尝?"我递上青瓷碟。
他沉默接过,吃得很快却不显粗鲁。日光淌过他棱角分明的下颌,那里有道旧疤隐入衣领——正是梦中见过的那道箭伤。
此后我常送衣食。他始终寡言,直到某日我发现他穿着我送的棉袍蹲在墙角——正将抢他新衣的恶仆揍得哀嚎不止。
"为什么?"我替他包扎伤口时问。
他第一次直视我:"衣服是你给的。"
苏玉茹急得跳脚时,窗外正飘起今冬初雪:"你还有心思风花雪月?璃亲王要我去替他经营皇商!"
我将鎏金簪塞给杂役:"劳烦交给万宝阁掌柜。"簪管里藏着苏玉茹给晋王的密信,簪头暗格却藏着我的血书——"晏家军旧部可安否?"
三日后,圣旨以制作太后寿服为由带走了苏玉茹。她趁机讨要我们二人,璃亲王竟也允了。
获得自由那日,雪下得正紧。我们住进我的陪嫁小院,炭盆里煨着红枣姜茶。暮色透过窗棂落在他肩头,我替他系好狐裘衣带:"我利用了你。"
"知道。"他握住我手腕,掌心粗粝却温热,"你给了我归处。"
他叫燕拾伍,却是前朝皇孙。当年晏家军蒙冤时,乳母抱着他跳下乱葬岗,被老铁匠捡去当了学徒。我早从梦中知晓他的身份,却未料到他如此直白相告。
"阿菱。"他替我绾发时突然开口,"你想要什么?"
"要仇人伏诛,要沉冤得雪,要世间再无女子如我这般,眼睁睁看至亲赴死却无能为力。"
他俯身拾起落在雪地的红梅,别在我鬓间:"如你所愿。"
晋王败落那日,苏玉茹仓皇撞开院门,发间金步摇碎成两截:"璃亲王要赶尽杀绝!"
我将藏有密信的簪子交给她:"城南有处宅子,快走。"
她红着眼眶抱住我,塞来沉甸甸的包裹:"这是醉仙酿的秘方和雀金织机图...若得再见,必当太平盛世!"
燕拾伍带我潜入深山时,我才见整装待发的三万晏家军。他的舅父晏将军见到我们交握的手,气得吹胡子瞪眼:"老夫说破嘴皮子不如姑娘一眼!"
山呼"殿下"的声浪震落松枝积雪时,他只是替我拢好雀金裘:"冷么?"
我献出密室转移的财富时,晏将军喜得连连搓手:"有此军资,何愁大业不成!"
他却认真道:"这是阿菱的嫁妆。"
璃亲王逼宫那夜,燕拾伍玄甲凛冽如战神临世。我在偏殿听着宫墙外的厮杀声,将匕首抵在心口——宁死不成累赘。
晨光熹微时,他带着满身血腥气归来,倒在我裙畔时还笑着拭去我颊边泪:"幸不...辱命..."
新帝登基后第一道旨,是为苏家平反。第二道是聘我为后。洞房夜他拆开苏玉茹送来的贺礼——竟是整箱异邦话本,最上头那本扉页写着:《霸道皇后与她的忠犬陛下》。
他低笑出声,将我揽入怀中:"娘子以后还是少见她为好。"
"为何?"
"她教坏你。"烛火摇曳中,他吻上我指间旧疤,窗外忽有万千天灯升起,照见锦瑟安放在紫檀案头。那些曾经藏锋的岁月,终成红帐里交缠的青丝,生生世世,绵延不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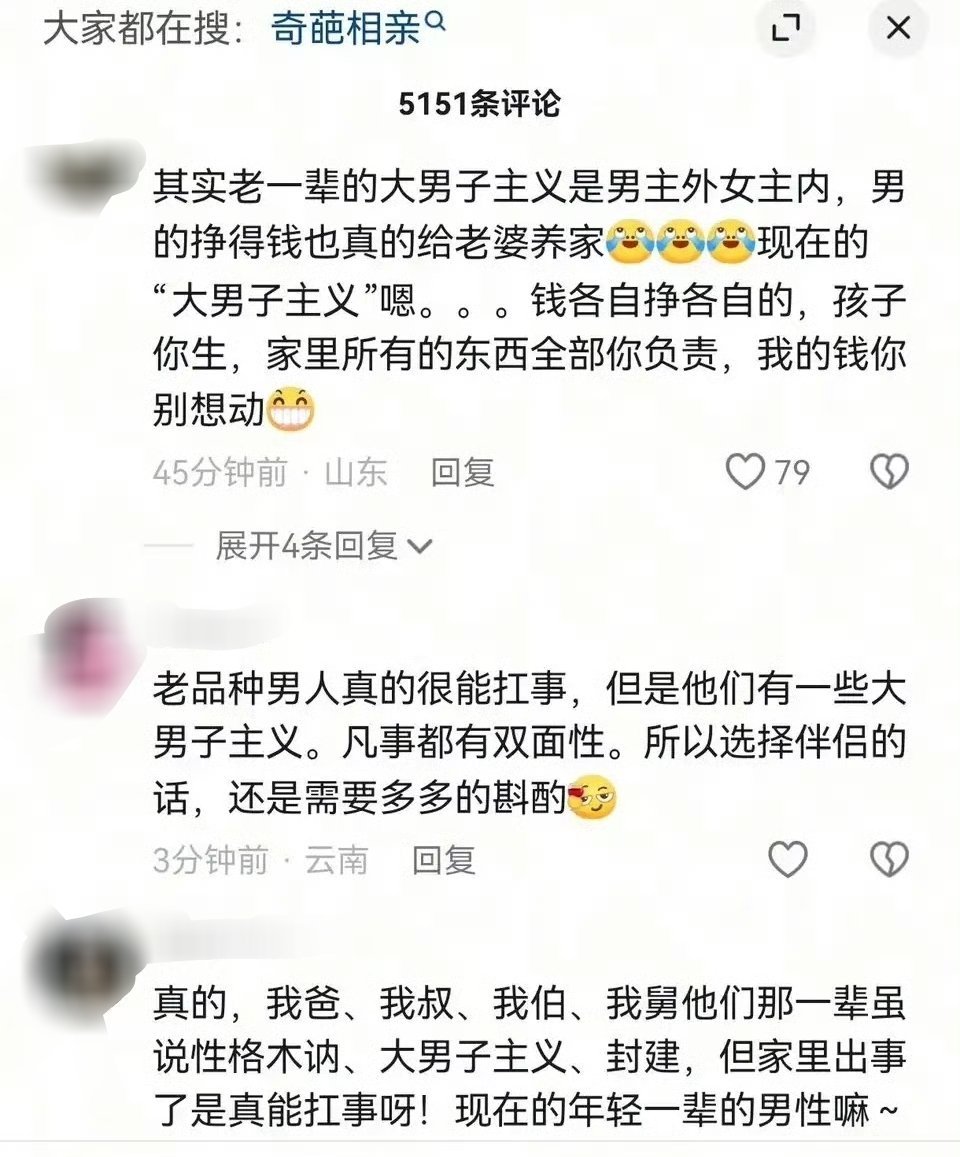


![这是嫉妒的眼睛都发绿了[捂脸哭][捂脸哭][捂脸哭]](http://image.uczzd.cn/566865349186400145.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