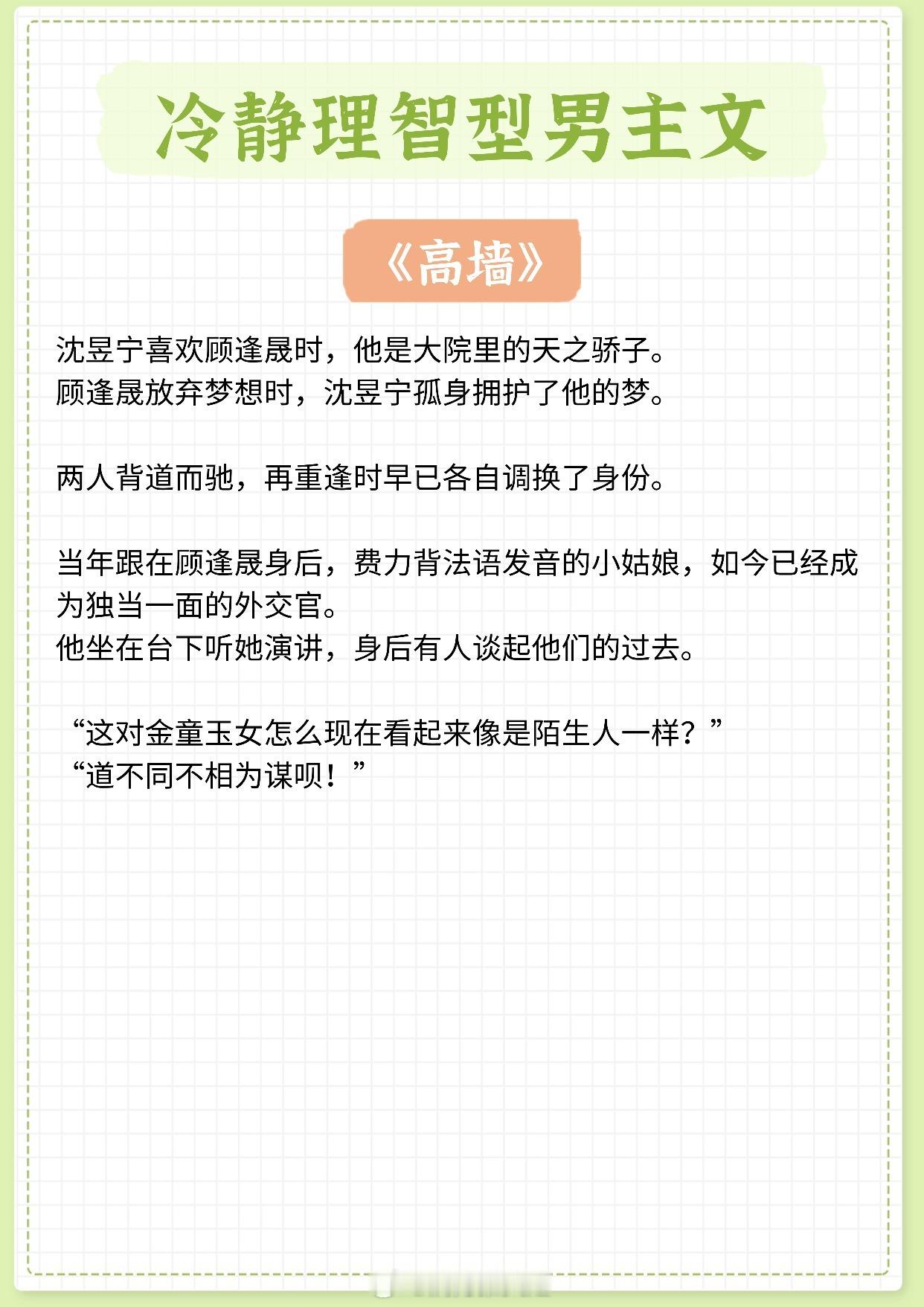三十二年的婚姻,三十二年的AA制,三十二年的分餐而食。
在别人看来,我们的婚姻方式或许有些奇怪,但这正是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
直到我丈夫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一切开始变得不同。
那天,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郑重地告诉我一个决定,既让我意外,又似乎在情理之中。
当他说完那句话后,我只是轻轻翘起嘴角,点了点头......
但有些事情,远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01
我叫张桂芳,今年58岁,和丈夫陈建华结婚整整32年了。
在这32年里,我们一直坚持AA制,分餐而食,这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桂芳,你们夫妻俩怎么还分开吃饭啊?这么多年了,不觉得别扭吗?”邻居刘大姐总是好奇地问我。
“习惯了,各吃各的,互不干扰,挺好的。”我总是这样笑着回答。
其实,分餐是从结婚第三年开始的。
那时候,陈建华刚调到锻造厂上夜班,经常凌晨两点才回家,早上八点又要赶去处理白天的事务。
他喜欢吃重口味的菜,辣椒、大蒜一个都不能少,还喜欢边吃饭边听广播,说这样感觉更放松。
而我口味清淡,喜欢吃些清蒸蔬菜和粥,最重要的是我吃饭时喜欢安静,稍微有点响动就觉得胃口全无。
“建华,要不我们分开吃饭吧,你吃你的重口味,我吃我的清淡菜,互不影响。”有一天晚上,我实在受不了他那盘辣得呛鼻的炒肉,提出了这个建议。
“分开吃饭?这合适吗?别人会不会觉得我们感情有问题?”陈建华皱着眉头,有些犹豫。
“管别人怎么想干嘛?我们又不是离婚,只是吃饭分开,生活还是在一起的。”我坚持道。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分餐的生活。
一开始确实有点不适应,但很快我们发现,这样的安排其实很舒服。
他可以在厨房炒他的辣椒肉,我在另一边煮我的清汤面,互不打扰,各自享受自己的口味。
至于AA制,那是我们结婚时就定下的规矩。
我在机场做地勤工作,陈建华在锻造厂,两人收入差不多。
“既然我们都上班赚钱,那就各管各的钱,互不依赖,这样最公平。”结婚时,陈建华主动提出了这个想法。
我当时也觉得挺好,经济独立,谁也不用看谁的脸色。
于是我们约定,家里的大开销,比如房租、水电费、买家电,两个人平摊。
日常的米面油盐,一个月我负责,一个月他负责,轮流来。
各自的衣服、个人用品、娱乐花销,都用自己的钱,从不混淆。
“桂芳,你们这样算账不麻烦吗?夫妻之间分得这么清楚干嘛?”我妈当初很不理解。
“妈,这样反而简单,钱的事儿不会吵架,感情更纯粹。”我耐心地解释。
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是对的。
这么多年来,我们几乎没因为钱的事儿闹过矛盾。
陈建华想买什么,自己掏钱,我从不过问。
我想买件新衣服或者去美容院,也是自己决定,不用跟他商量。
逢年过节给双方父母的孝敬钱,也是各给各的,从不混在一起。
“你们这样过日子,还像夫妻吗?”有亲戚忍不住质疑。
“怎么不像?我们只是经济上独立,感情上还是夫妻,日子过得踏实。”陈建华总是这样回答。
确实,虽然我们分餐吃饭,AA制,但感情一直很稳定。
陈建华是个老实人,工作勤奋,对我也体贴。
每天下班回家,他都会主动收拾厨房,帮我把餐具洗干净。
“桂芳,今天轮到我买菜,你想吃点啥?”他经常这样问。
“随便吧,你看着买就行。”我一般都这样答。
他的厨艺不错,尤其是麻辣鱼,辣得过瘾,鱼肉还特别鲜嫩。
“建华,你这麻辣鱼咋做的?味道这么好!”我忍不住夸他。
“多放点花椒和干辣椒,鱼得选新鲜的,火候掌握好就行。”他总是笑着分享秘诀。
虽然分餐吃饭,但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客厅一起看电视,聊聊天。
“今天厂里来了个新工,技术还不错。”陈建华会跟我讲工作上的事。
“我们机场新来了个调度员,业务挺熟练的。”我也会分享我的见闻。
这样的生活简单却温馨,我们都觉得挺满足。
02
1998年,我们搬进了单位分的二室一厅,空间更大了。
“现在房子大了,还要继续分餐吗?”陈建华问我。
“当然要,都习惯了,干嘛改?”我笑着回答。
于是我们各自在厨房里弄自己的饭菜,他爱吃辣的,我爱吃清淡的,井水不犯河水。
更大的空间让我们的生活更舒服了。
陈建华的饮食习惯没变,厨房里总飘着辣椒的香味,他的餐桌上永远是红彤彤一片。
我的餐桌则清爽许多,蒸鱼、蔬菜沙拉、杂粮粥,摆得整整齐齐。
“桂芳,你的饭菜看着真健康,我的估计太油腻了。”陈建华有时候会打趣道。
“各吃各的,你喜欢你的辣,我也喜欢我的清淡,挺好。”我笑着回应。
2003年,我们都下岗了。
机场效益不好,裁了不少人,我拿了一笔补偿金回家了。
陈建华的锻造厂也撑不下去了,他选择了内退。
“建华,咱们都没工作了,接下来咋办?”我有些担心。
“没事儿,我们还年轻,可以做点小买卖。”他安慰我说。
于是我们用各自的补偿金,在菜市场租了个摊位,开始卖水果。
虽然是合伙做生意,但我们依然坚持AA制。
摊位租金、进货成本,我们一人一半。
每天的收入,也平分。
“桂芳,你们这样分账不嫌麻烦?”新来的摊贩老赵好奇地问。
“不麻烦,习惯了,账算得清楚,心里也踏实。”我笑着回答。
陈建华负责每天早上去批发市场进货,我负责在摊位上卖。
“这些苹果多少钱一斤?”顾客问我。
“三块五,甜得很,今天早上刚进的。”我热情地招呼。
“能便宜点不?”
“三块二,不能再低了,都是好货。”我笑着回应。
卖水果虽然累,但收入还行,一个月下来,我们各自能分到三千多。
“比上班还多点呢。”陈建华挺满足。
“是啊,自己干,时间也自由。”我也觉得不错。
我们在菜市场干了十几年,生活模式没变过。
分餐吃饭,AA制,各管各的钱,各自过自己的小日子。
但我们的感情一直很好,吵架很少,偶尔有分歧也能好好商量。
2015年,我们快60岁了,觉得身体吃不消,就把水果摊转让了。
“桂芳,咱们也该享享福了。”陈建华说。
“是啊,忙了这么多年,该歇歇了。”我点头同意。
转让摊位得了六万块,我们一人分了三万。
加上这些年的积蓄,我们各自都有不少存款。
“建华,你现在有多少存款?”有一天我好奇地问。
“大概二十多万吧,你呢?”他回答。
“我也差不多,二十多万。”我随口说。
其实我没说实话,我的存款比这多得多,但我没必要全告诉他。
既然是AA制,各自的财务就是隐私,不需要完全透明。
陈建华可能也没说实话,但我也不在意。
退休后,我们的生活更悠闲了。
03
每天早上各自做饭吃,下午一起去公园散步,晚上在家看电视。
“这样的日子挺好,没啥压力。”陈建华经常感慨。
“是啊,简单的生活最舒服。”我也挺满足。
偶尔我们会跟老同事聚会,听他们聊各种家务事。
“我儿子买房,我们老两口把存款全掏了。”老张抱怨说。
“我女儿生孩子,请月嫂花了好几万,心疼死了。”老李也叹气。
听到这些,我和陈建华暗自庆幸。
我们没有孩子,没这些负担,可以为自己活。
“建华,我们没孩子,老了会不会没人照顾?”有时候我会担心。
“到时候再说呗,船到桥头自然直。”陈建华总是很乐观。
“再说,咱们还有彼此呢。”他补充说。
这话让我心里暖暖的。
虽然我们分餐吃饭,AA制,但我们依然是最亲密的伴侣。
32年的相处,已经让我们成了彼此生命里离不开的一部分。
2018年,陈建华开始经常肚子痛,食欲也不好。
一开始我们以为是胃病,没太当回事。
“建华,你这肚子痛好久了,要不去医院看看?”我提醒他。
“没事,可能是吃坏了肚子,休息几天就好了。”他不当回事。
但肚子痛持续了一个多月,还越来越严重,体重也掉了不少。
“建华,你这样不行,必须去医院查查。”我坚持说。
“好吧,明天咱们一起去。”他终于同意了。
第二天,我陪他去了市中心医院,做了全面检查。
医生让他做血检、CT,还查了肿瘤标志物,忙了一整天。
“结果啥时候出来?”我问医生。
“明天上午来拿报告。”医生回答。
那天晚上,我们都没睡好,心里忐忑不安。
第二天上午,我们拿着报告去找医生。
医生看完报告,脸色变得很严肃。
“陈先生,您的情况比较复杂,建议去肿瘤科进一步检查。”医生说。
听到“肿瘤科”,我心头一沉。
“医生,严重吗?”陈建华声音有些发抖。
“具体情况得专科医生判断,别太担心。”医生安慰说。
从医院出来,我们一路沉默。
“桂芳,如果真是那个病……”陈建华突然开口。
“别乱想,可能是小毛病。”我打断他。
但我心里其实比他还慌。
一周后,肿瘤科的结果出来了。
胰腺癌,晚期。
听到这个诊断,我感觉天塌了。
陈建华坐在那儿,脸色苍白,好半天没说话。
“医生,还有救吗?”我强忍泪水问。
“可以试试化疗,但效果不好说。”医生实话实说。
“费用大概多少?”陈建华问。
“一个疗程大概六万,可能得做几个疗程。”医生解释。
六万一个疗程,几个疗程就是几十万。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大数目。
04
回家的路上,陈建华一直没说话。
“建华,别想太多,先治病。”我安慰他。
“桂芳,化疗那么贵,万一治不好……”他忧心忡忡。
“不管花多少钱,都得试试。”我坚定地说。
回到家,陈建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半天没出来。
吃晚饭时,他突然问我:“桂芳,你现在有多少存款?”
“大概三十多万吧。”我如实说,但没说出全部。
“我这儿有二十多万,加起来够几个疗程。”他算了算。
“钱的事儿你别操心,先治病要紧。”我说。
第二天,陈建华开始住院化疗。
第一个疗程后,他瘦了一大圈,头发也掉了不少。
“建华,感觉咋样?”我每天都去医院陪他。
“还行,就是没力气,吃啥都没味。”他虚弱地说。
化疗副作用很大,他经常恶心呕吐,人都憔悴了。
“桂芳,我这样拖累你,心里过不去。”他愧疚地说。
“说啥傻话,夫妻就得一起扛。”我握着他的手说。
三个疗程化疗花了十八万,但效果不好。
医生说肿瘤没缩小,还有扩散的迹象。
“医生,还有别的办法吗?”我不甘心问。
“可以试试靶向治疗,但费用更高,也不一定适合。”医生说。
靶向治疗一个月要三万多,简直是个无底洞。
陈建华听后,变得更沉默了。
“建华,你在想啥?”我问他。
“我在想,是不是该放弃治疗了。”他苦笑说。
“为啥?”我震惊地问。
“治下去,钱花光也不一定好,还不如省点力气。”他分析说。
“钱没了可以再赚,人没了就啥都没了。”我反驳。
“桂芳,我都快60了,治好了又能活几年?”他看得很开。
“但不能放弃希望。”我坚持说。
我们又坚持了两个疗程的靶向治疗。
但效果还是不好,病情继续恶化。
“医生,还要继续治吗?”我问。
“目前效果不明显,可以考虑回家保守治疗。”医生建议。
这话等于宣判了放弃。
陈建华却很平静。
“桂芳,咱们回家吧。”他说。
“好。”我含泪点头。
办理出院时,我算了下费用。
这几个月的治疗,总共花了二十五万。
回家后,陈建华身体越来越弱。
他大部分时间躺在沙发上,很少活动。
“桂芳,麻烦给我倒杯水。”他的声音很微弱。
“好的,你等着。”我赶紧去倒水。
看着他瘦得不成样子,我心如刀割。
这个陪我32年的男人,就要走了。
“建华,想吃啥?我给你做。”我每天都问。
“没胃口,吃不下。”他总是摇头。
尽管如此,我还是变着花样给他做营养餐,希望他能多吃点。
有一天,陈建华的妹妹陈丽华来看他。
陈丽华比他小五岁,在外地做生意,平时联系少。
“哥,听说你病了,我专门请假回来看你。”陈丽华红着眼说。
“丽华,你生意咋样?家里还好吗?”陈建华关心地问。
“生意还行,就是女儿读大学开销大。”陈丽华叹气说。
他们兄妹俩聊了好久,回忆小时候的事。
“记得小时候你总带我去山上摘果子,怕我摔了还背着我。”陈丽华感慨。
“那时候年轻,现在都老了。”陈建华笑着说。
05
陈丽华住了三天,每天陪哥哥聊天。
临走时,她悄悄对我说:“嫂子,我哥的情况不太好吧?”
“医生说时间不多了。”我如实说。
“有啥需要帮忙的,你一定告诉我。”她诚恳地说。
“谢谢,有需要我会联系你。”我点头。
陈丽华走后,陈建华更安静了。
他经常坐在窗边发呆,看着外面的天空。
“建华,你在想啥?”我坐在他旁边问。
“我在想,这辈子值不值。”他慢慢地说。
“当然值,我们过得充实,挺幸福。”我安慰他。
“是啊,虽然没孩子,但我们有彼此。”他握住我的手。
“而且我们的生活方式虽然特别,但我们都习惯了。”他继续说。
“是的,32年了,我们从没后悔。”我点头。
这时,陈建华突然问:“桂芳,如果我走了,你咋办?”
这话让我心一紧。
“别说傻话,你会好起来的。”我回避话题。
“人得面对现实。”他平静地说,“我想把一些事安排好。”
“啥事?”我问。
“比如我的存款,我想……”他停顿了一下。
看他的表情,似乎在做某个重要的决定。
“你想咋样?”我追问。
他沉默了半天,然后说:“我想把我的钱留给丽华。”
这话让我愣了一下。
“为啥?”我不解地问。
“丽华女儿上大学,家里经济压力大。”他解释。
“可那是你的钱,你自己决定就行。”我说。
“我知道,但我觉着这样最好。”他坚持说。
我没再说什么,毕竟32年来,我们的钱各自管,我没权利干涉。
但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第二天,陈建华让我帮他联系银行,说要办手续。
“啥手续?”我问。
“我想把存款转给丽华。”他说。
“现在就转?”我有点意外。
“是的,趁我还能做决定。”他坚定地说。
我陪他去了银行,看着他把钱转给陈丽华。
银行工作人员问:“陈先生,您确定把这些钱都转出去?”
“确定。”陈建华毫不犹豫。
我在旁边看着,心里五味杂陈。
这是他一辈子的积蓄,就这样给了妹妹。
转账完,工作人员说总金额:523万。
听到这数字,我惊呆了。
陈建华的存款竟然有523万?
远超我想象。
从银行出来,我忍不住问:“建华,你咋有这么多钱?”
“这些年做生意,还有点投资,慢慢攒的。”他平静地说。
“为啥以前不告诉我?”我问。
“咱们不是说好各自管各自的钱吗?”他反问。
我无话可说,确实,他没义务告诉我。
但523万这个数字,还是让我震惊。
回到家,陈建华给陈丽华打了电话。
“丽华,我给你转了笔钱,你查查。”他说。
电话那头的陈丽华很惊讶:“哥,你转了多少?”
“523万,我全部的积蓄。”陈建华说。
“哥,这太多了,我不能要!”陈丽华急忙说。
“你拿着吧,我用不了这么多。”他坚持。
“可嫂子咋办?”陈丽华问。
“她有自己的钱,不用担心。”陈建华看了我一眼。
挂了电话,他对我说:“桂芳,我的钱都给丽华了。”
06
我看着他,心里百感交集。
这个和我一起生活了32年的男人,在生命的最后,把所有积蓄给了妹妹。
虽然按我们的约定,他有这个权利,但我心里还是有点复杂。
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我轻轻翘起嘴角,自信地点了点头。
陈建华看到我的表情,有些疑惑。
“桂芳,你笑啥?”他问。
“没什么,就是想起点事儿。”我依然保持着那份自信。
“啥事儿?”他追问。
我没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