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熙宁三年的开封,舍人院的烛火彻夜未熄。刚升任知制诰的苏颂盯着案头那份 “词头”(任命草稿),眉头拧成了疙瘩。纸上赫然写着:提拔秀州判官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
这道任命藏着天大的猫腻。按本朝规矩,御史需由中丞从太常博士以上、曾任通判的官员中举荐,而李定只是地方幕职官,连最低门槛都够不上。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位李定刚从南方回京,只因在神宗面前大夸 “青苗法便民”,就成了王安石眼中的 “新政红人”,要被火箭式提拔。

没等苏颂细想,同僚宋敏求已先一步抗命。这位老臣直接将词头封还,直言 “李定不合条件”。暴怒的神宗当即罢了宋敏求的职,第二次把词头送到舍人院 —— 这次轮到苏颂当值。
“未敢具草。” 苏颂的回复干脆利落,他在奏疏里写道:“李定从边郡小官骤登纠绳之任,近岁未有。坏了规矩,必遭天下非议。” 词头再次被退回,神宗的怒火隔着宫墙都能感受到。
第三次送词头来的宦官脸色铁青,传话时带着威胁:“圣上说了,再敢抗命,宋敏求就是榜样!” 可轮值的李大临依旧硬气,第三次封还词头。一日之内,皇帝旨意三遭驳回,这在北宋历史上从未有过。

神宗彻底被激怒了,第四次下旨,点名要苏颂执笔,还派宰相亲自督阵。苏颂却没慌,反而写了篇长疏跟皇帝讲道理:“乱世可破格选才,太平盛世当守规矩。李定无积累之功,仅凭一句话就登高位,以后人人都想走捷径,国法何在?”
这场君臣博弈就此升级。神宗搬出去年诏令 “御史台缺可不拘官职”,苏颂立刻反驳:“若真不拘,为何还要给李定加太子中允的头衔?这分明是强行凑资格!” 他甚至给皇帝出了道难题:“要写可以,请陛下明批‘特旨所除,不碍条贯’。”
苏颂算准帝王尊严不会屈从臣下,可没想到神宗真是个 “拗皇帝”,居然真的写下御批。第七次交锋,苏颂又用 “采听群议” 拖延,第八次干脆以 “非我轮值” 回绝,直到第九次李大临封还词头,神宗终于忍无可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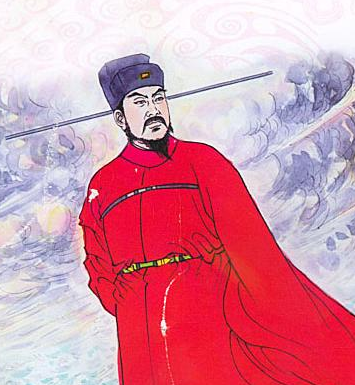
朝堂之上,王安石火上浇油:“陛下威福被臣下夺走,何以立君?” 这句话彻底断了转圜余地。一道罢免令送到舍人院,苏颂看着 “轻侮诏命,国法岂容” 八个字,平静地收拾好笔墨,走出了任职不到半年的官署。
谁也没料到,罢官的苏颂反而成了朝野称颂的英雄。那天他家门前挤满了人,有读书人送来 “直臣” 匾额,有百姓提着自酿的米酒,连退休的老宰相富弼都亲自登门:“你这一退,守住的是朝廷底线啊!”
更讽刺的是被提拔的李定。没过多久,就有人揭发他为当官隐瞒庶母丧事,连 “孝” 字都做不到。后来他又罗织罪名制造 “乌台诗案”,陷害苏轼,彻底成了朝野唾骂的小人。而苏颂虽赋闲在家,却没闲着,他埋头整理医药典籍,后来编纂出被李时珍盛赞的《图经本草》。

神宗渐渐后悔了。两年后淮南遭遇水灾,有人举荐苏颂治水,神宗立刻下旨:“苏颂仁厚,必能安民。” 果然苏颂到任后疏河修堤,还创新法子减轻百姓负担,神宗见状感叹:“此人终究埋没不了!”
苏颂的官宦生涯并未因这次罢官终结,他后来官至宰相,却始终坚守初心。权臣吕惠卿曾暗示他 “登门即可执政”,苏颂笑而不应;儿子该按惯例获官,他却说 “馆阁是育才地,不可循私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