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秉昆,今年四十二,家在苏南水乡的周家村,打小在水边长大,后来承包了村东头那片二十亩的鱼塘,靠养鱼卖鱼过活。我媳妇三年前走了,留下个上初中的儿子周小安跟着我,平日里除了看鱼塘,就是接送孩子、做饭,日子过得像村口那条河,平平稳稳,没什么波澜。
那天是六月十六,头伏刚过,天热得邪乎,鱼塘里的草鱼正长肉,得整夜盯着,怕有人来偷鱼,也怕天太热水里缺氧。下午我把小安送到他姥姥家,说好了住两晚,回来就扛着铺盖卷去了鱼塘边的小木屋。那木屋是我搭的,就一间房,摆了张床、一张桌子,墙角堆着渔网和饲料,屋顶吊了个昏黄的灯泡,风一吹就晃悠悠的。

傍晚的时候,邻村的王老实来给我送鱼药,他是个鱼医,平时常来串门。我俩蹲在木屋门口抽烟,他看我一个人闷得慌,从摩托车后座拎出一塑料桶散装白酒,又摸出两袋花生米和一包卤猪头肉,说:“秉昆,今晚我陪你守夜,咱哥俩喝两盅。”我本不想喝,怕夜里起不来,但架不住他劝,想着少喝点没事,就搬了张小板凳,跟他对着坐下来。
酒是本地酿的米酒,度数不高,但后劲足。王老实话多,从村里张家长李家短聊到城里的新鲜事,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手里的酒盅却没停。喝到快十点,桶里的酒见了底,王老实舌头都打卷了,说:“秉昆,我……我得回去了,我家那口子还等着我呢。”我扶着他往摩托车那边走,他骑上车晃了两下才稳住,没走多远又回头喊:“夜里别睡太死,记得起来看增氧机!”我挥挥手,看着他的车灯消失在田埂尽头,才晕乎乎地回了木屋。
屋里的灯泡更晃了,我往床上一躺,浑身发软,脑子里嗡嗡响。迷迷糊糊中,听见木屋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我以为是风,没在意,翻了个身想接着睡。可没一会儿,就感觉有人走到了床边,带着一股淡淡的青草香。我睁开眼,模模糊糊看见个女人的影子,穿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头发很长,垂在肩膀上。
“你是谁?”我嗓子发干,声音都变了调。
那女人没说话,只是站在床边,借着灯光,我看见她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我坐起身,酒劲醒了大半,又问:“你怎么进来的?我门明明插了。”
她这才开口,声音细细的,带着点哽咽:“我……我从门缝里挤进来的,门没插紧。周大哥,你别害怕,我不是坏人。”
我愣了愣,借着酒劲壮了壮胆,起身点亮了桌上的马灯,光线亮了些,才看清她的样子。二十七八岁的年纪,皮肤很白,脸上还挂着泪痕,连衣裙上沾了些泥点,像是走了远路。“你找我有事?”我问。
她低下头,手指绞着裙摆,半天才说:“我叫苏晚晴,是邻村苏家桥的。我……我跟家里吵架了,跑出来的,没地方去,看见这边有灯,就过来了。”
我心里犯嘀咕,苏家桥离这儿有四五里地,黑灯瞎火的,一个女人家跑这么远,确实怪可怜的。我从桌上拿了个干净的搪瓷缸,倒了点凉白开递给她:“先喝点水吧。吵架归吵架,也不能大半夜跑出来,多危险。”
她接过搪瓷缸,双手捧着,小口小口地喝着,眼泪又掉了下来:“我爸要把我嫁给镇上开五金店的张老板,那人都四十多了,还离过婚,我不愿意,他就打我……”说着,她撸起袖子,胳膊上果然有一块青紫色的瘀伤。
我看着那瘀伤,心里也有点不是滋味。我们这地方,虽说现在不兴包办婚姻了,但还有些老辈人想把女儿嫁个“有钱的”。我叹了口气:“那你也不能一直跑出来啊,总得想办法跟家里沟通。”
“沟通不了,我爸眼里只有钱,张老板给了他三万块彩礼,他早就答应了。”苏晚晴抹了把眼泪,抬头看着我,“周大哥,我知道我来这儿很唐突,但我实在没地方去了,能不能让我在这儿住一晚?明天一早我就走。”
我看着她可怜巴巴的样子,又想起自己媳妇在的时候,总说我心太软。这木屋就一张床,让她住下来,确实不方便,但大半夜让她一个女人出去,万一出点事,我良心也不安。犹豫了半天,我说:“行吧,那你睡床上,我在桌子边凑合一晚。”
她说:“不用不用,我睡地上就行。”说着,就想去抱墙角的草席。我赶紧拦住她:“地上凉,你一个女的,怎么能睡地上。别争了,我年轻,扛得住。”
我把床上的铺盖理了理,让她躺下,自己拿了件外套搭在身上,坐在桌子边的椅子上,想着眯一会儿,可酒劲还没完全过,眼皮越来越沉,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我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弄醒了。睁开眼,看见苏晚晴坐起身,正看着我。马灯还亮着,灯光照在她脸上,显得格外柔和。“周大哥,你冷不冷?”她问。
我摇摇头:“不冷,你怎么醒了?”
“我睡不着,想着你在这儿坐着,肯定不舒服。”她说着,往床里边挪了挪,“要不……你也上来睡吧,床够宽,我们各睡一边。”
我连忙摆手:“不用不用,我在这儿挺好。”
可她坚持:“周大哥,你别多想,我就是觉得你这样太遭罪了。你要是不上去,我也不睡了,就陪着你坐一夜。”
我看着她认真的样子,又想起夜里确实有点凉,椅子坐着也实在不舒服,心里就有点动摇了。加上酒劲还没全散,脑子一热,就点了点头:“那……那行,我就睡边上,绝不碰你。”
我脱了鞋,小心翼翼地躺在床的外侧,尽量离她远一些。床是一米五的,两个人睡确实够宽,但我还是浑身紧绷,不敢动。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小声说:“周大哥,谢谢你。”
“谢啥,都是乡里乡亲的。”我说。

屋里静悄悄的,只有窗外的虫鸣和远处鱼塘里的水声。我闭着眼,想赶紧睡着,可越想睡越睡不着,鼻子里总能闻到她身上的青草香,混合着一点淡淡的汗味,不难闻,反而让人心里有点乱。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觉她翻了个身,离我近了些。我屏住呼吸,不敢动。又过了一会儿,她突然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周大哥,你没睡着吧?”
我“嗯”了一声,没敢睁眼。
“我……我有点怕黑。”她说,声音带着点颤抖。
我心里一软,睁开眼,看见她缩在被子里,眼睛睁得大大的,确实像是很害怕。我想起我媳妇刚嫁过来的时候,也怕黑,晚上总让我陪着说话。鬼使神差地,我就开口了:“别怕,有我在呢。我给你讲讲我鱼塘里的事吧,去年我养的草鱼,有一条长到了二十多斤,卖了好几百块呢……”
我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讲着,她安安静静地听着,时不时“嗯”一声。讲着讲着,我感觉她离我越来越近,最后,她的胳膊不小心碰到了我的手。我像被烫到一样,想缩回来,可她却轻轻抓住了我的手。
她的手很软,有点凉。我浑身一僵,脑子里一片空白,酒劲一下子涌了上来,之前的顾虑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借着酒劲我感觉就像火星落到了干柴上,我浑身的血都涌了上来。我再也忍不住,伸手抱住了她。她没有反抗,反而紧紧地抱住了我。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鱼塘里的增氧机吵醒的。睁开眼,阳光已经透过木屋的窗户照了进来,床上空荡荡的,苏晚晴不见了。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坐起身,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周大哥,谢谢你昨晚收留我。我走了,别找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苏晚晴。”
我拿着纸条,心里乱糟糟的。昨晚的事像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我又羞又悔,觉得自己做了件天大的糊涂事。我怎么能跟一个陌生女人发生这种事呢?她还那么年轻,要是传出去,她的名声就毁了,我的脸也没地方搁。
我起身洗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头发乱糟糟的,眼睛里全是红血丝。我拍了拍脸,告诉自己别想了,就当是一场梦。可越想忘记,越忘不了她的样子,忘不了她抓着我手时的温度。
接下来的几天,我魂不守舍的,喂鱼的时候差点把饲料撒到田埂上,夜里守塘,总觉得木屋门口有人,一开门又什么都没有。王老实来送药,看出我不对劲,问我:“秉昆,你咋了?跟丢了魂似的。”我不敢告诉他实话,只说最近没睡好。
大概过了半个月,那天我正在鱼塘边拉渔网,准备捞几条鱼去镇上卖,忽然听见有人喊我:“周大哥!”
我回头一看,愣住了。是苏晚晴,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一条黑色的裤子,头发扎成了马尾,比上次见的时候精神多了,只是脸上还有点腼腆。她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站在田埂那头,看着我。
我心里一紧,赶紧放下渔网,走到她身边,左右看了看,没人,才小声问:“你怎么来了?”
她低下头,从布袋子里拿出一个瓷碗,递给我:“我……我给你做了点鸡蛋羹,想着你一个人,肯定没好好吃饭。”
我接过瓷碗,还热乎着,心里暖暖的,又有点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打听来的。”她说着,抬起头看着我,“周大哥,上次的事,我……我不后悔。”
我心里“扑通”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又说:“我后来没回家,去城里找了份工作,在一家服装厂上班。我想了很久,觉得不能就这么算了。周大哥,我知道你媳妇不在了,带着个孩子,我不嫌弃,我想……我想跟你过日子。”
我愣住了,手里的瓷碗差点掉在地上。我从来没想过,她会回来找我,还想跟我过日子。我看着她真诚的眼睛,心里又酸又胀。我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个孩子,没什么钱,她怎么会看上我?
“你……你别冲动,”我说,“我比你大十好几岁,还有个儿子,你跟着我,会吃苦的。”
“我不怕吃苦,”她说,“我就想找个踏实的人过日子。上次跟你在一起,我能感觉到,你是个好人。周大哥,你就给我一次机会,也给你自己一次机会,行不行?”
我看着她,想起那天晚上她的眼泪,想起她抓着我手的样子,想起这半个月来的魂不守舍,心里的防线一下子就垮了。我点了点头:“行,那……那你先试试,要是觉得不合适,随时可以走。”
她一下子笑了,眼睛弯成了月牙:“我不会走的。”
从那天起,苏晚晴就住进了我的木屋。她很勤快,每天早上起来给我和小安做早饭,然后帮我喂鱼、清理鱼塘边的杂草,晚上还会辅导小安写作业。小安一开始有点怕生,不怎么理她,可她从不生气,每天给小安买零食,陪他玩,没过多久,小安就一口一个“苏阿姨”地叫着,跟她特别亲。
村里的人见我身边多了个女人,都议论纷纷。有人说我走了桃花运,有人说苏晚晴肯定是图我的鱼塘,还有人跑去跟我丈母娘说,让她管管我。我丈母娘一开始也不同意,跑来跟我闹,说苏晚晴年纪太小,不靠谱。可苏晚晴一点都不生气,每次丈母娘来,她都热情地端茶倒水,还帮着做饭,把丈母娘伺候得舒舒服服的。后来丈母娘见她确实勤快,对小安也好,就慢慢接受了。
就在我们准备领证的时候,出了件事。那天我正在镇上卖鱼,忽然来了个男人,四十多岁,穿着西装,长得油光水滑的,一看见我就问:“你就是周秉昆?”
我点点头:“我是,你是谁?”
“我是张立伟,镇上开五金店的。”他说,语气很冲,“苏晚晴是不是在你这儿?”
我心里一沉,知道他就是苏晚晴说的那个张老板。我点点头:“是,怎么了?”
“怎么了?”他一下子火了,“她是我没过门的媳妇,你凭什么把她拐走?我告诉你,我给了她爸三万块彩礼,她必须跟我回去!”
我皱起眉头:“晚晴不愿意跟你,强扭的瓜不甜,你就别逼她了。彩礼的事,我会跟她爸说,我来还。”
“你还?你拿什么还?”他冷笑一声,“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么让苏晚晴跟我走,要么我就去告你,告你拐骗妇女!”
我气得浑身发抖,想跟他理论,可他根本不听,还动手推了我一把。我卖鱼的摊子被他掀翻了,鱼掉在地上,被路过的人踩得乱七八糟。
我赶紧给苏晚晴打电话,让她别出来。可她还是赶来了,一看见张立伟,脸色就白了,但还是挡在我前面:“张老板,我跟你说过了,我不嫁给你,彩礼我会让我爸退给你,你别找周大哥的麻烦。”
“退?你爸早就把钱赌光了,怎么退?”张立伟说,“我不管,你必须跟我走,不然我就砸了你的鱼塘!”
就在这时,王老实刚好路过,他看见这边乱糟糟的,赶紧跑过来,问清楚了情况,指着张立伟的鼻子骂:“你这人怎么回事?晚晴不愿意跟你,你还强迫人家?彩礼的事你找她爸去,跟秉昆没关系!”
周围的人也都看不过去了,纷纷指责张立伟。张立伟见众怒难犯,撂下一句“你们等着”,就灰溜溜地走了。
我看着苏晚晴,她吓得浑身发抖,我赶紧抱住她:“别怕,有我在呢。”
她靠在我怀里,哭着说:“对不起,周大哥,都是我连累你了。”
“傻丫头,跟我还说什么连累。”我说,“彩礼的事我来解决,你别担心。”
后来,我凑了三万块钱,找到了苏晚晴的爸爸,把彩礼钱还了。她爸一开始还不愿意,说苏晚晴不听话,可后来见我态度坚决,又怕我真的告他逼婚,就收下了钱,还跟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找苏晚晴的麻烦。
张立伟那边,见彩礼钱拿回来了,又知道苏晚晴是真心想跟我过日子,也没再来找过麻烦。
解决了这些事,我和苏晚晴就去民政局领了证。领证那天,天气特别好,阳光明媚,小安拉着我们俩的手,蹦蹦跳跳地说:“爸爸妈妈,我们去吃好吃的!”
苏晚晴一下子红了眼眶,看着我说:“周大哥,我真幸福。”

我握着她的手,心里暖暖的。谁能想到,那天鱼塘守夜,喝醉酒做了件糊涂事,竟然让我遇到了晚晴,收获了这么好的爱情。原来有时候,生活就是这么奇妙,看似不经意的一件事,却能改变人的一生。
现在,我们结婚已经三年了,小安也上了高中,学习成绩很好。我的鱼塘生意越来越红火,我们在村里盖了新房子,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每天晚上,我和晚晴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星星,听着鱼塘里的水声,小安在屋里写作业,我就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有时候,我会想起那天晚上的米酒,想起王老实的猪头肉,想起苏晚晴第一次出现在木屋里的样子。如果那天我没有喝酒,如果我没有收留她,也许我的人生还是一片灰暗。可偏偏,就是那一次“糊涂事”,让干柴遇到了烈火,让我这个中年男人,重新找到了家的温暖,收获了一辈子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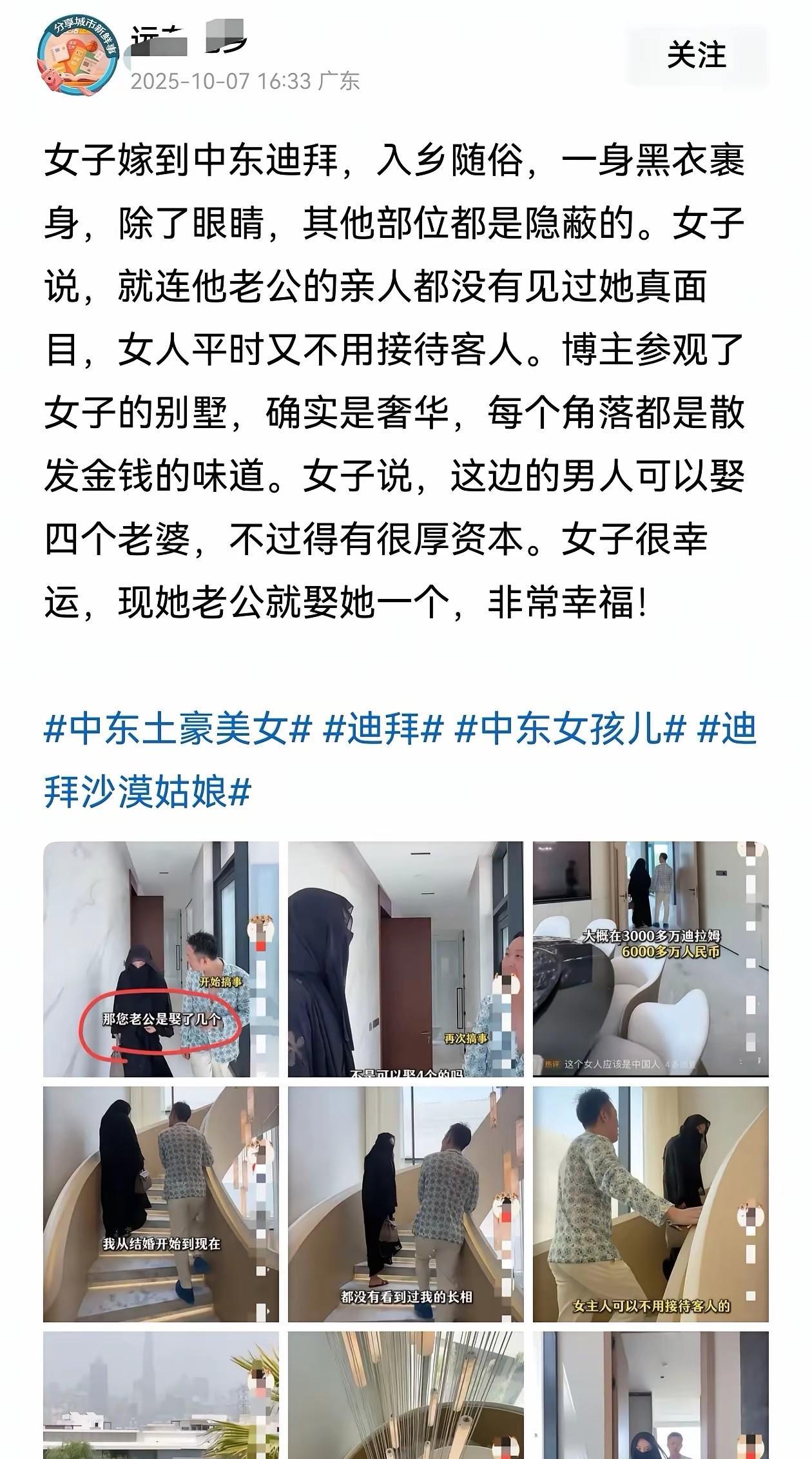

![彩礼不多,但是加上其他开销就很多了[吃瓜]](http://image.uczzd.cn/808891302984281102.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