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拔掉管子,用最后的钱买了157罐啤酒。 主治医生摇头说“没见过这样的”。 但数字更冰冷:他经历了32次放疗,肿瘤没小,人瘦了40斤。 呕吐把食道灼伤,皮肤溃烂到看见骨头。 他说,疼得想撞墙的时候,“活着”两个字只剩下笔画。 在医院的重症病房里,这样的场景或许少见,但对于晚期癌症患者来说,治疗带来的痛苦与生存希望之间的拉扯,早已是日常。 很少有人能真正体会他那段日子的煎熬。放疗的副作用从第一次治疗后就开始显现,起初只是轻微的恶心,后来发展成无法控制的剧烈呕吐。 胃酸一次次冲刷食道,灼烧感从喉咙一直蔓延到胸口,到最后他连喝口水都觉得像是吞了刀片。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皮肤反应。 放疗区域的皮肤先是发红、发痒,接着开始脱皮、溃烂,最严重的时候,伤口深到能直接看见底下的骨头,哪怕是轻轻碰一下床单,都能疼得他浑身发抖。 每天早上一睁眼,迎接他的就是针头扎进血管的刺痛,护士熟练地为他接上输液管,冰凉的药液顺着血管流遍全身,带来一阵又一阵的寒意。 而放疗后翻江倒海的呕吐,更是准时准点降临,他常常趴在床边吐到脱力,连抬起头的力气都没有。 护士推着治疗车进来的时候,他甚至不敢抬头看,怕看到那些闪着寒光的仪器,怕听到“今天还要加一次化疗”的通知。 癌症治疗中,放疗和化疗的叠加治疗是常见的激进方案,医生原本希望通过这样的组合拳缩小肿瘤,但对他来说,每一次治疗都是一次煎熬。 他的体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原本140斤的汉子,不到半年就瘦了40斤,瘦成了一把骨头,颧骨高高凸起,眼窝陷了下去,连走路都得扶着墙,每走一步都要大口喘气。 32次放疗,一次都没落下,他咬着牙扛过来了。每次治疗结束,他都会在病床上躺很久,浑身的力气像是被抽干了一样。 他也曾抱有期待,每次做完检查都会紧张地等待结果,希望能听到肿瘤缩小的好消息。可医生拿着片子叹气的样子,终究还是打破了他的幻想。医生说肿瘤的大小没变化,建议他继续治疗,试试更激进的方案,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可他看着片子上那个顽固的阴影,突然就累了。他想起治疗期间,因为喉咙剧痛,他只能吃流食,曾经最爱的烧烤、火锅都成了奢望。 因为皮肤溃烂,他夏天不能穿短袖,连洗澡都要小心翼翼;因为长期输液,他的手臂上布满了针眼,青一块紫一块。 他不想再被绑在病床上,不想再闻消毒水的味道,不想再让身体被各种管子和药物支配,更不想在无尽的痛苦中等待一个渺茫的结果。 于是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拔掉身上的管子,出院。他没告诉家人,也没和医生多争辩,只是平静地跟医生说自己想出院,态度坚决得让人无法反驳。 办理完出院手续后,他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一个装着几件换洗衣物的小背包,揣着身上仅有的一点钱,走进了家附近的小卖部。 他抬手算了算钱,是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的,加上报销后剩下的一点治疗费,刚好够买157罐,不多不少。老板帮他把啤酒搬到电瓶车上,还问他要不要帮忙送回家,他笑着摇了摇头,自己慢慢推着车往出租屋走。 回到那个狭小的出租屋,他脱掉上衣,光着膀子靠在床头,插管的位置贴着纱布,还隐隐渗着血,他拉开第一罐啤酒的易拉环,“咔嗒”一声脆响,比心电监护仪的滴滴声好听多了。 他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小口,冰凉的液体滑过喉咙,带着淡淡的麦芽香,竟然暂时压住了食道的灼痛。他慢慢品味着这份久违的惬意,一罐接一罐,没有豪饮,只是小口小口地喝着。 记忆慢慢浮现,他想起没生病的时候,和朋友在街边撸串喝啤酒的日子,夏天的晚风拂过脸颊,耳边是热闹的人声和碰杯的清脆声响。 想起自己曾经为了赶项目加班到深夜,下班路上买一罐啤酒,坐在路边喝完再回家,那些曾经觉得平凡的日子,原来才是最珍贵的。他不是不想活,只是不想那样活着——没有质量,没有尊严,每天在痛苦和煎熬里数着日子。 157罐啤酒,他喝了很久。有时候喝着喝着就睡着了,罐子空了一排。他会把空罐子整齐地堆在墙角,看着它们一点点堆积起来,像是在记录着属于自己的最后时光。 主治医生后来从护士口中听说了他的事,还是忍不住摇头,但语气里多了些理解。在临床治疗中,医生往往更关注患者的生存期,却容易忽略患者的生活质量,这位患者的选择,或许也让医生重新思考治疗的意义。 那157罐啤酒,它们被整齐地码放在李卫国家的储藏室里,像一座沉默的纪念碑。每一个易拉罐上,都凝结着一个普通人在巨大痛苦面前,最后的选择——不是选择如何死去,而是选择如何记住自己曾经活过。 官方信源: 商丘网络电视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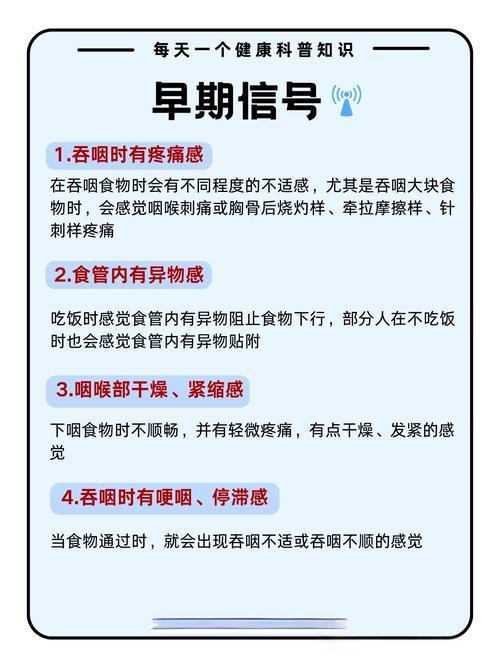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