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苏晚意,今年三十岁,在一家母婴用品店当店长。打我十七岁那年我爸带着柳玉茹进门,到现在十三年,我没跟她正经说过几句话,更别提喊一声“妈”了。
我亲妈在我十岁那年跟我爸离婚,跟着一个做建材生意的男人去了南方,头两年还寄点衣服零食,后来就断了联系。我爸是机械厂的老工人,寡言少语,每天下班回家就钻进厨房做饭,我放学回来写作业,父女俩一天说不上十句话。十七岁那年冬天,我爸突然跟我说:“晚意,爸认识了个阿姨,人挺好的,想让她来家里住,你看行吗?”
我当时正扒拉着碗里的白菜,头都没抬:“你自己乐意就行,别指望我跟她多亲近。”
没过一周,柳玉茹就搬进来了。她看着四十出头,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头发梳得光溜溜贴在脑后,手里提着一个旧木箱,站在客厅中央,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晚意,我叫柳玉茹,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她笑着说,眼角堆起细纹,手里还攥着个布包,“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你尝尝。”
我没接,转身回了房间,“砰”地关上门。那糖糕后来在客厅茶几上放了三天,硬得像石头,最后被我爸扔了。
柳玉茹话不多,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做饭,熬小米粥、蒸鸡蛋,还会给我爸熨好工作服。我爸上夜班,她就等他回来,把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我放学回家,总能看见她在厨房忙活,听见开门声,就探出头问:“晚意,今天想吃啥?阿姨给你做。”
我要么“嗯”一声,要么直接回房间,从不搭她的话。有次她洗了我的校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我床上,我拿起来就扔到沙发上,第二天穿着皱巴巴的校服去学校。我爸看见,叹着气说:“晚意,你别这样对玉茹,她没坏心。”
“我没让她洗。”我梗着脖子,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妈都没给我洗过这么多次衣服。”

我爸不说话了,蹲在门口抽烟,烟圈一圈圈飘进屋里,柳玉茹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拿着锅铲,眼圈红红的,却没说一句重话。
后来我考上外地的大学,报志愿的时候特意选了离家里最远的城市,就是想躲开柳玉茹。我爸送我去火车站,柳玉茹给我塞了个布包,里面装着她连夜做的酱菜,还有两千块钱。“晚意,在外头别省着,想吃啥就买,缺钱了跟家里说。”
我把布包塞回她手里:“不用,我爸给我钱了。”
火车开的时候,我看见她站在月台上,跟着火车跑了两步,手里还攥着那个布包,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我别过脸,心里有点酸,可一想到她不是我亲妈,那点酸就又变成了硬邦邦的石头。
大学四年,我很少回家,寒暑假要么在学校打工,要么跟同学去旅游。每次我爸给我打电话,柳玉茹都会在旁边小声问:“晚意吃饭了吗?天冷了有没有加衣服?”我爸把电话递给她,我就说“有事忙”,匆匆挂掉。
毕业那年,我在外地找了工作,处了个对象叫陈景行,是同公司的同事。谈了两年,我们打算结婚,我爸来参加婚礼,柳玉茹没来,说是厂里加班走不开,让我爸带了条她织的红围巾,还有一对银镯子。“这镯子是我妈留给我的,给晚意当嫁妆。”我爸把镯子递给我,“玉茹说,晚意结婚,她高兴。”
我拿着镯子,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婚礼那天,我亲妈突然来了,穿着一身名牌,手里提着个名牌包,拉着我的手说:“晚意,妈来晚了,这是妈给你的红包。”
我看着她,陌生得像个外人。她坐了不到一小时,接了个电话就走了,说生意上有急事。我站在酒店门口,看着她的车开远,手里的红包沉甸甸的,心里却空落落的。
婚后第二年,我怀孕了。孕吐得厉害,吃什么吐什么,陈景行每天下班回来给我煮粥,可我还是没胃口。有天我爸给我打电话,说柳玉茹听说我怀孕,非要来照顾我,已经买好了火车票。
“别让她来。”我赶紧说,“景行能照顾我,再说我们家小,住不下。”
我爸沉默了一会儿:“晚意,玉茹她……是真心想照顾你。”
“我不用。”我挂了电话,心里有点烦躁。可没过两天,柳玉茹还是来了,提着两大袋东西,里面装着小米、红枣,还有她自己晒的干菜。“晚意,我就在这儿住几天,帮你做做饭,等你好点了我就走。”她站在门口,局促地搓着手,“我跟你爸说了,不麻烦你们。”
我没辙,只能让她进来。她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熬小米粥,炒我能吃下去的清淡小菜,下午就帮我打扫房间,洗我换下来的衣服。有次我半夜腿抽筋,疼得叫出声,她听见了,赶紧跑进来,帮我揉腿,揉了半个多小时,直到我不疼了才回房间。
“谢谢你。”我小声说。
她愣了一下,笑着说:“谢啥,应该的。”
可我还是没喊她“妈”。她在这儿住了一个月,我孕吐好了,就催她回家。她收拾东西的时候,把一张银行卡塞给我:“晚意,这里面有五万块钱,是我跟你爸攒的,你生孩子的时候用。”
我把卡推回去:“不用,我们有钱。”
她把卡放在茶几上:“拿着吧,给孩子买点东西。”说完,提着行李就走了,没让我送。
预产期快到的时候,我给亲妈打了个电话,说我要生了,想让她来陪陪我。她在电话里说:“晚意,妈最近在国外考察,等你生了,妈给你寄礼物。”说完就挂了电话。我看着手机,眼泪掉了下来,陈景行抱着我说:“别难过,不是还有我嘛。”
生产那天,我进了产房,疼得死去活来,陈景行在外面等着,我爸也赶来了,蹲在产房门口抽烟,手都在抖。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外面有人喊“玉茹”,抬头一看,柳玉茹跑了进来,头发乱了,衣服上还沾着面粉,手里提着个保温桶。
“大哥,晚意怎么样了?”她抓住我爸的手,声音都在颤。
“还在里面呢,进去快两小时了。”我爸叹了口气,“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厂里忙吗?”
“我听说晚意要生了,请假赶过来的,路上堵车,来晚了。”她把保温桶放在地上,蹲在产房门口,双手合十,嘴里念叨着:“菩萨保佑,晚意平平安安,孩子也平平安安。”
我在里面听着,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疼得又有点暖。宫缩越来越频繁,我喊着“妈”,喊完才反应过来,我喊的不是亲妈,是柳玉茹。
不知过了多久,孩子终于生下来了,是个女孩,护士把孩子抱给我看,我眼泪掉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护士把我推出产房,我看见柳玉茹蹲在地上,头抵着膝盖,肩膀一抽一抽的,我爸拍着她的背说:“好了好了,晚意和孩子都平安了。”
她抬起头,脸上全是眼泪,看见我,赶紧站起来,想碰我又不敢碰,只是拉着我的手:“晚意,你辛苦了,疼坏了吧?”
我看着她,头发上还沾着面粉,眼睛肿得像核桃,手背上有一道划伤,应该是着急赶来的时候不小心弄的。“你手怎么了?”我问。
“没事,路上不小心蹭到了。”她笑着说,把保温桶打开,“我给你熬了鸡汤,你快喝点补补。”
这时候,我亲妈给我打了个电话,陈景行接的,说了两句就挂了。“我妈说啥了?”我问。
“她说她在国外,没时间回来,给你转了两万块钱。”陈景行叹了口气,“晚意,你别往心里去。”
我没说话,看着柳玉茹一勺一勺给我喂鸡汤,鸡汤很鲜,里面放了红枣和枸杞,是我喜欢的味道。她喂我喝汤的时候,手有点抖,汤洒了一点在我衣服上,她赶紧拿纸巾擦,嘴里念叨着:“对不起对不起,我太着急了。”

“柳阿姨,”我开口,声音有点沙哑,“你别忙了,坐会儿吧。”
她愣了一下,坐下的时候,眼睛里又有了眼泪:“好,好。”
晚上,陈景行回家拿东西,我爸也回去休息了,病房里就剩下我和柳玉茹。她坐在床边,给孩子换尿布,动作很熟练,嘴里哼着摇篮曲,声音轻轻的。“我以前在村里,帮邻居带过孩子,知道怎么换尿布。”她笑着说,“这孩子跟你小时候一样,眼睛圆圆的。”
“你见过我小时候?”我问。
“见过,你爸给我看过你的照片,扎着两个小辫子,穿着红裙子,可可爱了。”她把孩子放在我身边,“晚意,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不喜欢我,我也不怪你,毕竟我不是你亲妈。可我看着你,就想起我那早走的女儿,她要是还在,也跟你一样大了。”
我愣住了:“你有女儿?”
“嗯,在她五岁那年,得了白血病,没救过来。”她叹了口气,声音很轻,“后来我跟我前夫离婚了,一个人过,直到认识你爸。你爸跟我说你的事,我就想,要是我女儿还在,我肯定也会好好疼她,所以我就想对你好点,哪怕你不喜欢我。”
我看着她,眼泪突然掉了下来。原来她不是想抢我爸,也不是想占我们家什么,她只是把对自己女儿的爱,都转移到了我身上。我想起这十三年来,她每天早上给我做的早饭,洗的衣服,织的围巾,塞给我的钱,还有她每次欲言又止的眼神,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碎了,化成了一滩温水。
“妈。”我开口,声音有点抖。
她愣住了,手里的尿布掉在地上,抬起头看着我,眼睛瞪得大大的:“晚意,你……你刚才叫我啥?”
“妈。”我又喊了一声,眼泪掉得更凶了,“对不起,我以前对你那么坏,你别生气。”
她一下子扑过来,抱着我,哭得像个孩子:“不生气,我不生气,晚意,你终于肯喊我妈了。”
她的肩膀很窄,却很温暖,我靠在她怀里,像小时候靠在我爸怀里一样,心里踏实得很。
第二天,陈景行和我爸来了,看见我喊柳玉茹“妈”,都愣了,然后不约而同地笑了。我爸说:“这下好了,我们家终于像个完整的家了。”
我亲妈后来给我寄了个名牌包,我没要,让陈景行给她寄回去了。我给她发了条信息:“我有妈了,以后不用你操心了。”
从那以后,柳玉茹就在我家住了下来,帮我带孩子。每天早上,她都会给我熬小米粥,给孩子换尿布,下午推着婴儿车带孩子去小区里玩,晚上等我和陈景行下班回家,做好一桌子菜。
有次我跟她一起带孩子去公园,遇见小区里的邻居,邻居说:“你婆婆对你真好。”
她笑着说:“这是我闺女,我不对她好对谁好。”

我抱着孩子,挽着她的胳膊,心里暖暖的。原来不是亲妈又怎么样,她给我的爱,比亲妈还多。十三年的隔阂,终于在一声“妈”里烟消云散,而我也终于明白,家人不是靠血缘,而是靠真心实意的付出和陪伴。
现在,我每天下班回家,都会喊一声“妈,我回来了”,她听见了,就会从厨房里探出头,笑着说:“回来了,快洗手吃饭,今天做了你爱吃的糖醋排骨。”
孩子也会跟着喊“奶奶”,她抱着孩子,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看着她们,我就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家,温暖又踏实,而这一切,都是柳玉茹给我的。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我早点放下偏见,是不是就能早一点感受到她的爱。可现在也不晚,往后的日子还长,我会好好孝顺她,就像她当初毫无保留地对我好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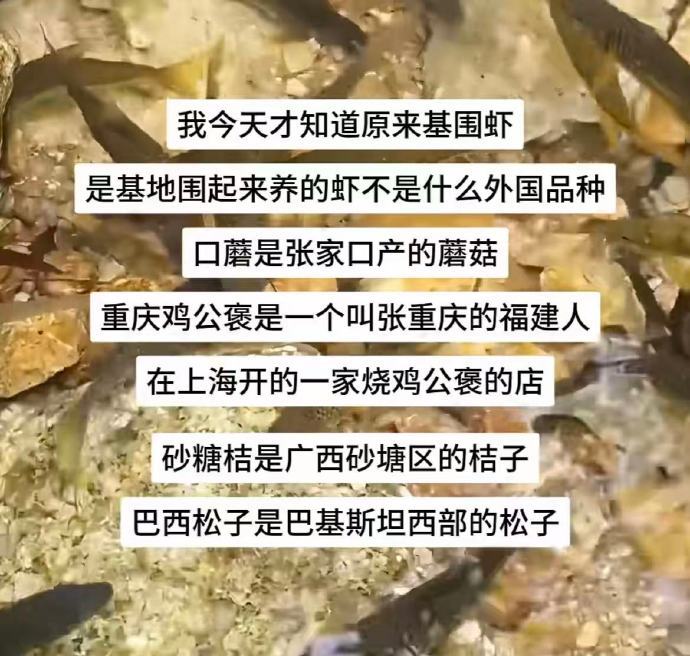
![近视眼的世界真这么离谱吗[笑着哭]](http://image.uczzd.cn/4097665969324366154.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