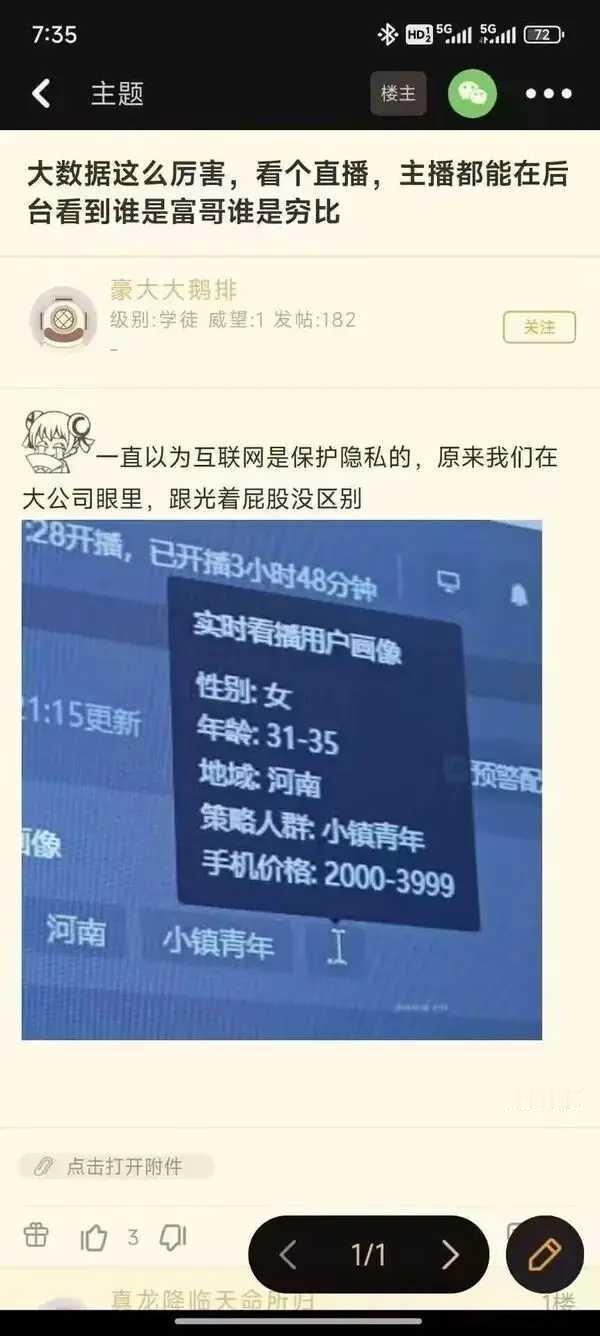昨天去医院看刚生完娃的外甥女,好家伙住院部走廊空空荡荡,跟淡季菜市场似的!走进她住的单间,屋里可热闹了——顺产的外甥女精神头挺好,怀里抱着7斤重的大胖小子,粉雕玉琢的模样招人稀罕。 昨天下午三点多,揣着给外甥女炖的红糖小米粥,我拐进了市医院住院部。 三楼产科走廊静得吓人,瓷砖地光溜溜的,映着头顶惨白的灯,连保洁阿姨的拖把声都在尽头打了个转才回来,跟我想象中挤满探望家属的热闹样儿完全对不上——这哪是生娃旺季,倒像被按了暂停键的空剧场。 走到302病房门口,刚要敲门,里头先飘出句脆生生的笑:“妈,你别老摸他耳朵,刚睡着!” 门一推开,暖烘烘的气浪裹着股奶香涌过来。 外甥女半靠在床头,蓝白条纹病号服套在身上,居然不显松垮,脸色是透着粉的红,哪像刚挨过一刀的人?她怀里躺着个粉团子,裹在鹅黄色的襁褓里,露出来的小脑袋上胎发软软的,闭着眼,小嘴巴还一瘪一瘪,像是在梦里咂奶。 “哟,这就是我大外孙?”我把保温桶放床头柜上,凑过去想摸又不敢,“7斤2两,可真会长,把你俩的优点全扒拉走了!” 外甥女笑出声,手轻轻搭在孩子背上拍着,动作熟稔得不像头回当妈:“你以为呢?从阵痛开始到生,我硬是咬着牙没哭一声,就等着他出来给我长脸呢。” 她说话时,我才瞥见她手背上还贴着输液贴,青了一小块,估计是昨天挂缩宫素扎的。可那点青,哪盖得住她眼里的光——亮得像揣了两盏小灯笼,以前她跟我吐槽孕晚期腿肿得穿不上鞋时,眼里可没这光。 “累坏了吧?”我把小米粥盛出来,吹了吹递过去,“我熬了俩小时,你趁热喝。” 她接过去抿了一口,突然低头亲了亲孩子的额头,声音软得像棉花:“不累。你都不知道,他刚出来那会儿,护士把他抱到我胸口,那么小一只,闭着眼抓着我手指头不放,我当时就想,以前怕疼怕麻烦的那个我,好像一下子就长大了。” 阳光从窗户缝里溜进来,刚好落在孩子闭着的眼睫毛上,金闪闪的,像撒了一把碎星星,连带着空气里飘着的、她特意让姐夫买的百合香,都软乎乎的。 我突然想起她小时候,摔破膝盖坐在地上哭,非要我吹三下才肯起来;想起她高考失利,躲在我家沙发上啃面包,说“姨,我是不是特没用”;想起她结婚那天,穿着婚纱朝我挥手,眼眶红得像兔子——那些画面里的小姑娘,怎么就突然成了能护住另一个小生命的妈妈了? 是不是每个妈妈都是这样?前一天还在跟我吐槽孕晚期睡不好,翻个身都费劲,第二天就能抱着孩子笑得一脸满足,好像生孩子受的那些罪,都被怀里那声轻轻的呼吸给抹平了? 外甥女喝着粥,突然抬头看我:“姨,你看他耳朵,像不像我小时候?” 我凑近了瞧,还真像——耳廓圆圆的,耳垂厚厚的,跟她婴儿时期照片里的模样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像!太像了!”我忍不住笑,“这就是血脉吧,不用说话,一根头发丝都带着记号。” 她低头又亲了亲孩子的耳朵,动作轻得像怕碰碎琉璃:“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妈妈’这词离我远,现在抱着他,才知道这俩字有多沉,又有多暖。” 临走时,姐夫提着刚买的果篮回来,推门带进一股冷风,外甥女下意识把孩子往怀里紧了紧。我站在走廊里回头看,302的门缝透出暖黄的光,隐约还能听见她小声哼着跑调的儿歌。 走廊依旧空荡荡的,瓷砖地反射着冷光,可我心里那点因为“医院”俩字冒出来的紧张,早被刚才屋里那团暖烘烘的人气烘得没影了。 原来热闹不一定要人挤人,有时候,一个新生命的呼吸,就能填满一整个房间的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