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离开黄埔军校时,只有一位学生敢冒死前来送行,这在当时是比较难得的,这一位学生后来还成为了国军名将,成为了我军在西北战场上的主要对手。 黄埔那会儿,天热得烦人,教室闷得像蒸笼,地上的灰尘一拍就飞。周 恩来穿着旧制服,站在讲台上,声音不高,神情倒是清清楚楚的。 课讲得不激昂,但能听进去,讲组织,讲人心,讲政治不是喊口号。坐在下头的学生多半年轻,胡宗南也在,坐得笔直,记得很勤快。有人打瞌睡,有人偷偷看枪械图,胡宗南不看别的,就听那人说话。 周恩来没急着跟人拉近,他讲话讲得慢,常常停顿。 胡宗南时不时去找他,问问题不拐弯。周也不藏着掖着,反问他:“你想清楚了吗?”说完就泡茶,茶叶在杯里浮上浮下,几句对话,算是听懂了个脉络。 两人关系就这么搭上了。 不是师徒那种贴身的教,不是朋友那种常来常往,就是彼此知道彼此在想什么。 胡宗南有点较真,对谁都不太放低姿态,跟周却从不端着。周也从没当他是听话学生,讲事就事。那时候黄埔校内气氛开始变了,风向从门口卫兵的眼神就能看出来。 谁跟谁走得近、谁去哪开会,哪天讲话变得小心了,都能感受到。 蒋介石开始排斥共产党人,周恩来在黄埔的位置越来越不稳。 有人说他要走了,走得安静,没有通知,没有送别。 黄埔那么多学生,平日里叫他老师的,不在少数,真敢露面送一程的,只有胡宗南一个。 他那天什么也没说,打着伞,站在校门口。 周恩来走出来,身上没带多少东西。两人碰了面,没寒暄,胡宗南只说一句:“老师,走好。” 周看着他,点头,没说谢谢,也没拍肩膀。 就这么走了,身后没人议论,没人鼓掌,校门口只有雨声。 这事后来还是传出去了。 蒋介石知道了,叫胡宗南过去问:“你去送他干什么?”胡宗南答:“他是我老师。”蒋没追问,点了点头,算是放过了这茬。 从那以后,他们两个,一个走了北方的路,一个留在国军系统。 走着走着就成了敌人。 十几年过去,西安的街道多尘,风一刮能把人脸上的油带下来。 胡宗南那时候已经是大人物了,兵权在手,是蒋介石的心腹将领。听说周恩来要从重庆回延安,途经西安,他主动提出请吃饭。 手下有劝的,说身份不合适,胡宗南没听,说:“老师路过,请一顿饭,有问题?” 这顿饭没多少人。桌上菜不少,动筷的人不多。气氛不热闹,也不紧张,就那种不好形容的安静。说到一半,胡宗南提了一桩旧事,说1935年他在松潘,红军经过那一带,兵力不足,他司令部就在城里,心里实在发虚。 他说:“那时候我就在想,要是被抓了,老师会不会理我?”说完笑了笑,倒了杯酒。 没人接话,连周恩来都只是看了他一眼,轻轻碰了下杯子。 大家都知道他说这话不是想求情,也不是想认错,就是提个往事。说出来,算个交代。饭后送别,胡宗南照例敬礼。 车开远了,他还站在原地。 再见,是在战场,1947年春,胡宗南带大军攻延安。 兵力不少,态势声势也大。延安当时已经是个象征,他觉得自己这一仗要打得硬气。但进城时,红军早就撤走了,留下的只是空屋和几张传单。他站在城里,看着土墙裂缝发愣。 有人凑上来说:“我们拿下了。”他没回头,只说:“晚了。” 后来的战局,越来越不顺。 他打得吃力,补给跟不上,部队情绪也低。人虽在战线前,心却早分了神。那时身边有个机要秘书,叫熊向晖,很稳,不多话,事情做得细。 胡宗南一直用他,信任得很。可没人想到,这人是周恩来安排的,身份藏了多年。 熊向晖从不主动表态,也不插手军务,光是把该抄的电报抄清楚,把该传的传出去。 这人也从不和胡宗南起冲突,甚至没让人起疑。后来被识破了身份,有人问胡宗南:“你真不知道?”他没作答。有人猜他早看出来了,只是没动他。 这事真假谁也说不准。就算知道,他也没动。 这种事在别的将领手里,早是一纸军法了。他偏没动。是不是还念着旧情?没证据,但人都有心,不能说完全没想过。 再过两年,国军退守,胡宗南一路到了西北。 战事节节败退,他自己也知道撑不了多久。有一阵他夜里喝闷酒,把黄埔时期的合照翻出来,边看边皱眉。照片旧了,边缘泛黄,周恩来站在队伍边上,脸模糊,但轮廓还在。 他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又放下,没说什么。 有人说他那晚写下几句话:“人各其路,恩未敢忘。”这话有没有落在纸上不清楚,留在传闻里倒是常有人提起。 周恩来那时已经身在北京,建国事务繁多,整天见人、开会、处理文件。有一次听人讲到西北那边的情形,说胡宗南退得快,形势很不利。 周恩来只嗯了一声,低头翻资料。又有人说:“他曾是您学生。”他抬起头,说:“我记得。” 这一句话之后,没再多提。外头的天暗了,风吹过窗缝,吹得纸页沙沙响。他伸手压住纸角,又继续看文件。 胡宗南后来去了台湾,没再上战场,也没再带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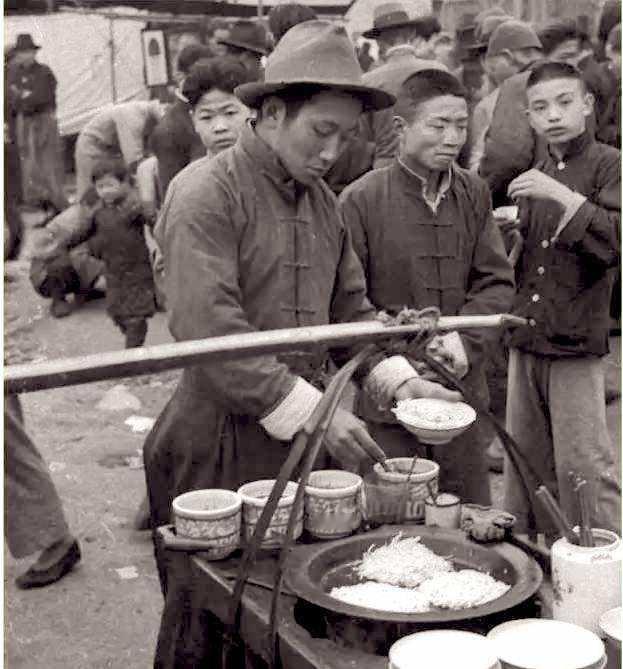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