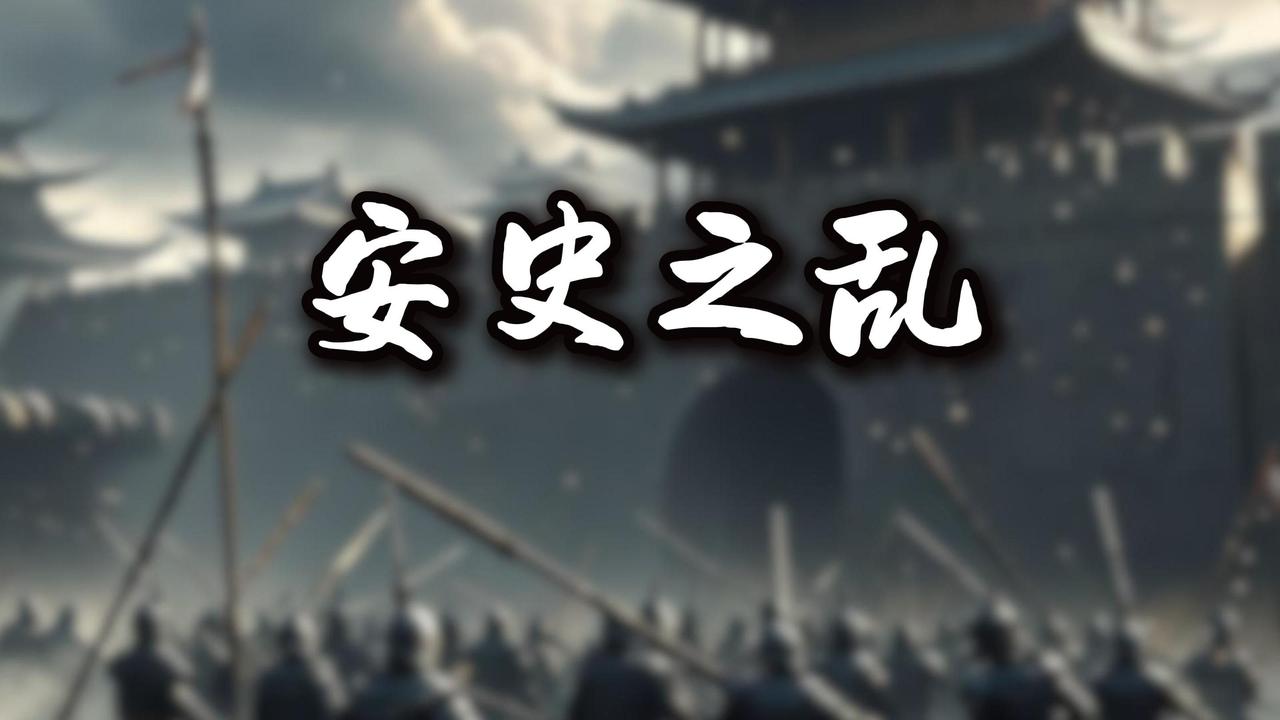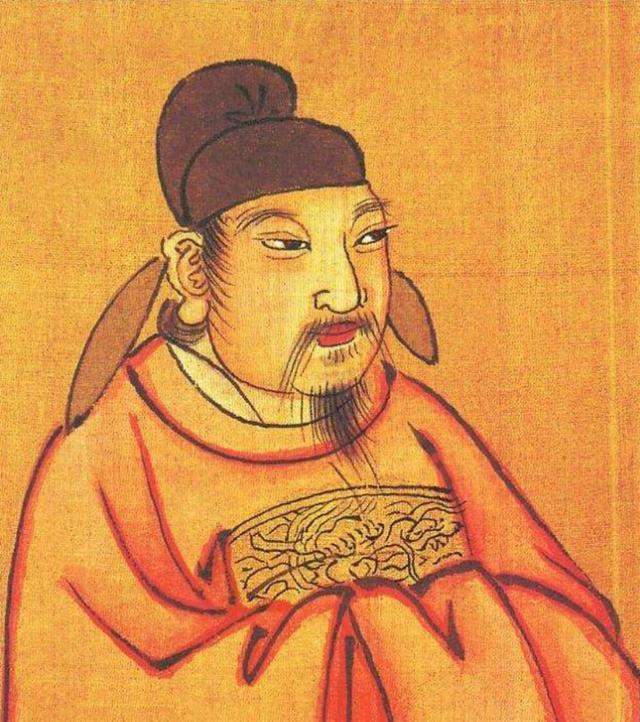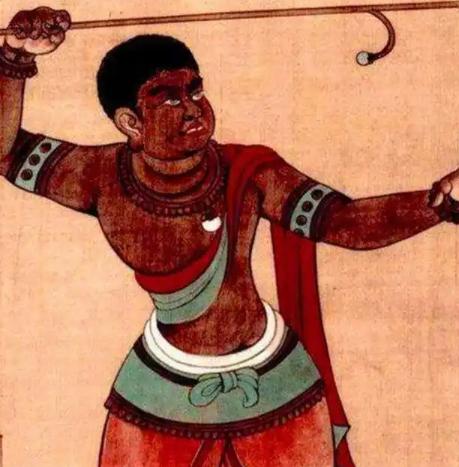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主要是:在唐中宗年间,朝廷在边镇设置节度使,为常设的军事长官。 安史之乱这事,要说根子,就是唐朝把军权给撒出去了,地方上接着了,中央再也收不回来,乱子就这么来的,安禄山反不反,那是个结果,不是原因,他背后那套帝国的玩法,早就跑偏了,该管事的人闲着,能干事的人没人理。 节度使这玩意儿,一开始就是个临时的,边疆有事,派个人去,带着兵,打完了就撤,后来到了中宗玄宗那会儿,味道就变了,开元年间,玄宗嫌换人太折腾,干脆把节度使变成了固定岗位,一个人长期管一大片地,兵权,钱粮,民政,他都能插手。 看着是省事了,其实是中央把自己的权力往外扔,开元末年,全国十来个节度使,手里攥着四十多万兵,有的人一个人就管好几个军镇,手下几万兵马,跟自己家养的差不多,军政财三权合一,活脱脱的地方土皇帝。 中央为什么敢这么玩,玄宗觉得武将搞不懂政治,兵权给他们也翻不了天,有文官压着,中书省那帮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只要朝廷里头稳住,地方上闹不起来,可问题是,那帮人不是不想闹,是没机会闹,安禄山就是踩着这么个空子,一步步往上爬。 安禄山这人,粟特胡人,小时候没妈,在东北边地混出来的兵痞子,但他会来事,嘴巴甜,还特能演,胡语汉语突厥语张口就来,在军队里靠着拍马屁混得风生水起,后来让他碰上了唐玄宗和杨贵妃,命就活了,玄宗就喜欢他这种能演的武将,安禄山装傻充愣,扮忠心,杨贵妃那边他也哄得好,认了干娘,朝里上上下下都当他是自己人。 安禄山造反前,一个人就顶着范阳,平卢,河东三个节度使的帽子,整个北方军事重地都在他手里,十几万兵马,粮草补给,战马基地,全是他自己人管着,自己掏钱养兵,自己搞训练,自己调动,中央想查个账都费劲。 更要命的是,朝廷还一个劲给他加官进爵,李林甫在的时候,心里明白这人有鬼,也懒得动他,算是养虎为患,等李林甫一死,杨国忠跟安禄山就掐上了,矛盾一下就爆了,安禄山本来还想着等玄宗老了再动手,结果杨国忠天天盯着他,扣他军饷,派人监视,还想削他的兵权,安禄山一看这架势,自己再不动手,别人就要动手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他起兵这事也不是一拍脑袋,准备了十几年,就是一场军事政变,755年,安禄山扯着“奉密诏诛杨国忠”的旗号,从范阳带着兵就往南打,号称二十万大军,历史上叫安史之乱,这名头一听就不是临时起意,范阳到长安两千多里地,中间没多少像样的防守,几个月洛阳就丢了,他自己当了燕帝,朝廷调兵,一开始谁也打不过他,大唐攒了几十年的家底,几乎一夜之间就给败光了。 节度使该出兵了,有的节度使根本不动,唐玄宗这才看明白,自己手底下这些兵,压根不是“皇帝的兵”,都是人家各个节度使自己养的,根本指挥不动,有的甚至还跟安禄山有交情,出工不出力,安史之乱一打就是八年,最后虽然平了,唐朝的元气也没了,钱袋子空了,人心也散了,盛世彻底翻篇了。 乱平了之后唐朝怎么办,只能接着让步,把更多的节度使合法化,给地盘给官职,变相把反贼和倒戈的将领收编了,就图个安稳,结果节度使的势力更大了,后来什么河朔三镇,藩镇割据,中央彻底管不住了,皇帝成了个摆设,中晚唐就是宦官,军头,节度使轮流坐庄,开元盛世再也回不去了。 安史之乱的根子,不是安禄山有多厉害,是唐朝的制度自己出了大漏子,节度使制度本来是为了守边疆临时用的,后来统治者自己害怕,慢慢就养成了个自己控制不住的怪物,安禄山只是运气最好,胆子最大,手腕最硬,捡着了这个机会,最讽刺的地方,唐玄宗最信任他,让他住宫里,给他修宅子,派太监伺候他,最后就是他亲手养的兵,把自己的国给砸烂了。 这事根本不是谁好谁坏,是唐朝用一个盛世的幻觉,拖着一个快烂掉的制度往前走,指望用皇帝的个人魅力压住将军,用文官去平衡武将,结果权力早就滑到地方去了,再也收不回来了,安禄山,史思明,哥舒翰,李光弼,郭子仪,这些人打的是半个唐朝的内战,也差点把自己的命都给打没了。 制度从内部垮了,不是农民起义,也不是外敌入侵,最要命的是自己的兵不听自己的话,安史之乱以后,大唐还撑了一百多年,但骨架子已经空了,那场乱,不只是一场战争,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这个帝国最深的那道裂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