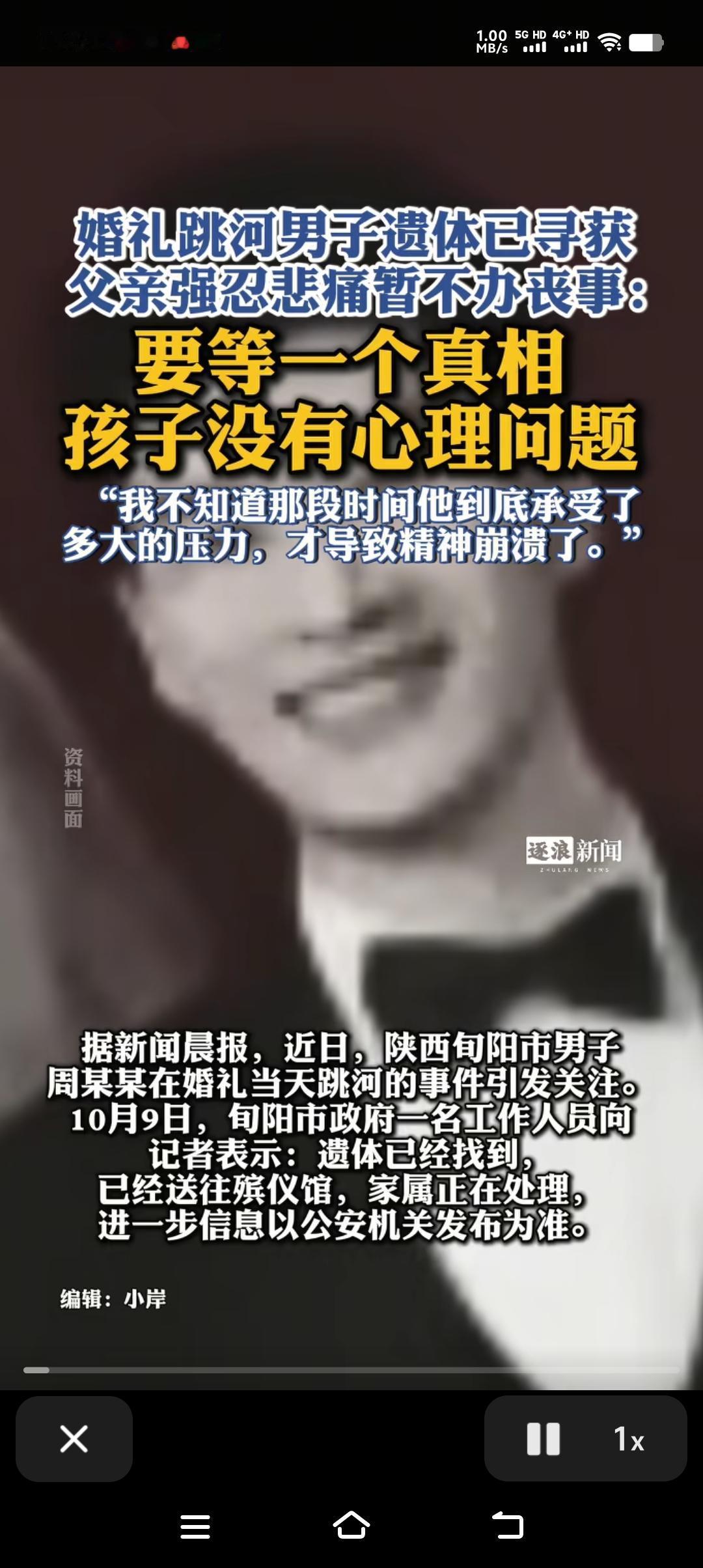[太阳]1998年,何家庆教授前往深山调研,而这段经历充满了磨难,被毒蛇咬、被马蜂蛰,吃猪食、乞剩饭,更不用说被石头割破的腿,肿胀流脓的脚踝……让人不忍直视。 (参考资料:2019-11-04 央广网——一本日记 走近“布衣教授”何家庆) 2019年10月19日,当这位与共和国同龄的教授在合肥走到生命尽头,嘴里还挂念着瓜蒌的收成和瓜农的收益。 如果他能听到,安徽潜山的瓜农会告诉他,虽然雨水少了点,但靠着他留下的技术和产业模式,大家基本没什么损失,一亩地照样能挣上几千块。 这场跨越生死的对话,或许就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注脚,何家庆留下的,远不止一两项致富技术,更是一套完整的扶贫哲学——以科学为犁,以身躯丈量土地,为未来绘制蓝图。 他做科学,有一个特别的“规矩”,他不去追逐那些能让学者声名鹊起的“新物种”,而是把目光牢牢锁定在那些“跟百姓关系密切、能成为脱贫之路”的农作物上。 魔芋和瓜蒌,就是他千挑万选出来的“致富宝”,他不是简单地口头传授,而是硬生生写出了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魔芋的专著《魔芋栽培技术》,后来又有了《中国栝楼》,他把零散的经验,变成了谁都能学的科学体系。 他的科学是开放的,农民找他,不光问魔芋和瓜蒌,金银花、笋干,甚至家里的病猪出了问题,他都倾囊相助,他的专业,是为解决农民的一切难题而存在的。 何家庆的哲学,必须用脚去读,用身体去感受,他的三次“远征”,就是用血肉之躯在中国贫困的土地上刻下的度量衡。 1984年,他孤身一人扎进大别山,225天,步行12684公里,采集了近万份植物标本,成了全面考察那片土地的第一人,也正是在那里,瓜蒌第一次进入他的视野。 1998年,他又出发了,揣着自己16年攒下的27720元钱,独行305天,跑遍大西南8个省区市的426个村寨,他找到了最原始的魔芋,用事实证明这东西原产于中国。 他那本《我的1998何家庆西行日记》,成了理解他的“解码本”,里面没有豪言壮语,只有被毒蛇咬、被马蜂蛰,饿到吃猪食、乞讨剩饭的真实记录。 他的脊柱因为常年背负沉重的行囊而肿胀,甚至不敢触摸,但他心里想的却是,得赶紧去下一个贫困县,帮那里的芋农解决问题,心里才踏实。 他称自己是“一头疲惫不堪的役牛”,这并非自谦,而是他对自己最精准的定位,这头“役牛”源自贫苦的出身,和父亲用账本记下每一笔资助、要求他加倍回报的教诲。 他那身缝补过的中山装,那双褪色的鞋子,还有用橡皮筋固定的眼镜,都是这头“役牛”最朴素的勋章,他甚至要求想跟他去野外的学生,必须先跟着他跑上4个月的步,因为他不愿孩子们也像他一样去冒险。 他想的,从来不是一锤子买卖的“授人以渔”,他的目光,早已投向了技术之外的产业未来。 他敏锐地看到,中国的魔芋产业存在研究成果转化率低、中间产品缺少国家标准等根本性障碍,这些问题不解决,农民的富裕就不可持续。 所以他大力推广“公司+农户”的模式,用自己获得的6项瓜蒌相关国家发明专利,成功撬动了企业的参与,甚至推动企业建立起20多人的科研团队。 这一步,实现了从“教授助农”到“产业助农”的关键飞跃,让扶贫事业有了自我造血的能力。 他晚年还有一个未竟的心愿:建立中国瓜蒌协会。他想用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来系统地推广他的专利成果,让这颗“致富宝”在更广阔的土地上造福更多人,这是一个超越了个人生命长度的构想。 何家庆用一生回答了“知识分子该做什么”这个时代命题,他留下的哲学朴素得惊人:科学要精准地扎根土地,身体要不知疲倦地去丈量,眼光要超越当下,构想未来。 他走了,最后捐出了自己的两枚眼角膜,为贫困的孩子送去了光明,正如他毕生所为,为贫瘠的山区带去了希望之光。 这头“役牛”终于停下了耕耘的脚步,但他犁开的土地上,春意正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