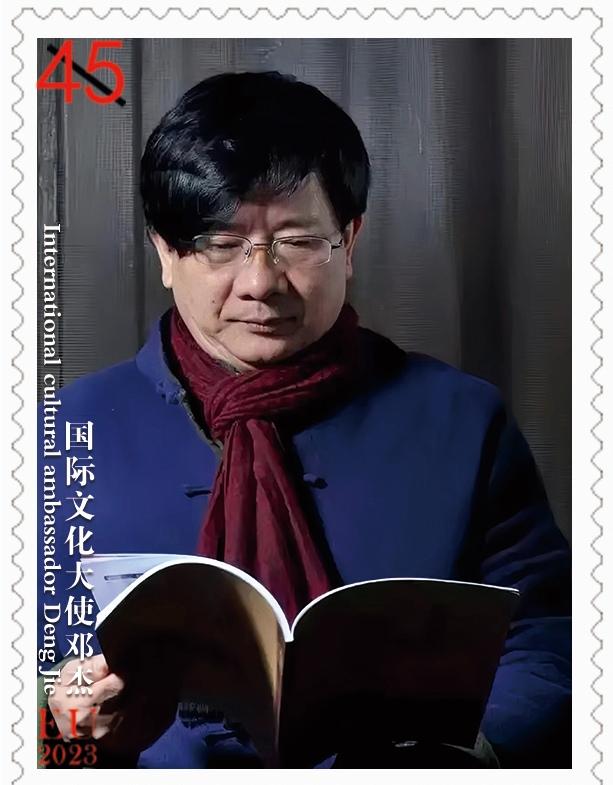邓杰第三部散文集书稿《怕你为自己流泪的季风》之二 《薯香记》 十月的红薯地,是大地写给秋天的情书。墨绿的藤蔓,匍匐成浪,风一吹,便翻出银白的叶底,像一群嬉闹的孩童在互相挠痒……你若来到湘西南五百里红丘陵,轻轻蹲下身,指尖掠过粗糙的叶脉,就能触到泥土下蠢蠢欲动的甜——那种甜,是时光窖藏的蜜,只需轻轻一挖,便会挖出一阵惊叫:那红红的薯儿,成排成排地在薯地展现,宛如一座壮观的由薯阵筑成于大地深处的微型长城! 而最难忘的是小时候的滚薯地——那是一场莽撞的狂欢。我们提着竹篮,踩着松软的泥土,把藤蔓掀得哗啦作响。有人摔进薯垄,往薯地一滚,舒服的很啦!虽然身体沾满了草屑,可是我们的笑声惊飞了田埂上的麻雀。 在漫山遍野的薯地,我们放飞一个完全自我的童年。偶尔,我们饿了,便刨出一个个正在长大的红薯仔解馋,那嫩嫩的薯仔还带着潮气,掰开时立即渗出乳白色的汁水……大人们说,霜降后的红薯最甜!可是,事实上,我们等不及,我们总会在初秋的阳光里偷啃生涩的块根,舌尖被那乳汁蜇得发麻,但心里觉得比喝岩蜜水还欢喜。 我长期住在长沙某个著名的小区里,旁边有一个王公塘农贸市场,如今常常见到市集上的红薯,这些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贩运过来的家伙,艳红得诱人,圆润得如工艺品,可是买回家一蒸,味道不知道寡淡得像一张白纸,让我怎么也寻不到童年时代那口粗粝的甜。 “或许滋味从未改变,只是记忆里的风,总把往事吹得格外温柔。”妻子说得真好,薯香确实承载着湘西南红丘陵上最质朴的乡愁记忆。那些在柴火灶里烤得焦黄流蜜的红薯,或是用红泥巴裹着煨熟的板栗薯,都是都市里鲍鱼、鱼翅无法替代的温暖。 儿时的记忆总与灶台相连:冬日里围炉烤红薯的暖意,勤奋的母亲用竹篮吊在房梁上风干薯干的忙碌,或是饥荒年代红薯粥救命的恩情……这些片段被薯香串联起来,成为漂泊时突然涌上心头的“味觉闪回”。都市的鲍鱼再珍稀,也比不上柴火灶里那捧带着草木灰味的温暖。红薯,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族谱之外的连接土地与血脉的文化脐带。 或许我们该偶尔停下追逐珍馐的脚步,让舌尖重新记住:最动人的美味,往往就藏在红丘陵的炊烟里,藏在红丘陵人家代代相传的灶火中。薯香,承载乡愁,是一种味觉与记忆的双重密码。它不仅是食物,更是故乡的呼吸、土地的体温和时间的刻度。 十月又到了,湘西南的红丘陵上的红薯又到收获季节了。每一颗红薯颗,从贫瘠的土壤里长出,却饱含土地的慷慨。农人弯腰刨土时,指尖沾满的红泥,灶膛里柴火噼啪的声响,薯皮焦黑后露出的金黄甜糯——这些画面,深深地构成了我这个游子心中最原始的乡愁。是的,薯香里,藏着祖辈的汗水,也藏着他们“靠山吃山”的生存智慧,更藏着他们与土地最直接的契约。 2025-10-12 改于鸿铭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