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祖父陶侃有一个极其诡异而奇葩的爱好。 担任广州刺史时,府内的书房在凌晨总是会传出一种特殊的声音。那不是翻阅公文的声音,也不是叹息或低语,而是一种沉重、规律、令人心悸的摩擦声——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被一遍遍地拖拽过心脏。 仆役们私下颤抖地低语:“使君又在搬砖了!” 无人理解,位列封疆的陶侃,为何十年如一日,在拂晓与深夜,将百余块冰冷的青砖从书房内搬到院中,日落后再如虔诚的仪式般,一块不差地搬回原位。 这诡异的“砖瘾”背后,是晋室南渡后最坚实的栋梁。 没有人能质疑陶侃的能力。从广州调任荆州后,他展现出名将的真正风采。平定陈敏、杜弢叛乱,他指挥若定;治理荆州,他令行禁止。某日见下属闲来无事玩弄赌博器具,他当即命人将所有赌具投入长江,厉声道:“樗蒲者,牧猪奴戏耳!君子当正其衣冠,惜其分阴。” 这话语与他“搬砖”的执着如出一辙——他要在这礼崩乐坏的时代,用最笨拙的方式,为自己、为这个王朝建立起不容逾越的秩序。 最辉煌的时刻在苏峻之乱时到来。叛军攻陷建康,挟持幼帝,百官蒙尘。年过七旬的陶侃被推举为讨逆联军主帅。 “父亲,朝廷待我陶家素来凉薄,何必为他们拼尽所有?”长子陶瞻曾如此问道。 陶侃望着江水中沉浮的赌具,如同看着这个浮沉的王朝:“我所效忠的,非是龙椅上那一个两个人,而是这华夏正统,是这片土地上千千万万的生民。” 然而他的忠诚,换来的却是朝廷一次又一次的猜忌。 当年王敦当权,只因忌惮他的才能,便将他明升暗降,调离权力中心,贬至岭南。那一路南下,他看着中原在身后渐渐消失,心如刀割。 即便在平定苏峻之乱、再造社稷后,来自建康的猜忌依然如影随形。某日深夜,亲兵送来密报——朝中有人诬告他“拥兵自重,意图不轨”。陶侃笑了,那笑声苍凉如夜枭。他走到院中,开始一块块地搬动那些青砖。肌肉在抗议,关节在呻吟,但唯有这种纯粹的痛苦,能让他确信自己还保持着清醒。 “使君,何苦如此?”老部将看不下去。 “北方未复,中原未定,”陶侃喘息着,又将一块砖垒上,“我若耽于安逸,他日有何面目见先帝于九泉?” 咸和九年(334年)的春天,陶侃病重。 他已位极人臣,官至太尉、大将军,封长沙郡公。但每当晨曦微露,他仍会示意侍从扶他起身,目光望向书房角落那些陪伴他多年的青砖。 每一块砖都是一段记忆: 那块边缘泛黑的,是当年在荆州整顿军备,日夜督造战船时,被炉火熏燎的印记; 那道深刻的刻痕,是得知爱子陶瞻在抵抗苏峻叛军时战死沙场时,他以指甲生生抠出的痕迹; 那些细密的纹路,像极了长江的波浪,承载着他无数次率水师巡防的往事…… “搬…”他虚弱地抬手。 儿子们含泪将砖块一块块挪到他面前。老将军的手一一抚过,如同抚过自己为这个王朝征战的一生。 “朝廷…”他喃喃道,目光渐散,却依然望向北方——建康的方向,洛阳的方向,那个他毕生守护却屡屡伤他的晋室所在。 陶侃死后获极尽哀荣,但这一切对他已无意义。 他就像那些被他搬动了一生的砖石——朝廷需要时,他是筑起高墙的基石;猜忌来时,他便是被随意搬动的物件。但他自己,却始终恪守着作为臣子的本分,从未动摇。 青砖沉默,承载着大厦将倾时的最后坚持。而那日复一日的搬砖声,最终成为了一代名将献给一个不值得的王朝最悲壮的挽歌——他用近乎自虐的忠诚,为自己砌就了一座无字的丰碑。 他的一生,就像那百余块砖。朝廷可以随时将他搬来挪去,用时置于中流砥柱,闲时置于角落积尘。但他自己,却始终恪守着作为“基石”的本分,坚定不移地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晋室江山。 这,就是陶侃的悲剧——一场以天下为舞台,以忠诚为信仰,在猜忌与奉献中燃烧殆尽的,伟大的孤独史诗。 也许,目睹伟大的祖父寒透了心,导致陶渊明选择了一生彻底躺平?陶侃 陶渊明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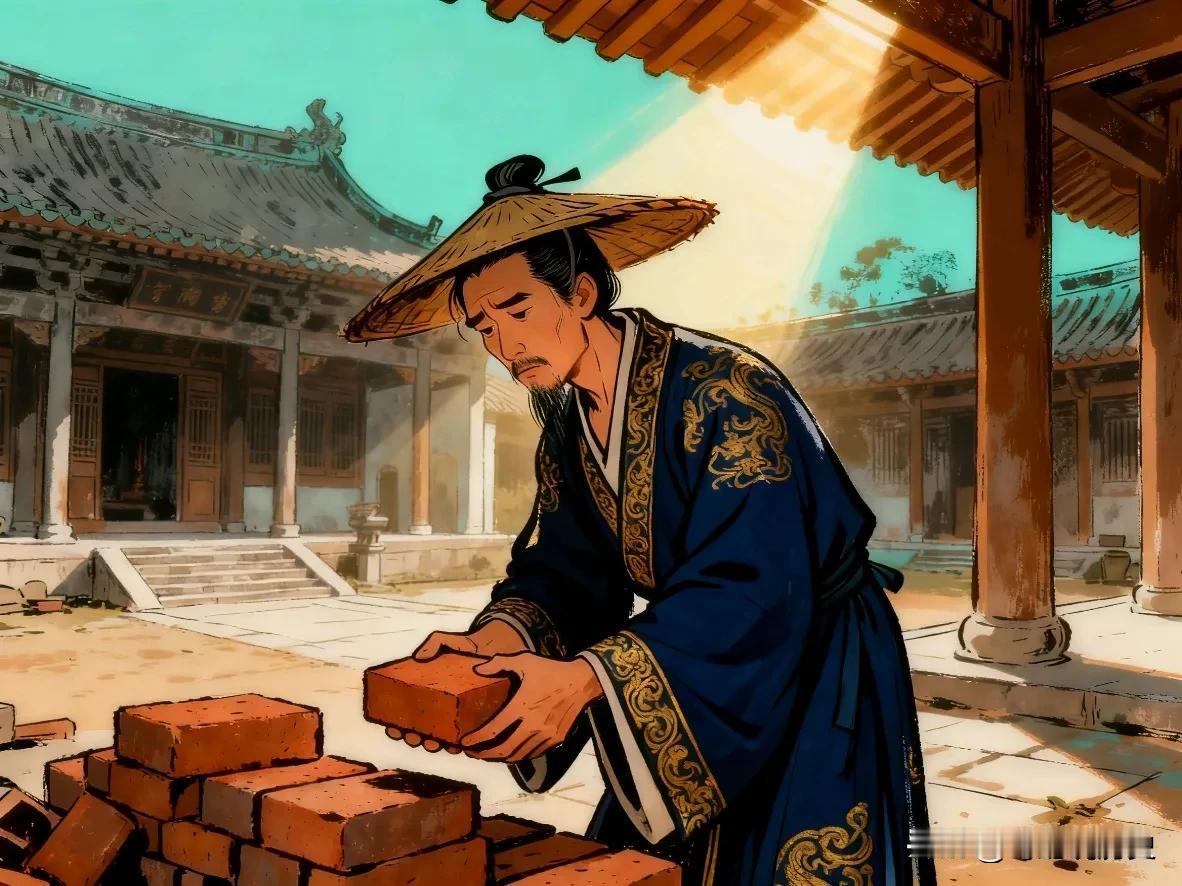




![刘太公的太上皇是封的,可不是打下来的[吃瓜]](http://image.uczzd.cn/701054539546715138.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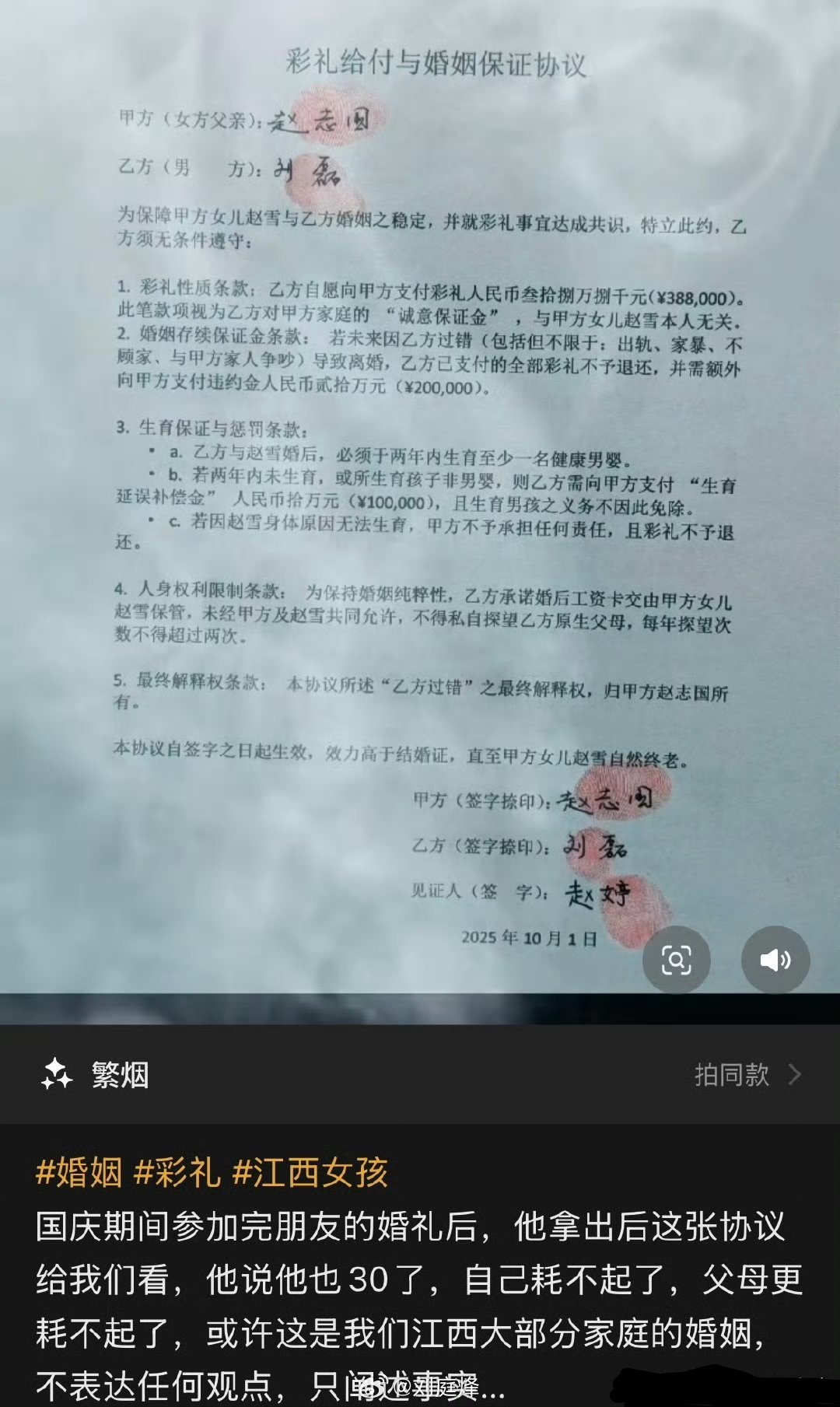



用户17xxx68
搬砖的典故来源
冰川
他发明了麻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