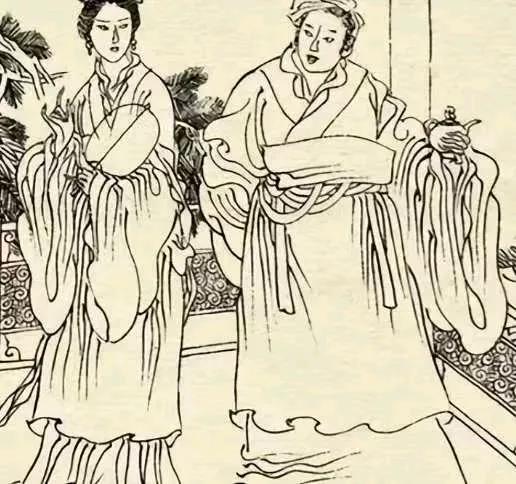北宋的军队有一个习俗,打仗时为了让士兵卖命,必须当场给予丰厚的赏赐,这样的习惯导致在与金国交战中,因为犒赏迟迟没有到位,将士们知道后,他们纷纷放下了武器,四散逃去。 要说这奇葩的习惯,根子还得从大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那儿找。老赵家怎么得的天下?“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说白了,就是手握兵权的将军造了反。这事儿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他坐上龙椅后,天天琢磨的,就是怎么防止手下那帮兄弟也学他来这么一出。 于是,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摆了顿酒席,和石守信这些老哥们儿喝着酒、唱着歌,就把兵权给收了回来。那怎么安抚这些功臣呢?赵匡胤的方法简单粗暴:给钱、给地、给豪宅,让他们回家当富家翁去。 这一手,直接给整个宋朝的军事制度定了调:武将的权力必须被限制,而他们的忠诚,可以用物质财富来换取。 从此,宋朝的军队文化就变了味儿。当兵不再是为了保家卫国,更像是一份高风险、高回报的职业。朝廷用优厚的军饷养着庞大的军队,打仗胜利了,更是有数不清的赏赐。这种风气下,士兵们对朝廷的忠诚,渐渐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交易。 仗打得越狠,赏钱就越多。打了胜仗,皇帝的赏赐流水一样地送到军营,金银、绢帛、美酒、牛羊,应有尽有。甚至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监军会抬着成箱的银子在阵前督战,谁砍下一个敌军首级,当场就领一份赏钱。这叫“阵前犒赏”,刺激得士兵们嗷嗷叫着往前冲。 这方法不是挺好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没错,在国库充裕、小打小闹的时候,这招确实管用。但问题是,一旦这种“交易”成了习惯,成了理所当然,军队的血性就被金钱腐蚀了。将士们打仗的动力,不再是家国情怀,而是白花花的银子。忠诚一旦可以用金钱衡量,那当金钱不到位的时候,忠诚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颗雷,终于在北宋末年爆了。 公元1126年,金军第二次南下,几十万大军把北宋的都城汴京(今天的开封)围得水泄不通。史书上管这叫“靖康之变”,是汉人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当时城里号称有几十万禁军,可真正打起来,却是一触即溃。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一个细节,特别能说明问题。 当时守城的宋军将领叫李纲,是个主战派的硬骨头。他带着军民拼死抵抗,金军几次攻城都被打了回去。可城里的宋徽宗、宋钦宗这对父子皇帝,早就吓破了胆,一心只想求和。他们一边跟金军谈判,一边却干了件蠢事——克扣守城将士的犒赏。 打仗是要花钱的,尤其是这种守城血战。按照宋军的老规矩,每次击退敌人,或者有什么英勇表现,都得立刻发赏钱。可那时候,朝廷的钱早就被徽宗皇帝拿去修园子、买奇石,挥霍得差不多了。国库空虚,拿不出那么多钱来犒赏三军。 一开始,士兵们还能凭着一股气顶着。可时间一长,金军围城越来越紧,城里粮食也快没了,大家伙儿饿着肚子,冒着生命危险在城墙上跟金兵肉搏,回头一看,说好的赏钱却迟迟不见踪影。 人心,就这么散了。 根据《三朝北盟会编》里的记载,当时城里的气氛非常诡异。将士们私下里议论纷纷:“咱们在这儿卖命,连抚恤金都拿不到,凭什么?” 军官们去催款,管后勤的官员两手一摊:“没钱,你们找官家要去。” 终于,在一次金军发动总攻的时候,矛盾彻底爆发了。当催战的鼓声响起,城墙上的许多宋军士兵,非但没有拿起武器,反而开始鼓噪,公开索要赏钱。 有的甚至直接对着皇宫的方向大骂。监军的太监急了,连声许诺说赏钱马上就到,可已经没人信了。 最致命的一幕发生在守将郭京身上。这家伙是个神棍,吹牛说自己会“六甲神兵”之术,能撒豆成兵。钦宗皇帝病急乱投医,竟然信了他,把城防交给他。郭京开了城门,带着一群乌合之众出去“作法”,结果可想而知,被金军一顿乱杀。城门大开,金军蜂拥而入。 城里的宋军呢?在看到郭京作法失败、城门洞开的那一刻,彻底崩溃了。他们想的不再是抵抗,而是逃命。许多士兵扔下兵器,脱掉盔甲,混在老百姓里四散奔逃。 他们跑的,不是因为怕金兵,而是对这个连赏钱都发不出的朝廷彻底绝望了。一个靠金钱维系的军队,在金钱链条断裂的那一刻,也就失去了所有的战斗意志。 靖康之耻,两个皇帝被人家像牵羊一样掳走,皇后公主、文武百官,数千人被押往北方,受尽凌辱。繁华的汴京城被洗劫一空。这背后,是军事的无能,是外交的失败,但归根结底,是这个王朝从根子上就出了问题。 用钱来买忠诚,就像在沙滩上盖楼,看着风光,一个浪头打过来就全塌了。 一支军队真正的灵魂,绝对不是金钱,而是信仰、是荣誉感、是对这片土地和人民深沉的爱。当士兵们知道自己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时,他们才能在最绝望的境地里,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他们的故事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如果把一切都变成交易,那它离灭亡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