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河南一男子蹲在集市摊位前,上下打量一枚小巧的玉兔许久,摊主以为大生意来了便说道:“这枚玉兔没有200元,我不卖。”接下来男子的话让摊主面红耳赤,不知如何是好。 安阳老城护城河边的集市,在大早上正是热闹的时候。 青石板路上支着各式各样的摊位,到处传来的都是讨价还价声。 就在这嘈杂里,一个穿蓝布衫的年轻人蹲在木板摊前,盯着枚玉兔看得入神。 摊主见他半天不言语:“小伙子,这玉兔可是好东西,没二百块不卖!” 这年轻人叫赵涛,二十二岁,刚从郑州大学历史系文物鉴定专业毕业。 要懂这枚玉兔的缘分,得先看赵涛的“底子”。 他生在安阳老机械厂的工人家庭,父亲修机器时总把旧零件码得整整齐齐,母亲纳鞋底时会把碎布按颜色分堆。 这种刻进骨子里的“讲究”,早早就渗进了赵涛的生活。 打小他就爱往厂区旧书摊钻,捡些带图的旧书翻,看见“商周玉器”“唐代金银器”的字眼就挪不动腿。 高中时煤油灯下抄《中国通史》,铅笔头在草纸上磨秃了三支。 上大学后,他也是认认真真的看仿古玉样本。 毕业那年,他在省图书馆借了本《唐代工艺史》,翻到“玉器”章节时突然拍大腿。 书里说,唐代宫廷流行用和田青玉制镇纸,多刻瑞兽纹,因“玉质缜密,久用不损”最得文人青睐。 合上书页时,赵涛摸着兜里攒了三个月的工资,心里动了:“要是能在民间寻到一件,该多好?” 这念头刚冒出来没几天,就遇上了集市上的“缘分”。 那天他揣着从同学那借来的五十块钱,在护城河集市转悠。 摊位上的东西杂得很,有青铜镜,有瓷碗,还有汉简。 他蹲在一个卖杂项的木板摊前,目光突然被枚玉兔勾住了。 青绿色的玉质泛着温润的光,长八厘米、高四点五厘米,兔身伏卧,双耳后竖,前爪蜷曲,尾巴短得像团绒球。 “小伙子,看上这个了?”摊主是个精瘦的中年人。 “这玉兔可是从老坟头挖出来的,最低二百!” 赵涛没接话,仔细观察玉兔表面的沁色。 黄中透青,是土沁和铜沁混合的痕迹,符合唐代玉器“出土千年,色如蒸栗”的特征。 再看底部,隐约有行小字:“贞观廿三年秋,尚工张盈造”。 他用袖口擦了擦,字迹更清晰了。 这是唐代少府监尚工署的款识,专给宫廷制器的工匠名号。 摊主见他不说话,急了:“二百是良心价!你要是嫌贵,我再搭个青铜小镜子?” 赵涛这才抬头:“大叔,您这玉兔要是唐代的,别说二百,五百我都收。” 摊主愣了:“你当这是菜市场?随便开价?” 赵涛没争辩,拿出了五十块钱:“我只有这么多,您要是愿意,我明天再送钱来。” 摊主盯着他兜里露出一角的笔记本,又看看玉兔底部的款识,突然蔫了。 “行吧行吧,就当交个朋友。” 赵涛数出五十块递过去,把玉兔用软布包好,塞进衣袋里。 回到宿舍,赵涛用放大镜对着玉兔看了三天三夜。 他还翻《唐六典》查“少府监”的职责,对照《中国玉器全集》里的唐代标本,甚至骑了两个钟头的自行车,跑到省博物馆找老专家请教。 老专家戴着老花镜直点头:“这沁色是自然形成的,雕工是唐代典型的‘圆雕法’,底部款识也对。贞观廿三年,正是唐太宗驾崩那年,这玉兔说不定是宫里赐给哪个大臣的。” 为保险起见,赵涛又跟着省考古队去了趟西安。 他又去了碑林博物馆,拓下唐代墓志铭里的“尚工张盈”条目。 果不其然,这位张盈在史书里有记载,是贞观年间的制玉高手。 三个月后,赵涛带着玉兔回了安阳。 他写了篇《唐代宫廷玉镇初探》,附上玉兔的照片和检测数据,寄给了《文物》杂志。 玉兔的名气越来越大,不少人找到赵涛,说要出高价买。 有收藏商专门找来:“十万块,这玉兔我包了”。 赵涛都摇摇头:“这玉兔是国家的,我不过是替它找了个临时的家。” 1978年年底,他把玉兔捐给了河南博物院。 捐赠仪式那天,馆长直夸奖:“小赵啊,你这可是给国家留了件宝贝!” 赵涛挠挠头:“我就是个搞文物研究的,这些东西放在我这儿,睡不踏实。放博物馆,每天有那么多人看,才算没白找。” 后来,这枚玉兔成了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 而赵涛呢?他后来成了大学教授,教文物鉴定课。 课堂上,他总爱拿着这枚玉兔的照片说:“文物不是死的,它们是有温度的。每一件文物背后,都藏着一段人情冷暖,一段家国记忆。我们守护文物,其实是在守护我们的根。” 就像老辈人常说的:“是金子总会发光。” 可有些东西,比金子更珍贵。 那是刻在骨子里的热爱,是融入血脉的责任,是一个普通人对文明的守护。 主要信源:(中国甘肃网——传承千年的玉石文化——探寻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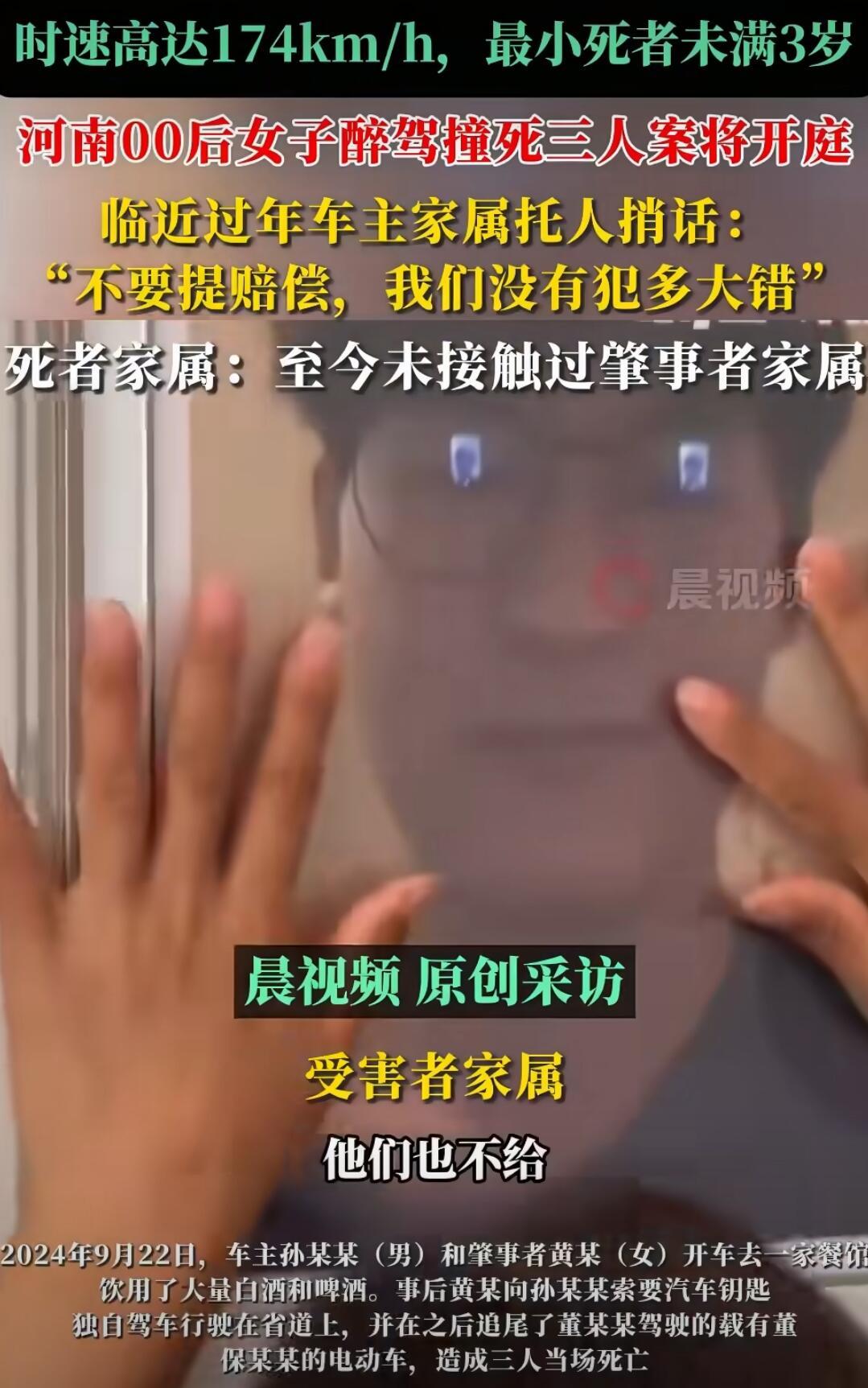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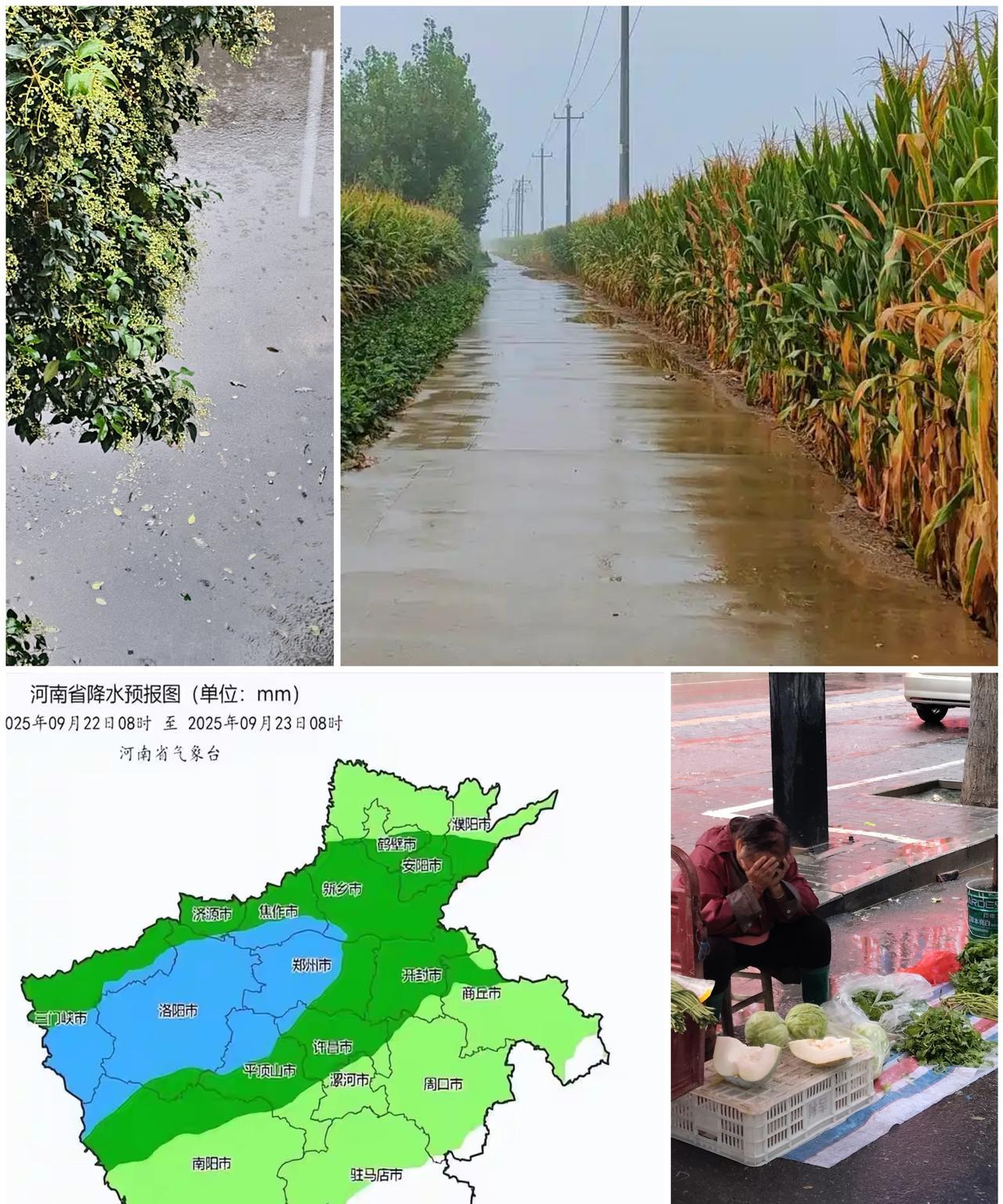


喵喵呜哒
不地道,没有还摊子15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