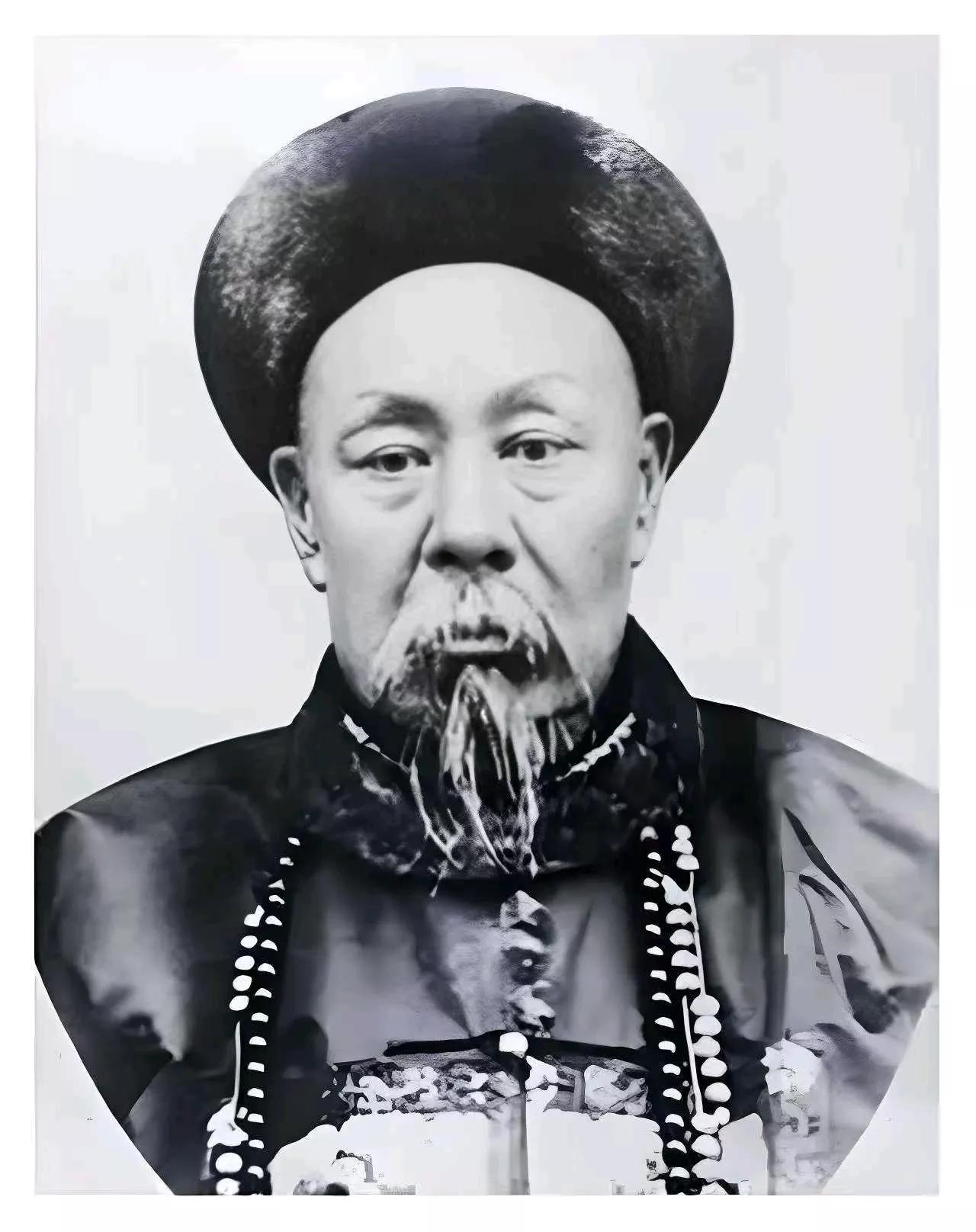道光十七年,两江总督陶澍回安化老家祭祖,途中停留醴陵县。总督大驾,醴陵县令受宠若惊,他来到渌江书院,找到在书院担任山长的左宗棠,求墨宝一副,送于陶澍 那天渌江书院里的桂花开得正盛,左宗棠刚给学生讲完《论语》里“为政以德”的章节,就见县令的轿子停在书院门口。县令下轿时额头上还沾着汗,一见到左宗棠就快步迎上来,手里攥着块帕子不停擦手:“季高先生,可算找着您了!陶总督明日就要到醴陵,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想求您写副对联,给总督大人添点雅兴,也让咱们醴陵露个脸。” 左宗棠当时才三十出头,虽在书院里名声响,可在官场没什么门路。他看着县令急得团团转的样子,又想起陶澍在两江办漕运、改盐政,实实在在帮百姓办了不少事,便点头应了:“总督是办实事的官,这墨宝我得好好写,不能怠慢。” 回到书房,左宗棠磨了半盏茶的墨,铺开本地产的竹纸,却没急着下笔。他坐在窗前琢磨,陶总督一路从江南回来,见惯了繁华,也经了不少民生事,对联里不能只写客套话。想着想着,就想起前阵子听百姓说,陶澍在江苏修了不少水利,让庄稼少受了洪涝,又想起醴陵本地的渌江码头,往来商船全靠这水脉活计——不如就从“水”和“政”上做文章。 提笔时手腕稳如磐石,笔锋落纸沙沙响。上联写“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说的是当年陶澍在京城受道光帝召见,二十年来始终记着家乡安化的“印心石屋”,不忘本;下联配“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既点出陶澍总督两江、管着八州百姓的身份,也写了湖南子弟盼他荣归的心意。写完又看了遍,觉得字里少了点力道,又重新铺纸写了一遍,直到墨色浓淡相宜,笔锋里透着股刚劲才作罢。 第二天陶澍的船队到了醴陵,县令赶紧把对联挂在迎宾馆的正堂。陶澍刚进门,目光就落在了对联上,先是站着读了两遍,眉头慢慢舒展开,又走近了些,指着“印心石在”四个字问:“这字写得有骨力,内容也合我心意,是谁的手笔?” 县令赶紧回话:“是咱们渌江书院的山长左宗棠,左季高先生写的。这人学问好,教出来的学生也懂礼,就是性子直,不爱跟官场人打交道。” 陶澍一听来了兴致:“有学问还敢说直话,这才是真人才。快请他来见我,我倒要跟他聊聊。” 左宗棠接到消息时,刚给学生改完策论。他换了件干净的青布长衫,没带随从,自己步行去了迎宾馆。见到陶澍,他没像旁人那样躬身行礼,只作了个揖:“晚生左宗棠,见过总督大人。” 陶澍倒不介意,拉着他坐在桌边,先问起书院的事,又聊到醴陵的农田水利。左宗棠说起本地渌江年年涨水,冲坏不少田地,提议在下游修个水闸,既能防洪又能灌溉,说得头头是道。陶澍越听越点头,最后拍着他的肩膀说:“季高啊,你这脑子装的不是死学问,是能帮百姓办事的真法子。我在两江办漕运,缺的就是你这样懂民生、敢做事的人。” 那天两人聊到日落,陶澍留左宗棠吃了晚饭,临走时还送了他一本自己编的《海运全案》,摸着书皮说:“这里面记的是我办海运的经验,你要是不嫌弃,就拿去看看,往后有想法,随时给我写信。” 后来陶澍回安化祭祖,特意绕路又去了趟渌江书院,跟左宗棠聊了三天三夜,从湖南的风土人情聊到国家的边防要务。临走时,陶澍还跟县令说:“左先生是璞玉,得好好待他,将来定是能担大事的人。” 再后来,左宗棠果然没让人失望,平定西北、收复新疆,成了晚清的栋梁之臣。有人问他早年最难忘的事,他总说:“道光十七年在醴陵见陶文毅公(陶澍谥号),那回聊天,才让我知道学问要用到实处,才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家国。”而渌江书院那副对联,后来被人刻在了石碑上,成了当地一段“伯乐识千里马”的佳话。 (根据《清史稿·陶澍传》《左宗棠年谱长编》及醴陵地方文史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