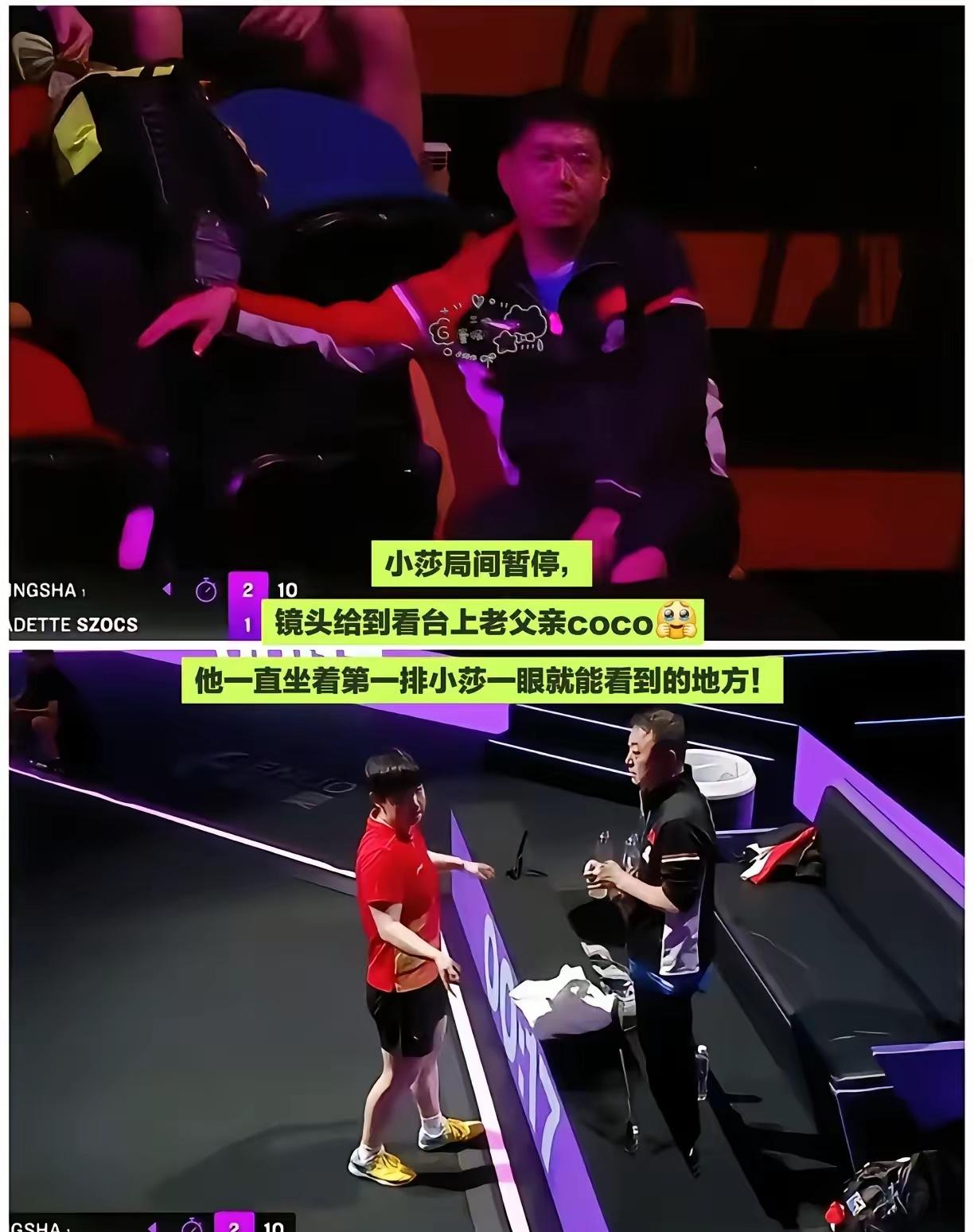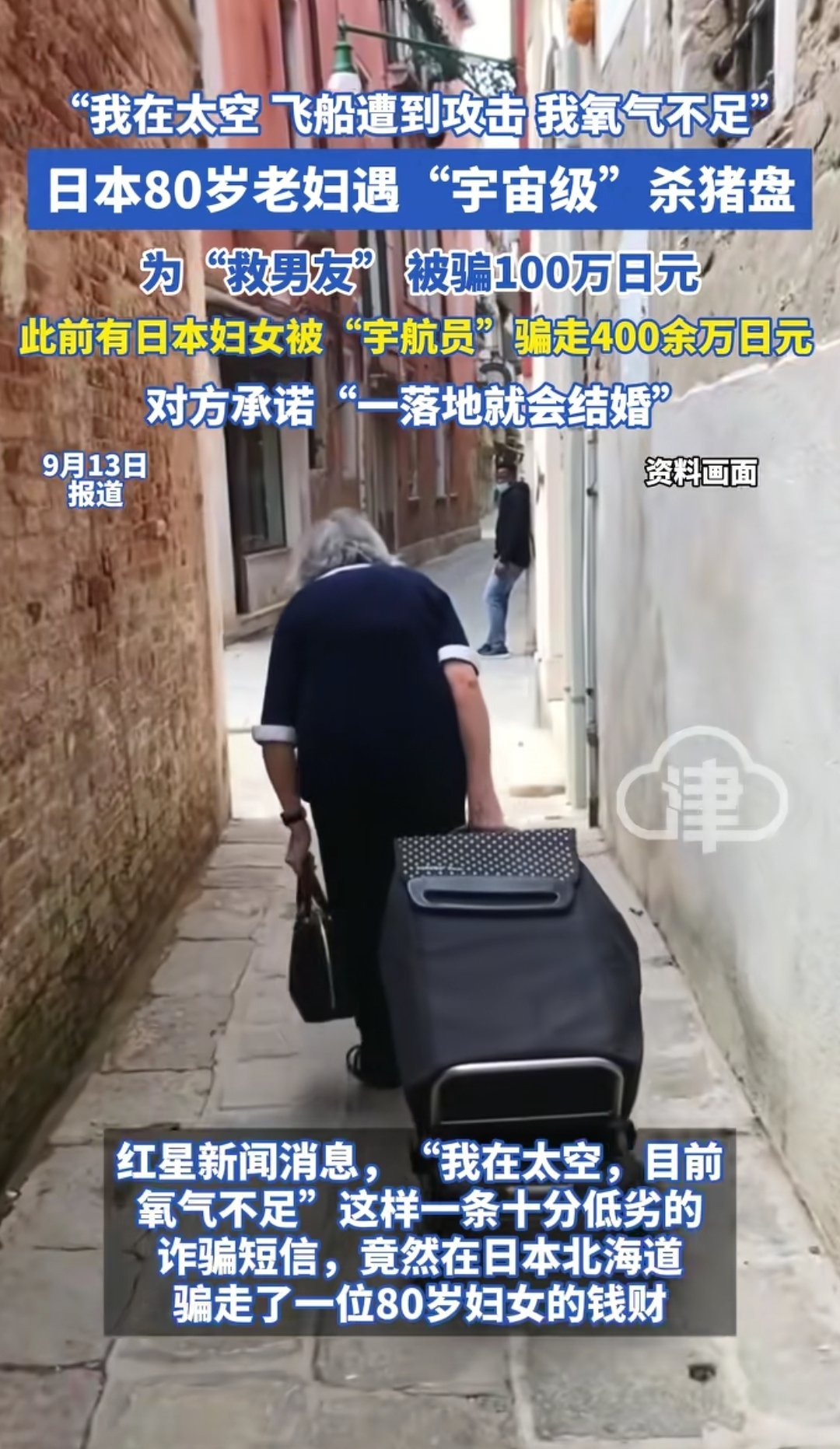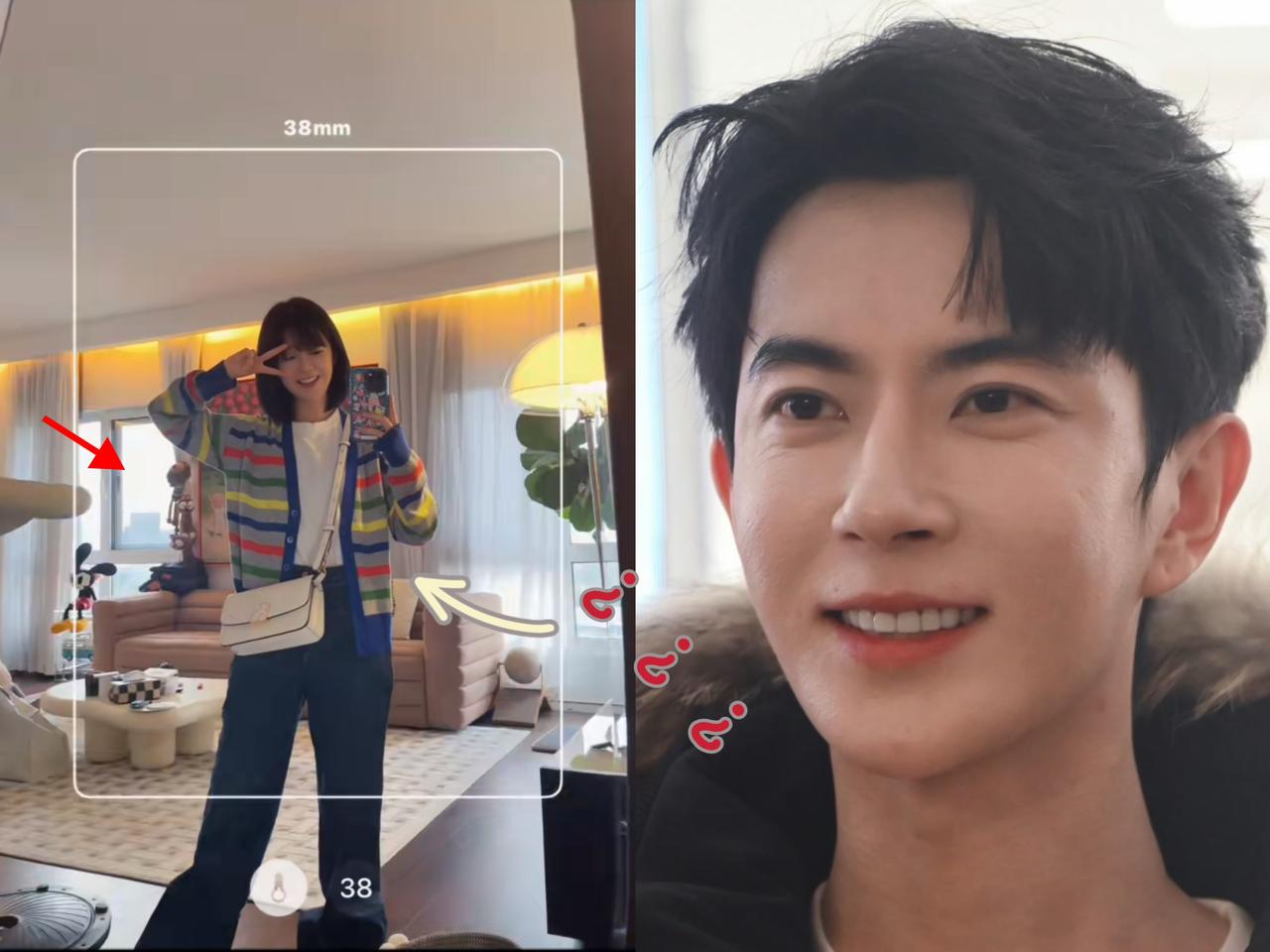嘉靖年间有个郎中,给一位老者把脉。然而,在把脉过程中,郎中奇怪地发现,老者脉象奇特,根本不像是常人浮、沉、迟、数、虚、实等几种脉象之一,于是郎中问道:“老先生,你...恐怕不是人吧。” 这话一出口,诊室里的空气都像冻住了。郎中陈敬之的手还搭在老者腕上,指腹下那若有若无的触感更明显了——既不像活人的脉那样带着气血流动的力道,也不像死人的脉那样僵硬不动,倒像是晨露落在草叶上,稍碰就散,却又总在指尖绕着一丝凉意。他后背早沁出了汗,眼睛盯着老者的脸,就怕对方突然变了模样。 可老者没恼,反倒捋着下巴上的白胡子笑了,笑声像风吹过松枝,沙沙的带着股清劲。“陈先生莫怕,我没害人的心思。”老者说着,抬手拂了拂袖口,陈敬之瞥见他袖口沾着点松针,翠绿得不像这个时节该有的颜色——毕竟此时已是深秋,城外山上的松树早该显了老态。 陈敬之咽了口唾沫,慢慢收回手,又给老者倒了杯热茶:“老先生若是...有难处,不妨直说。我从医二十年,虽没见过您这样的脉象,可治病救人的心思是真的,绝不会对外声张。” 老者端着茶杯,却没喝,只望着杯里的热气出神。“我本是城外翠屏山的一棵老松,活了快一千年了。前些年山下闹瘟疫,我看着村民受苦,便抖落些松针,让路过的樵夫带下山,煮水喝能防瘟疫。后来见人间日子太平,就常化成人形来镇上逛逛,也学些人间的道理。” 他顿了顿,抬手按了按自己的胸口,声音轻了些:“可这半年来,山北来了伙砍树的,不光砍杂木,连百年的老松也不放过。我为了护着身边几棵小松,硬扛着斧头挡了几次,耗了太多元气,近来总觉得身子发虚,连化形都费劲。听镇上人说陈先生医术好,就想来求副药,没想到刚把脉就被你识破了。” 陈敬之这才明白过来,难怪前阵子总听人说,翠屏山的樵夫上山,总能遇到个穿青布衫的老者指路,还会给迷路的孩子塞野果——原来都是这位“松仙”。他心里的惧意早没了,只剩敬佩,赶紧起身翻药柜:“您护着山林,护着百姓,是大善。我虽治不了‘仙病’,但知道几味草药能补元气,您且等着。” 他从药柜里翻出晒干的柏子仁、茯苓,又找了些山中采的灵芝片,仔细包好:“这几味药您拿回去,若是化形不方便,就把药埋在树根旁,浇些山泉水,药效会顺着根须渗进去。还有,您要是再遇到砍树的,别硬扛,可去县衙报官——上个月新知县刚贴了告示,禁砍百年以上的古树,说要护着一方水土。” 老者接过药包,指尖碰着纸包,竟有淡淡的松香飘出来。他对着陈敬之深深作了个揖:“多谢陈先生。我无以为报,这东西您留着。”说着从怀里摸出个小布包,里面是十几枚圆润的松子,每颗都泛着琥珀色的光。“这是我攒了五十年的松子,您要是遇到久咳不愈的孩子,取一颗煮水喝,比川贝还管用。” 陈敬之收下松子,送老者到门口。看着老者的身影消失在巷口,他才发现刚才老者站过的地方,竟落了两根翠绿的松针,捏在手里软乎乎的,不像普通松针那样扎手。 后来,陈敬之照着老者的话,把药埋在了翠屏山的老松旁。没过多久,就有樵夫说,山上那棵最粗的老松又冒出了新枝,连砍树的人也被县衙抓了,罚了银子还补种了树苗。他也用那些松子救了好几个咳嗽不止的孩子,家长们都来谢他,说他有“仙药”。 陈敬之总跟人说,哪有什么仙药,不过是护善念的“生灵”遇到了肯帮忙的人。直到他老了,还在诊室里摆着个小罐子,装着每年从翠屏山老松上落下的新针——他说这样能提醒自己,行医不光要治身体的病,更要护着心里的善,就像那棵老松护着山林一样。 (根据嘉靖《徽州府志》逸闻篇、清代《草木异闻录》及皖南民间传说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