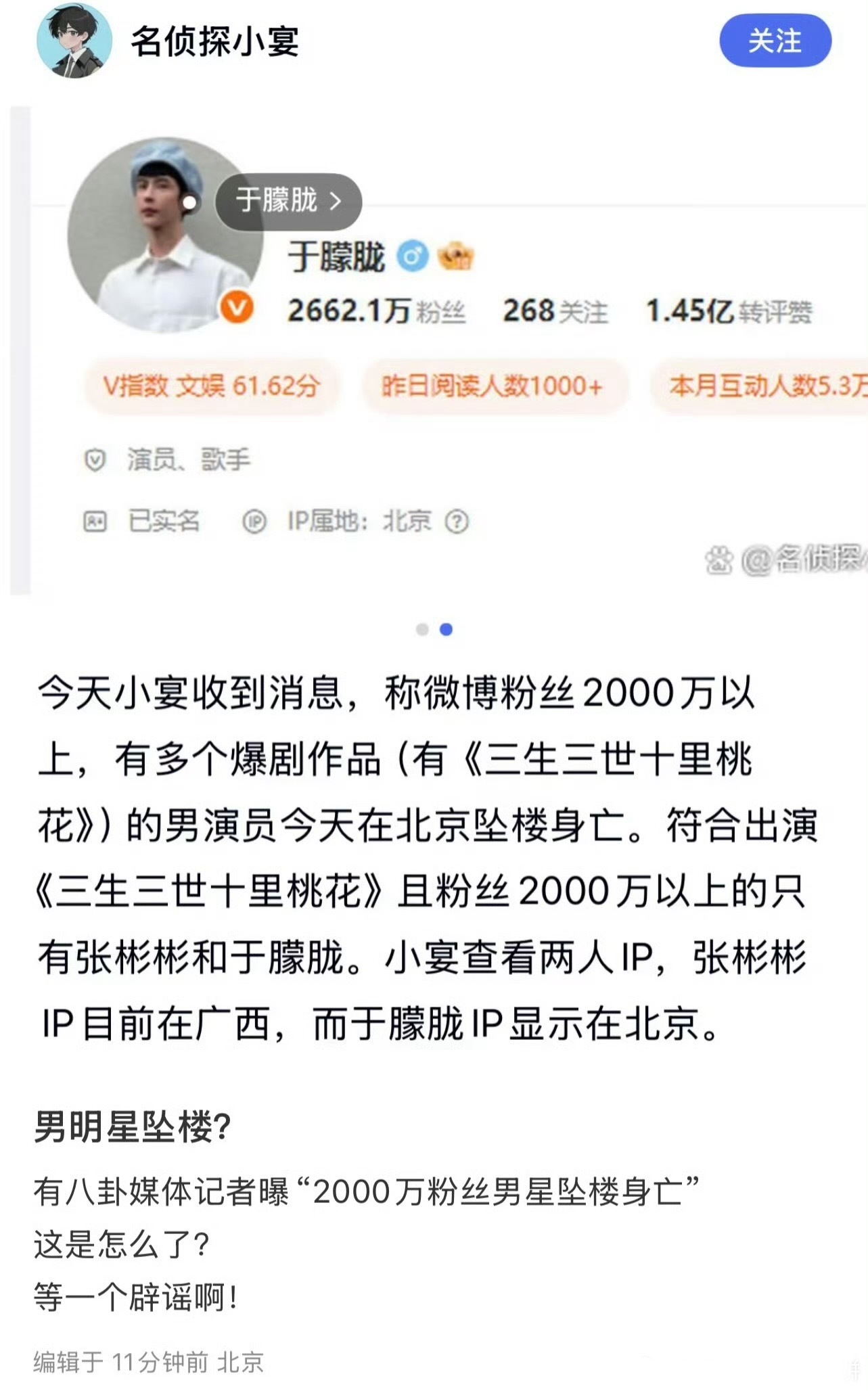2002年,一个陌生男子走进老屋,附下身对刚满6岁的郭麒麟说:“我是你的父亲。”还没等郭麒麟反应过来,他就被送上了一辆从天津开往北京的黑色轿车。 司机一句话没说,一路上车窗紧闭。等车停下,郭麒麟被领进一间铺着厚地毯的屋子,墙上挂着几幅字画。他记得很清楚,刚落座,父亲就从厨房端出一碗青菜汤。 饭桌上没人说笑,气氛沉得让人坐不住。小孩哪懂这么多规矩,看到桌上一盘红烧肉眼睛一亮,筷子刚伸出去,就被父亲按住了手。 “饭不是这么吃的。”郭德纲低声说完,挟了一筷子菜塞到他碗里。那天之后,吃饭这件事变成了规矩最多的一件事。饭桌上动筷要等人齐,吃不完不许走,最爱吃的东西只能吃一点点。后来这几条被家里称为“饭桌三令”。 他在北京住的第一间屋子,是德云社旧楼后面的一间小屋,冬天靠电热毯取暖。早上六点要起床练声,晚上十点还得在灯下背台词。那时他还没进学校,每天就跟着大人们混在后台跑场子,午饭是盒饭,午休是搭在后台的折叠床。 有次后台太吵,他钻到道具箱里睡着了,结果晚上被错当成道具直接推上了舞台。观众还以为这是德云社的新包袱,全场爆笑。他趴在地上哭,那是他第一次在演出中哭,不是为了角色,是委屈。 于谦第一次见他,是在一次小剧场彩排后。他一个人坐在走廊里,鞋子掉了一只,裤脚湿了一半。于谦把他带到旁边小卖部,买了双拖鞋和一瓶热饮。那天两人坐在胡同口聊天,于谦问他,“你知道你来这干嘛的吗?”他点点头说:“我爸说,我以后得像他说书那样说话。” 在外人看来,于谦像是个不太严的叔叔。但郭麒麟知道,他跟父亲不一样。父亲骂他不带脏字,语气冷冷的;于谦骂他,是边说边比划,讲完还会拍拍他的头。 大概是从2007年开始,郭麒麟开始正式站台说活儿,前排经常有人议论:“这是谁家孩子,怎么这么小?”起初台下很静,大家好奇这个“娃娃相声演员”能说成啥样。后来,他开场第一句话还没说完,就有人起哄:“少班主来啦!” 这些话他都听得见,但也只能装听不见。父亲从来不夸他,一次演出下来,只会点评句尾处理、节奏卡点、观众反应。于谦不同,他在后台总会递瓶水,说几句:“刚才那段不错。” 13岁那年正式拜于谦为师。仪式很简单,在德云社旧址的排练室,几张椅子围成一个圈,一杯茶、一个鞠躬。那年他刚升初三,暑假几乎没休过,整天排练、演出、改稿子。 2010年德云社出事,父亲四面楚歌,很多人劝他“把儿子拉回来读书”。郭麒麟已经半年没去学校了,课本上落了厚灰。他没等父亲开口,自己提出退学。 外界很快炸了锅,“初中没毕业就要接班”的说法传得沸沸扬扬,连他小时候的老邻居都发消息问:“麒麟怎么不上学了?”郭德纲一开始没表态,只是把他拉进书房,把那本《中庸》扔到他面前说:“这本你读完,我就同意你不上学。” 他读了三天,把重点都划了出来,用夹子装好塞进书桌抽屉。从那天开始,他每天写段子、背词、排演,还要跟父亲学习架构、音准、语气和走台。晚上回家还要看书,他翻过的书从《围炉夜话》到《蒋勋讲美学》,有些书他其实也没看懂,但都读完了。 2011年他的第一场个人专场在天津开演,台下坐了一半记者。观众席上有人喊“太嫩了”,也有人喊“像郭老师”。那场结束后,他没去聚餐,独自回房把当天的录音听了三遍。 之后几年,他跟阎鹤祥搭档,跑了全国十几个城市,演了上百场。有次在青岛,演出前夜他发烧到39度,上场前吃了两粒退烧药。第二天观众在论坛上留言说:“小郭那晚的节奏特别稳。” 他没回应,只是把那场录像留到了现在。 这几年他开始演影视剧,拍综艺,很多观众开始叫他“演员郭麒麟”。他没反驳,也没承认。他说自己“只是换了个平台讲段子”。 一次节目中,录制现场突然响起父亲的声音,他顿了一下,把手里的麦轻轻放下,然后走进房间,轻声喊了一句:“您来了。” 现场没有剧本,那句“您”是他自己加的。 有人说他是靠父亲成功的,也有人说他情商高会做人。他自己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小时候蹲在楼梯上吃剩菜的时候,没想过这些。” 北京 德云社 人物故事 他现在偶尔还会发些看书的照片,有时候是随手一页,有时候是一段标注。很少有人注意到,他每张图上都会圈出一个字,或许是巧合,也可能是习惯。 你觉得他会不会哪天,写一整本自己的书?






![兄弟们,我回本了[哭哭][哭哭][哭哭]卖不卖,大过山车扛过来了[笑着哭][笑c](http://image.uczzd.cn/15488165185729678017.jpg?id=0)


![岚图泰山官图来了,长相非常……尊。这门把手,尊界S800看了表示专业[doge]](http://image.uczzd.cn/6797880503656448874.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