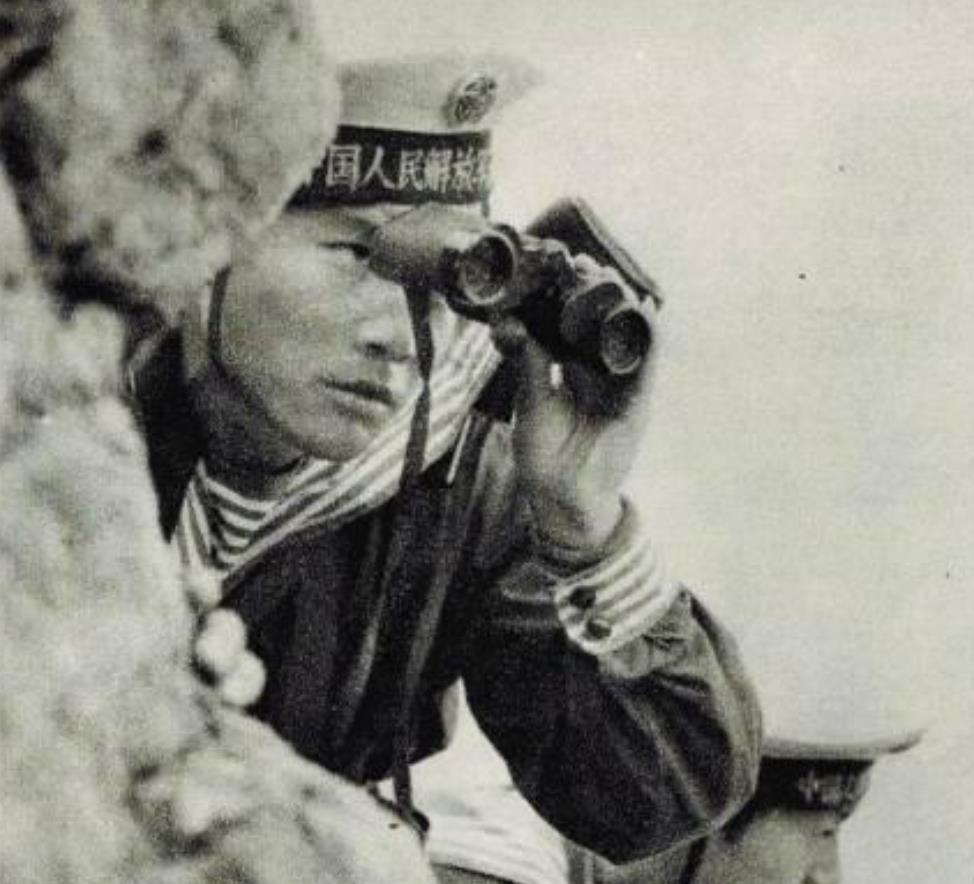1958年,志愿军战士爱上了一个朝鲜姑娘,他放弃回国,甚至放弃了国籍,坚持与朝鲜姑娘结婚。到了晚年,他携带7个孩子回国定居! 1953年,仗打完了。大部队分批撤回国内,22岁的王兴复却被留了下来,在平安南道江东郡的石岭村,帮着当地搞战后重建。 那时候的石岭村,说是个村子,其实就是一片废墟。房子没顶,墙上全是枪眼儿。他刚到那儿,话也听不懂,每天就跟着比划干活。可就在这片废墟里,他认识了吴玉实。 那姑娘才17岁,瘦得像根高粱秆,但干活比男人还猛。家里没男人了。她爹早逝,两个哥哥都在战场上牺牲了,全家就靠她和她妈撑着。王兴复瞅着心疼,这姑娘命太苦了。 王兴复开始默默地帮她。今天送双自己舍不得穿的旧胶鞋,明天帮她家把漏雨的房顶给修了。周末休息,他就往吴玉实家跑,带点部队的剩饭,顺手把水缸挑满,把柴火劈好。 这感情,就像地里的种子,你不经意间,它就发了芽。村里人、部队战友,谁都看在眼里,但谁也不敢捅破。为啥?天大的纪律在那儿摆着呢:志愿军严禁与朝鲜妇女通婚,违者军法处置。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好日子没过几年,1958年,中央一纸令下,所有志愿军必须全部撤离。 这命令对别人是喜讯,对王兴复简直是晴天霹雳。回国,就得跟吴玉实永别;留下,就得放弃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他抽了几天几夜的烟,最后把一份“就地复员”的申请书交了上去。 这一下,整个兵站都炸了锅。领导轮番找他谈话:“小王,你脑子糊涂啦?你回国前途一片光明,为了个姑娘,值吗?”他一言不发,就把头埋着。 吴玉实的母亲,一个朴实的朝鲜妇人,也急了。她托人给当地政府写了封信,信上就一句话,却比什么都有分量:“我女儿心里,只有一个中国人。” 这事儿层层上报,一直报到中朝指挥部。谁都觉得这事儿办不成。可谁也没想到,这个几乎不可能的申请,最后竟然批了。特批他“就地复员”,脱离中国国籍,转为朝鲜居民。 那一刻,王兴复不再是志愿军战士,他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朝鲜老百姓。 1959年,俩人结婚了。婚礼简单到不能再简单,没照片,没仪式,就是一桌饭,几瓶酒,还有几个偷偷跑来送行的老战友。这杯酒,喝下去的是喜悦,也是和过去的诀别。 婚后,王兴复先是在一所华侨小学当校长,后来学校关了,他又去牧场养牛。日子苦,但他从没抱怨过一句。他和吴玉实一共生了七个孩子,三个儿子,四个女儿。 每多一个孩子,他就多一份牵挂,也多一份对家的渴望。 他坚持给每个孩子都起中文名,还一次次跑去给孩子们申请中国国籍。他说:“我生是中国人,我的娃,根也得在中国。” 身在异乡,心在故土。他的母亲还在辽宁海城老家,七十多岁了,天天盼着儿子回家。从1970年开始,王兴复写了第一封回国申请,信里就一句话:“母亲年老,盼归。” 回信冰冷无情:手续不全,身份不明。 他现在的身份是“朝鲜人”,那个叫王兴复的中国军人,档案上已经“消失”了。从那以后,他年年写,年年申请,次次都被驳回。 吴玉实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知道丈夫心里那块最大的石头是什么。她开始更努力地学中文,她说:“等你回家了,我得能听懂家里人说话。” 这份等待,一等就是二十多年。人生有几个二十年?青丝熬成了白发,故乡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直到1981年,转机终于来了。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很多政策都松动了,开始重新审查处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 王兴复递交了第11次申请。这一次,信封里装着的,是他二十多年的期盼。几个月后,批准的消息传来,他一个快五十岁的汉子,当着全家人的面,哭得像个孩子。 那一年,他带着吴玉实和七个孩子,一家九口,登上了开往中国的火车。当列车跨过鸭绿江,进入丹东地界时,王兴复“扑通”一声,在车厢里跪下了,冲着窗外的土地,磕了三个响头,嘴里反复念叨着:“我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 这一跪,是还给了这片土地二十多年的思念。 海城市政府对这位特殊的老兵非常照顾,给他们全家安排了住房,还给了1000块安家费,王兴复也被安排进了海城变压器厂工作。他干活比谁都卖力,天不亮就到厂里,他说:“能在祖国的土地上干活,心里踏实。” 吴玉实和孩子们也慢慢适应了中国的生活。当地的朝鲜族同胞对她特别好,教她说东北话,教她包饺子。几年下来,她已经是个地道的东北媳妇了。记者采访她,她笑着说:“中国是我第二个故乡,我丈夫在哪,我的家就在哪。” 晚年的王兴复话不多,但他每年清明,雷打不动地要去烈士陵园,在志愿军纪念碑前,一站就是大半天。他从没跟国家提过任何要求,也没找组织要过什么待遇。他说:“国家能让我回来,我就心满意足了。” 他活到了九十岁。走的时候,身上穿的,还是那套早已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他的墓碑上,没有长篇的生平,只有简简单单八个字:“志愿军老兵,魂归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