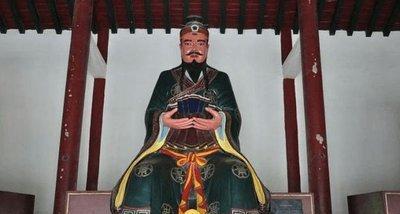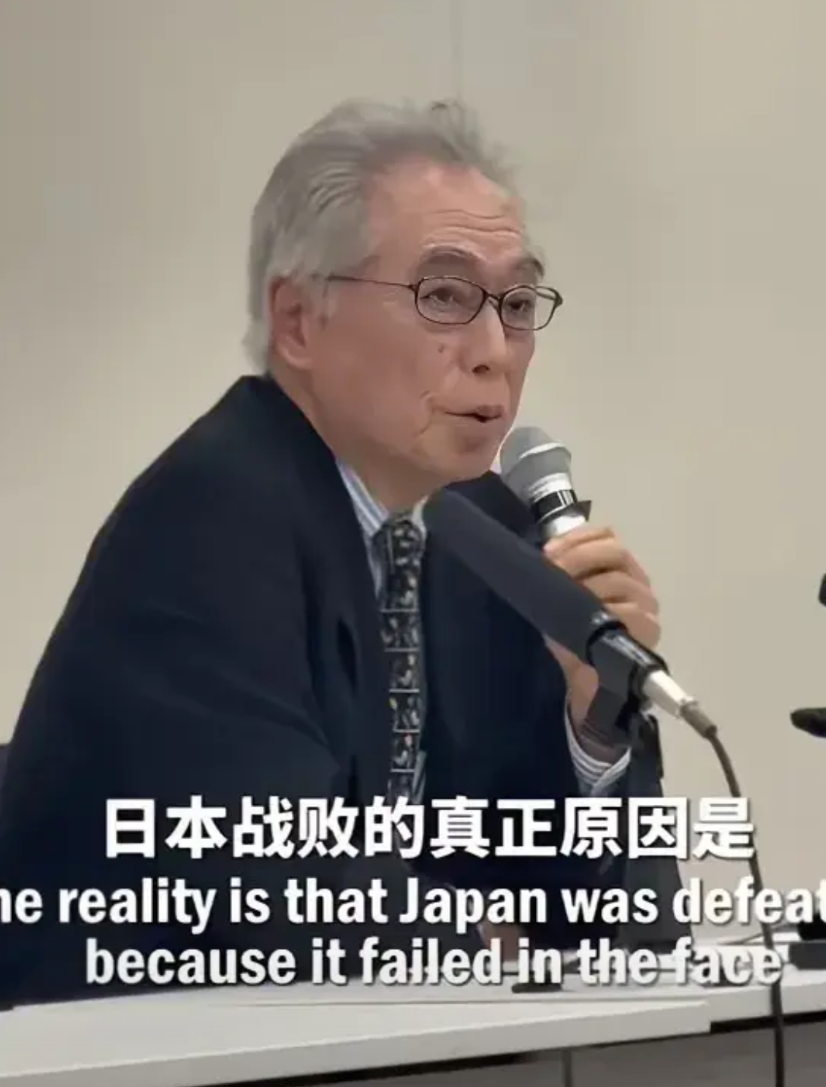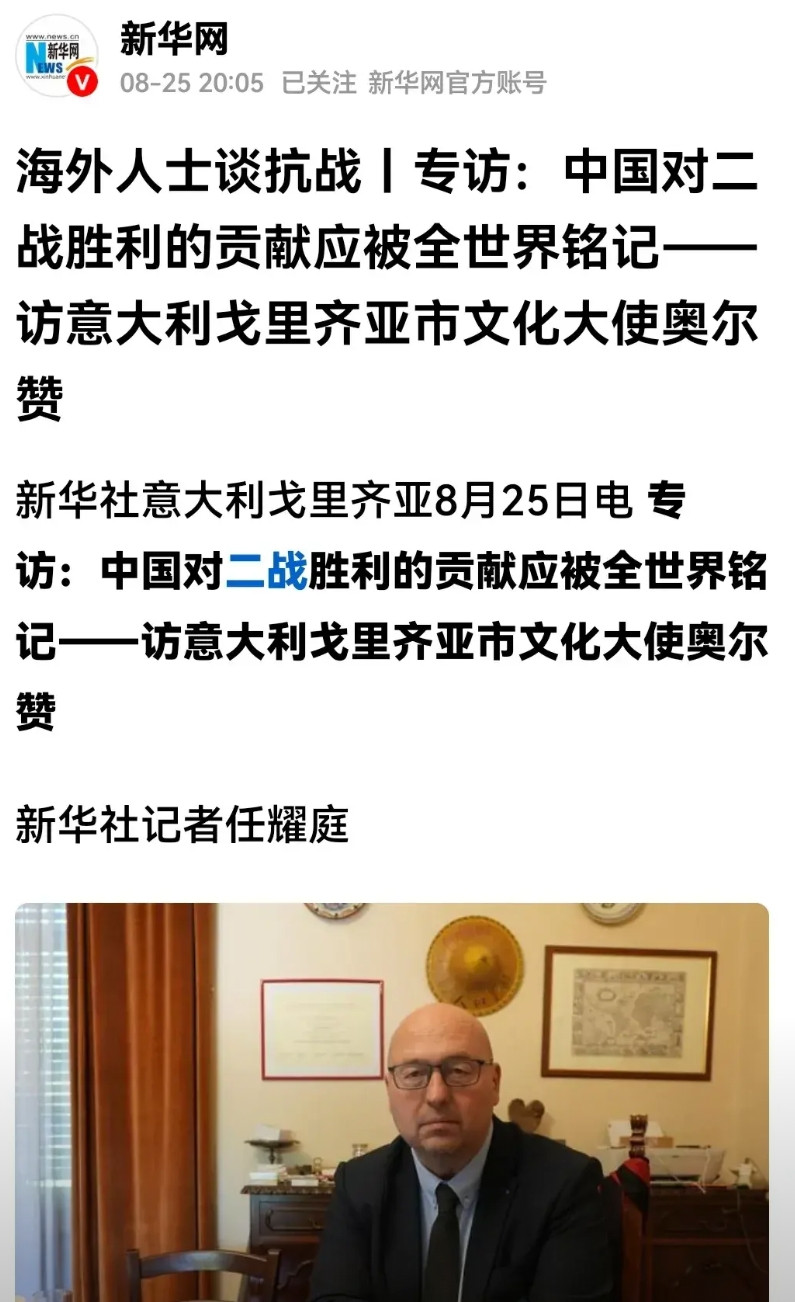法国没想到,德国也没想到,就连美国都没想到,在中国的端午节被韩国捷足先登后,韩国如今又宣布将黄豆酱和酱油申遗。 继端午节被韩国抢先申遗后,2024年12月,韩国又把黄豆酱、酱油和辣椒酱的制作工艺打包成“腌制酱料文化”,塞进了联合国非遗名录! 韩国的逻辑很简单:只要现在还有人在用,就能申遗。至于发明是谁的,早就不在他们考虑范围内。用得久、叫得响、改一改口味,就能变原创。 黄豆酱和酱油,亚洲各国都有,谁家不吃?中国最早在《周礼》里就记载了“醢”“豉”这些发酵豆制品,汉代之后更是家常调料。古人连制法都写得明明白白。黄豆原产于中国,发酵制酱的工艺几千年历史。 韩国哪来的自信说那是祖先留下的?祖先从哪来的他们心里没数吗?这不就是你家锅里煮的菜,别人吃一口转头告诉全世界“我发明的”。最魔幻的是他们说得理直气壮。韩国民众一边吃着本地改良过的酱油,一边在网上激情留言:“我们是世界发酵之国”“大酱汤的味道全球独一份”“中国只会模仿我们”。 韩国敢申,是因为他们从上到下有一套完整的文化运作系统。政府有计划,媒体来宣传,学术机构跟着论证,老百姓也配合表演。所有人拧成一股绳,文化输出像打仗一样干。他们从1962年起就把文化遗产立法,设专门机构统筹申遗,每年评估、遴选,地方项目由中央统一管理,专人撰写英文材料,翻译、审查、制作申遗片,一环不落。 反观中国这边,明明拥有最完整的发酵饮食历史,结果没人申、没人提、没人关心。哪怕有文化人想做,也经常被各种审批卡着。村里奶奶的手艺,传不到城里来;书上的配方,没人真去做。中国人更关注产品好不好吃,价格实不实惠。没人关心你这东西是不是“非遗”。就算知道是,也没人管韩国那边申遗申得飞起。 消息传回中国,中文互联网上瞬间炸开了锅。中国网友纷纷表示:“我们有马王堆酱坛子!两千年前的!”确实,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酱器,标注清楚“豆豉酱”,更早的《齐民要术》也记下酱油雏形“豆酱清”。但问题来了:这些考古证据有没有变成可申遗的文化项目?有没有组织体系进行文化转译?有没有地方文化部门牵头提报?几乎没有。 日本网友也坐不住了,他们在网上留言:“韩国的黄豆酱和我们的味噌很像,难道他们也要申遗?”东南亚国家的网友则表示:“亚洲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酱料文化,韩国这是要把整个亚洲的文化都据为己有吗?” 韩国这次申遗成功,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警示。中国并非没回应,2009年端午节成功列入非遗,是中国第一个入选的“节日类”项目。截至2024年底,中国已有42项人类非遗入选,数量高居世界前列。而韩国,仅23项。数字上我们赢了,节奏上却始终被动。 像“火炕”“剪纸”“酱油酿造”,这些有极深文化根脉的项目,要么迟迟未启动,要么申报时间一拖再拖。问题不在“有没有”,而在“敢不敢快推”。20世纪上半叶,国家动荡、文化破坏,很多民俗技艺本身已出现断代。再加上上世纪末的“经济优先”逻辑,文化投资排在末位。 改革开放后,物质飞速增长,但传统文化传承几乎是靠民间守艺人“自己养自己”。而韩国,从中学就设有“民族文化体验课程”,寒暑假组织孩子做绳结、做泡菜、做竹器,不为就业,只为传承。 韩国这次申遗成功,对国际社会来说也是一个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只看三点:是否仍在日常生活中传承、是否有完整的文化表达、是否有持续的社区参与。韩国靠着大企业和地方政府联手包装,把黄豆酱拉进文化展馆,还专门请法国纪录片导演拍宣传片,一套组合拳下来,把“酱文化”打成全球IP。而中国还在争吵“这根本是偷的”。 中国的文化输在这上面。不缺东西,缺讲法。东西越古老,我们越懒得讲。越普遍的,越没人申遗。结果便宜了邻居,让他们拎走了标签,还能顺带踩我们两脚。 中国需要加快文化保护的步伐,把自己的文化讲明白,讲响亮,不是因为“怕被抢”,而是因为我们自己也值得被世界记住。毕竟,文化不是专利,也不是国界线。但一个国家如果不去争、不去讲、不去保护,就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