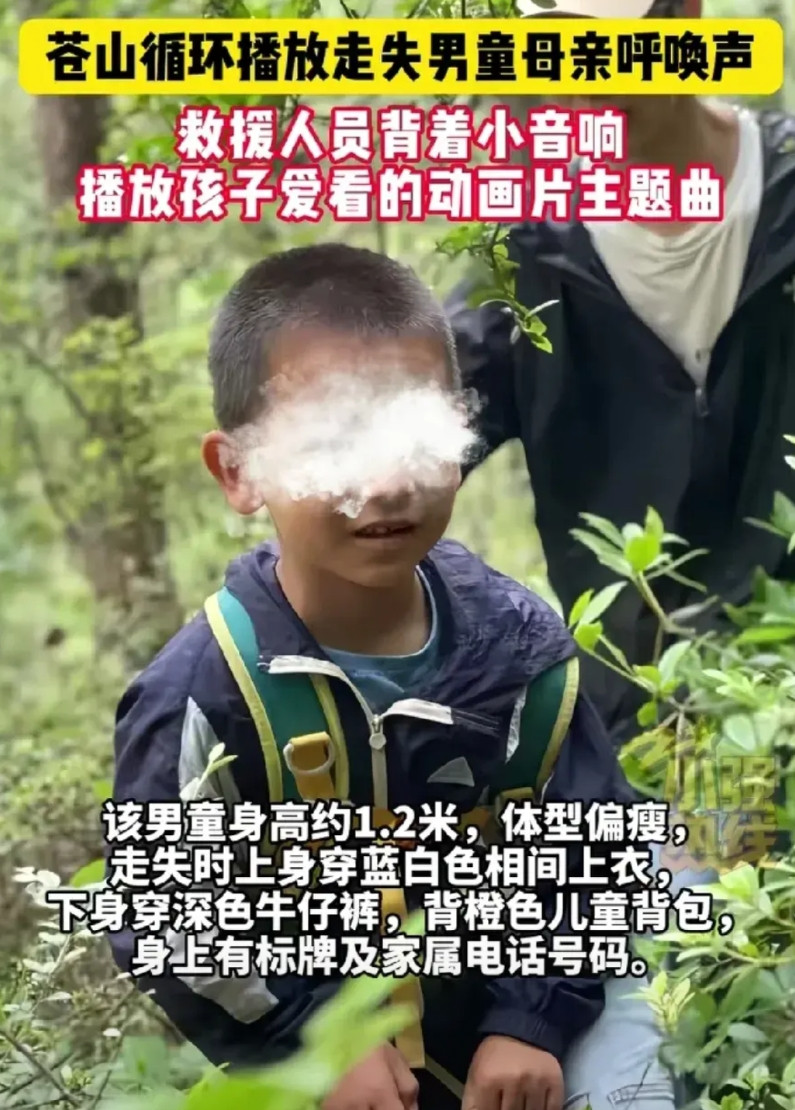1888年,山东一乞丐讨饭28年,攒下230亩良田、3800吊钱,盖了一豪华宅子,没想到,49岁的他穿着破烂衣服,挨家挨户磕头:求求你跟我走吧,我帮你干活,可村民却将他赶出门:哪有这好事! 在很多人眼里,一个四十多年都靠讨饭为生的老头,突然拿出几千吊钱盖起宅子和书堂,这事本身就让人不安。 当武训穿着补丁衣裳跪在村民家门口,求他们把孩子送来上学,换来的不是感激,是骂声,他说可以免费教书,还能帮干农活,村民觉得这人疯了。 白吃白住还帮忙干活,哪有这样的买卖?这事搁谁身上都得怀疑,这不是人心冷漠,是他们根本想不到,一个“乞丐”真能咬牙苦熬几十年,为的是让别人家的孩子识字,这种信任的缺失比铜钱还难挣。 可武训并没走,他继续一个个敲门,一户户跪,一条街一条街跪过去,没人相信他真的不图名、不图利,他早就习惯了这种羞辱,毕竟行乞三十多年,脸皮早磨平了。 可这次的跪,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为了一群穷苦孩子能有资格坐进教室,他跪出的不是学费,而是一种教育的入场券,哪怕只招到一个,他也认了。 这事后来闹大了,有的人说他演戏,有人说他图名,可就是这些骂他“戏精”的人,几年后眼睁睁看着从义塾里走出一批批孩子,有的成了秀才,有的成了举人。 这时候,村里人才知道,他们错得有多离谱,可错过了最初的信任,很多孩子也错过了能读书的年纪,可武训没怨谁,他从来就没求别人懂,只求有人愿意来听书。 谁都说他疯,可清廷却给他盖了坊、赐了“义学学正”的官衔,他自己却从不把这些当回事,门上没挂过名,讲堂他都不进,就怕脏了读书人的地。 这个被赶出门的“丐帮老头”,偏偏活成了那个年代最有资格说“教育”二字的人。 要不是有人算了一笔账,没人知道这老头到底攒了多大一笔钱,有人说,武训要是愿意,他完全可以在当地买下五百亩水浇地,娶上媳妇,当个吃喝不愁的小地主。 可他偏不,他卖艺、化缘、下地干活,甚至用石板压胸、铁锤砸背,都不为自己,只为在账本上多添一吊钱。 他把这些钱交给当地一位武举人保管,自己却住在破庙里,吃发霉的剩馍,睡凉席、穿旧布鞋,他早就不是在过日子,是在熬命。 他知道自己这辈子享不了什么清福,可如果能让几个穷孩子学会写字认账,不被人随便骗工钱打出门,那他吃多少苦都不叫事。 民国年间,为他修祠堂、建雕像,蒋介石、张学良、陶行知纷纷题字,可他若还活着,大概只会摇摇头,他不懂这些名人是谁,也不稀罕。 他想听的,从头到尾就只有一句话:读书声,天不亮,他就站在义塾墙外,听那一声声“天地玄黄”,那才是他真正的奖赏。 故事要从头讲,得从那个还没“疯”的小武七说起,那年他十四岁,去张财主家做长工,一年到头没白没黑地干,结果工钱被一本假账本一笔勾销。 他去理论,换来一顿暴打,嘴里全是血,那天傍晚,他蹲在村外的破庙,整整想了一夜,他不懂得算账,更不会分辨真假,这顿打,是穷人不识字的代价,他明白了,想不被踩在脚下,得先认得字。 不过知道自己这辈子是读不成书的,可别的孩子呢?要是他能给他们一个读书的机会,是不是就能少挨几顿打,少走几步冤路? 从那一夜开始,他就不再为自己活,他靠着一口气,讨饭、卖艺、做杂活,连命都能扔出去,就为建学堂。 他一生没成家,可他有后人,不是血脉,是精神,他的侄孙武芳林、曾孙武金兴、玄孙武玉泉,几代人都在坚守着他的这间义学。 可不是谁都懂这条路多难,祠堂被毁,碑被砸,连武训的遗骨都找不回来,可他留下的那股劲没散。 几十年后,墓修好了,祠堂立起来了,一座座石碑,一幅幅字,重新立在他曾跪过的土地上,来祭拜的人多了,不光是后人,还有学生、教师、远方慕名而来的旅人。 很多人说,一个讨饭的能办出什么像样的学堂?可当年的“崇贤义塾”立起来那一刻,谁都惊住了,青砖黛瓦,雕梁画栋,一看就知道是下了血本。 武训请来了本地最有威望的秀才赵老先生,还自掏腰包给高薪,他自己呢?不进讲堂,不署名字,不坐上席,他说他是乞丐,配不上这些清净地儿,他怕自己身上的穷气,污了读书人的台阶。 三所义学都不挂他名,土地和房产也一律登记在学堂名下,有人劝他多留点,他摇头说,钱是给娃娃们读书的,不是给他养老的。 他死后,连块墓地都没占便宜,只是躺在义学旁边的田里,一块小碑刻着“武训”二字,却站成了千秋的背影。 很多年过去了,他的故事没凉,民国时就有漫画连载,叫《武训画传》,后来还拍了电影《武训传》,虽然因为政治风波被禁播多年,但那股子精神,怎么也封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