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5年,清军和准噶尔部族的拉锯战已经打了好几年。乾隆两次派大军攻打,终于拿下了准噶尔的首领达瓦齐,把伊犁等地拿在手里,以为胜利在望了。但乾隆和清廷都高兴得太早了。
准噶尔内部并不服气,那些手握实权的部落首领们,像辉特部的阿睦尔撒纳等人,根本不想真心归顺清朝。清军主力刚撤走没多久,这些手握重兵的部落首领就翻脸了。他们联合起来,突然发动叛变!
这次叛变极其凶狠。清军留在当地的最高将领定边左副将军策棱(超勇亲王),措手不及,不幸战死了。
另一位负责帮办军务、很有能力的参赞大臣兆惠,这时正在伊犁处理战后事务,一下子被四面八方涌来的叛军团团围困在城里,和外界完全断了联系,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刚被平定的准噶尔几乎全境反叛,清军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打了胜仗,形势却在一夜之间退回到原点,甚至更糟。
这场仗,看起来要白打了。
坏消息像雪片一样传到紫禁城。乾隆坐在龙椅上,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更让他头疼的是,朝廷里抱怨和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大臣们觉得,这仗打得太久,死了太多人,花了太多钱,结果还没占到便宜,现在又打成这样,再打下去恐怕是个无底洞,建议赶紧收手算了。当时国库也因为连年打仗开始紧张,支持继续打下去的力量在减弱,局势对乾隆非常不利。
乾隆内心是愤怒和不甘的。他想再次调集大军,狠狠教训那些反复无常的叛军。但环顾四周,乾隆发现手头没大将可用了!
前两任主持这场战事的最高将领(北路定北将军班第和北路定边左副将军策棱)都战死了,剩下最能干的大臣傅恒,是乾隆非常倚重的左膀右臂,需要留在北京帮他坐镇朝堂,稳定局面,根本走不开。整个清廷似乎陷入了无人可派、进退两难的僵局。
就在这个异常低沉、希望渺茫的关键时刻——大约在公元1756年的冬天,一道惊人的消息如同闪电划破了阴云,从遥远的西北边陲传到了京城:兆惠还活着!不仅活着,他还带着人从伊犁杀回来了!
消息首先传到了甘肃巴里坤大营(清军在西域的重要据点)。所有人都震惊了,包括驻守在那里的清军官兵。原来,兆惠被围困伊犁后,形势险恶,但他没有坐以待毙。
眼看孤立无援,守下去必死无疑,他当机立断,选择拼死突围。他手里能用的兵,不是精锐铁骑,大部分是两千名负责建城挖渠的工程兵(当时称作“匠役兵”),还有少量卫兵,普遍疲惫带伤,装备也很差。就是这样一群老弱病残的杂牌军,在兆惠的带领下,硬是在十几万叛军的重重包围圈里,杀开了一条血路!
他们且战且走,忍受着严寒、饥饿和不断的追击,跋涉数千里,经过大小几十场战斗,一次次击溃堵截的敌人。这支队伍像一把烧红了的钝刀,硬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和伤亡,一路往东闯,目标明确——巴里坤大营!
当这支衣衫褴褛、血迹斑斑,却气势依然彪悍的队伍,在兆惠带领下奇迹般地冲入巴里坤大营时,整个大营都轰动了!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几个月音讯全无,都以为兆惠和伊犁守军早已全军覆没,尸骨无存。没想到,这位悍将居然带着残部从地狱爬了回来!他带回来的不仅是人,更是一股烧灼着复仇烈焰的冲天杀气!
兆惠本人,更是被这场惨烈的千里突围彻底激发了血性。他在巴里坤一边收拢残兵,一边咬着牙,用最直接、最狠绝的言辞给乾隆写了一封奏章。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想法:要求皇帝允许他带兵打回去,并且必须用最严厉的手段,对那些屡次叛乱的厄鲁特(准噶尔蒙古)各部进行彻底的清剿,“除恶务尽”,不能再留情面!
兆惠生还并成功突围的消息传到京城,立刻在沉闷的朝廷里炸开了锅。乾隆更是精神大振!兆惠的幸存本身就是个奇迹,他带领残兵拼死杀回的壮举,如同一剂强心针,让朝野上下的主战派瞬间有了底气。看着兆惠那份充满决绝杀气的奏章,乾隆所有的犹豫一扫而空。再也没有拖延和抱怨的理由了。
乾隆立刻下旨:任命这位从尸山血海中杀回来的猛将兆惠为“定边将军”(实际上的第三任最高统帅),统率包括新集结的八旗劲旅在内的大军,再次向西进发,目标直指混乱的准噶尔!这一次,清军不再轻敌,乾隆也给予了兆惠绝对的信任和最大的支持。
有了兆惠的“复活”和复仇意志的注入,清军的士气被点燃。最终,在兆惠等人的坚决打击下,清军取得了彻底胜利,平定了准噶尔地区的叛乱,将其纳入清朝版图。
兆惠那场在绝境中爆发、不可思议的成功突围,以及他本人强烈的复仇意志,成为了整个战争走向最终彻底胜利的最为关键、也是最为惊心动魄的转折点。清军不再被动,而是彻底掌握了主动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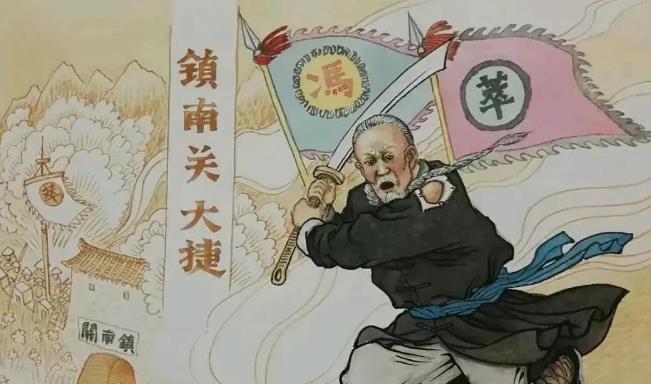








牧野天下
都是天地会蛊惑的,准噶尔沙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