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上将进京开会,特意去看望老首长徐帅。硬着头皮,吃完了一碗合子饭,肚子里是直翻酸水。回到福州后,韩司令还对夫人讲:“徐帅家的饭,实在太难吃了,我捏着鼻子往里灌。” 那碗让韩先楚 “遭罪” 的合子饭,端上桌时冒着热气。 荞麦面的碗沿还沾着点面疙瘩,里面卧着煮得面乎乎的土豆块,飘着几缕槐花的白,看着清清淡淡,入口却满是粗糙的颗粒感。 韩先楚夹起一筷子,山西粗粮特有的涩味混着槐花的微苦,在舌尖上打了个转。 他自小在湖北吃惯了糯米的软、稻米的香,连面条都得是带汤汁的碱水面,这口寡淡的合子饭,着实像在嚼带糠的麸皮。 可徐帅吃得香。他端着碗,筷子夹得稳,每一口都嚼得仔细,偶尔夹起块土豆,还会笑着说:“这土豆是后院种的,比菜市场买的面。” 韩先楚顺着老首长的话点头,眼角瞥见桌角的咸菜碟,一碟腌萝卜,一碟酱黄豆,都是最普通的家常味,连点油星子都少见。 徐帅的警卫员站在一旁,见韩先楚碗里的饭没动多少,想添点别的,被徐帅摆手拦下:“就吃这个,挺好。” 韩先楚后来才知道,这不是徐帅特意 “招待” 他。徐帅的儿媳王彦彦小时候常去家里写作业,见过最多的 “菜” 是马笕齿 。 那种田埂边随处可见的野菜,开水焯过,撒点盐就能端上桌。 有回她留到饭点,徐帅给她盛了一碗,说:“尝尝,败火。” 她嚼着带点草味的野菜,看着徐帅和家人围坐一桌,吃的都是一样的棒子面饼、小米粥,才明白 “徐伯伯家的饭,从来就没分过‘大人的’和‘孩子的’”。 那天饭桌上,徐帅没聊别的,净问福州军区的训练:“海边风大,战士们的棉衣够不够?” “新兵练射击,有没有实弹打?” 韩先楚边答边往嘴里扒饭,粗粝的荞麦面刮得嗓子眼发紧。 可看着老首长碗里的饭和自己的一模一样,连最后一口汤都喝得干干净净,他硬是没敢剩下一粒米。 放下碗时,手心都攥出了汗,胃里却像揣了个秤砣,沉甸甸地坠着。 回福州的火车上,韩先楚还在琢磨那碗饭。他想起战争年代,徐帅在前线指挥,嚼的是冻成硬块的窝头,就着雪水往下咽。 解放后住进北京的院子,院里种着茄子、辣椒,连吃的菜都要自己动手种。 有回他去见徐帅,见老首长穿着件打了补丁的旧衬衣,袖口磨得发亮,警卫员说:“元帅总说,补补还能穿,扔了可惜。” 韩先楚跟夫人讲起这些,语气里没了抱怨:“不是饭难吃,是咱没吃过那份苦。 你想啊,徐帅一辈子指挥千军万马,可家里的饭桌,比咱战士的食堂还简单。他不是吃不起好的,是觉得没必要。” 夫人听着,想起韩先楚自己也总把 “不许搞特殊” 挂在嘴边,部队食堂吃什么,他就吃什么。 顿顿少不了辣椒,那是湖北人改不了的口味,可碰上粗粮,也从没皱过眉。 后来部队开作风整顿会,韩先楚特意讲了这事儿:“徐帅家的合子饭,我吃不惯,但我佩服。 那碗饭里没山珍海味,却有老革命家的本分 —— 不搞特殊,不图享受,心里装着的,永远是战士,是老百姓。” 他让炊事班学着做粗粮,自己带头吃,有年轻干部吃不惯,他就说: “韩先楚当年捏着鼻子能灌下去,你们就不能尝尝?尝尝,才知道今天的日子咋来的。” 徐帅家的饭桌,就这么成了部队里的 “教材”。有人说那是 “苦行”,韩先楚却摇头:“那是本色。 一个能跟战士同吃野菜的元帅,一个家里顿顿粗粮的首长,他的命令,战士们才信;他的作风,才撑得起军队的骨头。” 许多年后,韩先楚再跟孩子们讲起徐帅,还会提那碗合子饭:“难不难吃?难。 但那口饭,比任何训话都管用 —— 它告诉你,当官的不把自己当特殊人,队伍才能硬;过日子不忘本,家业才能稳。” 话里的意思,孩子们当时似懂非懂,直到后来走进军营,看到食堂里 “光盘行动” 的标语,看到老兵们捧着粗粮饭吃得香甜,才忽然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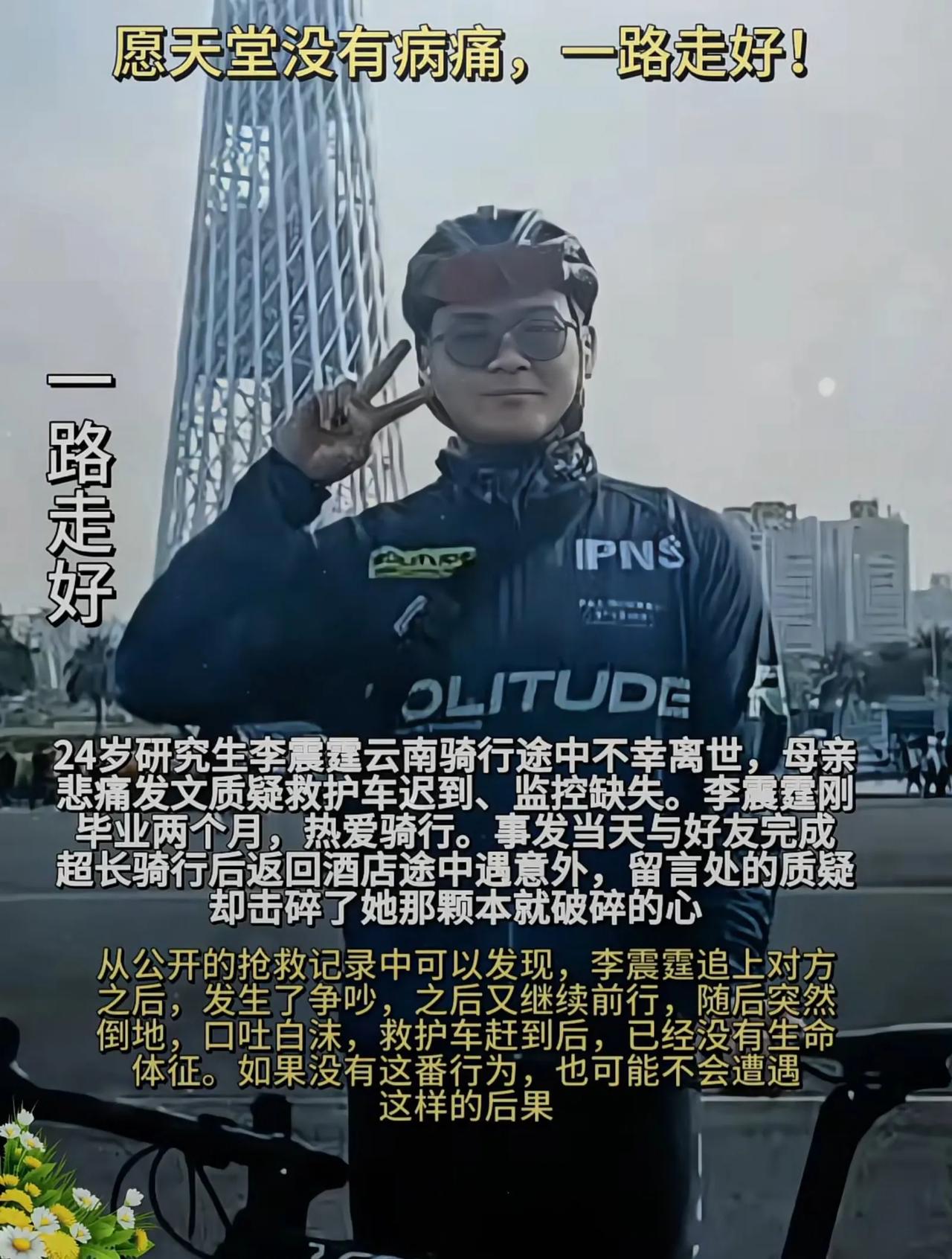





23s
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