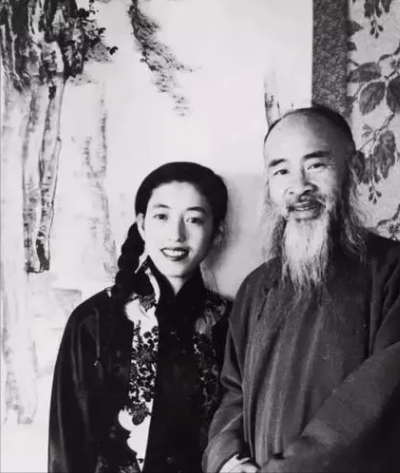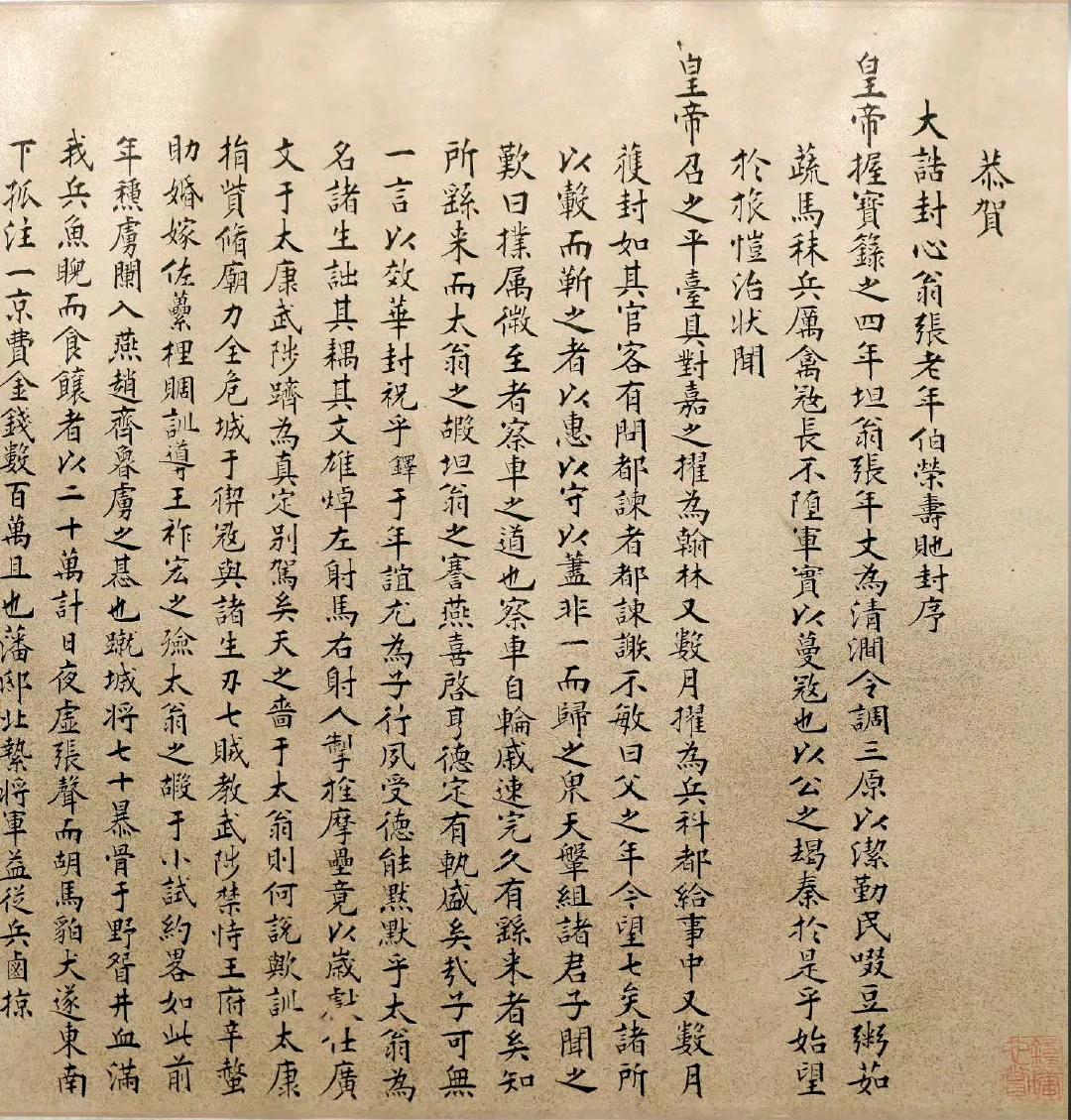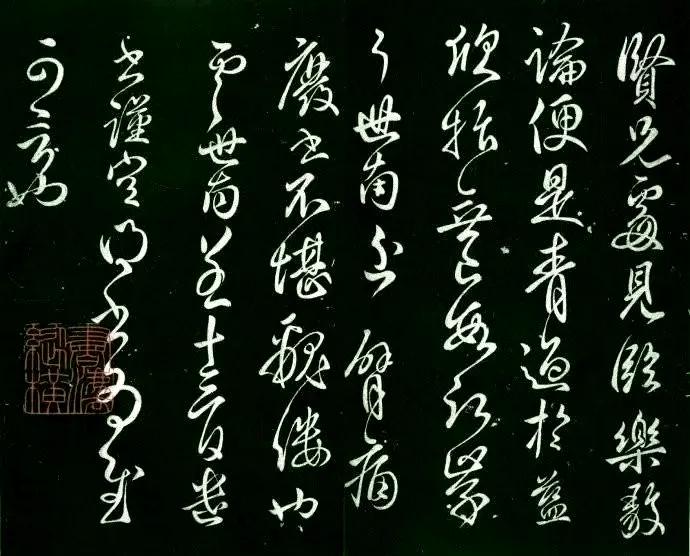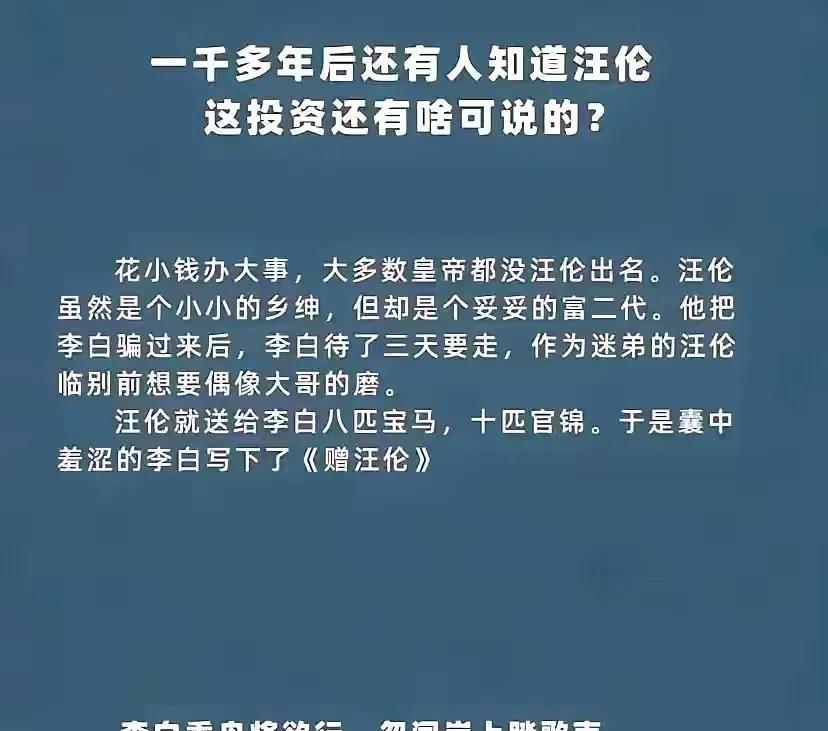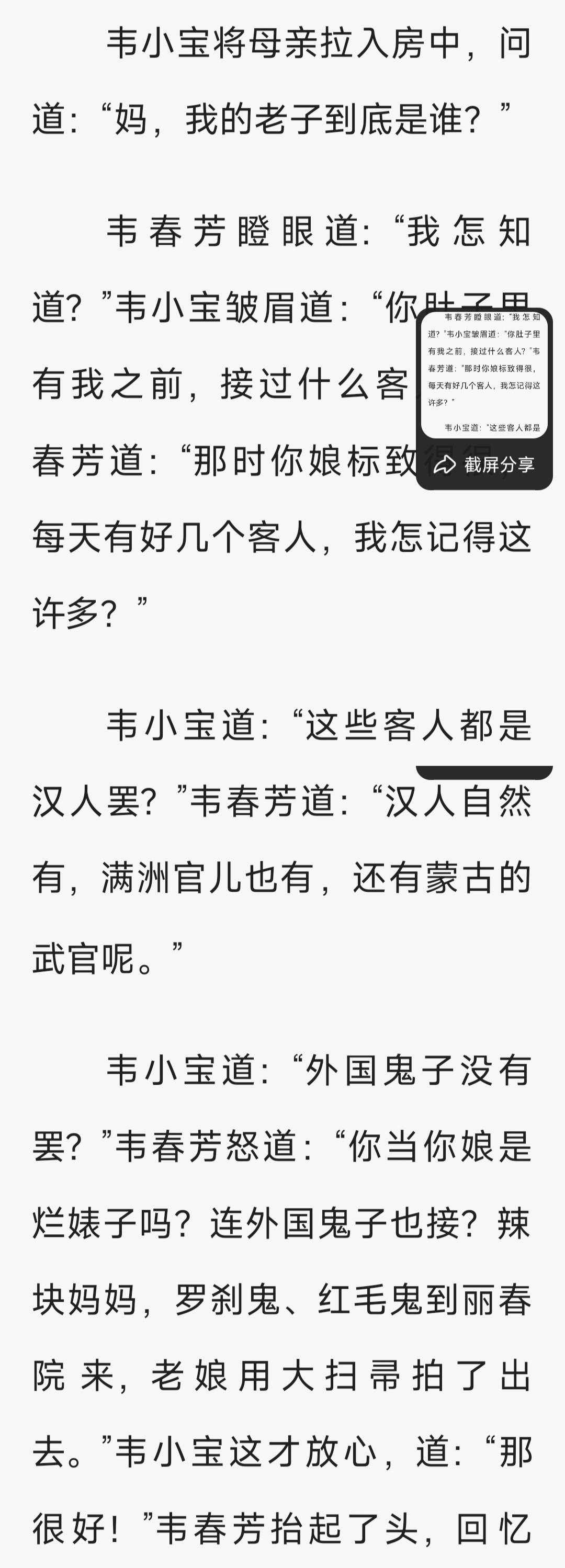1899年,张之洞审问光绪:“听说你要见我,有事就说。”光绪走向前回道:“朕私下和你说。”张之洞斥道:“不说就办你砍头之罪!”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1899年,武昌城北的金水闸口,一群百姓突然围住了一顶外来马车,车上跳下的青年身穿明黄色常服,脚踏白靴,头戴小冠,背后紧随一名尖嗓太监模样的中年人。 他步伐稳重,目光直视远方,有人盯着他的脸,突然喊了一句:“是皇上!”人群瞬间骚动,青年叫崇福,出身旗人,原本是京中一个戏班的伶人。 他个头不高,肤色白净,眉眼之间轮廓清晰,长得极像宫中画像上的光绪,早年因模样出众,被太监赵德兴看中,两人私下勾结,设想出逃宫后的“翻身之法”。 赵德兴早年在宫内做事,对皇宫礼仪、物件、制式烂熟于心,在慈禧禁锢光绪、维新失败的舆论混乱中,他们抓住了这一历史缝隙,决意假扮皇帝南下自立为尊。 赵德兴提前离京,藏匿了几件“御用”之物,一条金龙织纹的缎被、一方刻着“御用之宝”的玉印,还有几件带有内务府标记的漆器。 他与崇福会合后,在途中多次伪装试演,逐步在南方铺设身份,他们抵达武昌后住进城北一处偏远宅院,自称“行在”,门口悬挂黄幡。 赵德兴每日早晚跪拜伺候,街头巷尾消息流传得极快,接连有小吏、士绅登门求见,场面越演越烈,崇福在街头招摇地出行,马车不加遮掩,前后仆从随行,一路清道。 他不言不语,但每到路口必令仆人高呼“驾到”,引来民众围观,甚至下跪叩拜,他用的器具都极为讲究,不仅衣饰华丽,还大量使用玉器、黄缎与京中样式的食器。 他饮水用玉盏,用膳讲究宫规,吃饭不许出声,说话需通传,他在行宫内自设内务班子,号令仆人不得正眼直视,赵德兴则负责对外接见,暗中收银受礼。 最初,地方官员未敢妄动,江夏知县陈树屏听闻传言后登门试探,竟被赵德兴斥退,知县不敢怠慢,先是递帖“请安”,接着命人密查宅内情形。 然而几日过去,所谓“圣驾”不但未离去,反而越发张扬,不但扩张院落,还私设仪仗,更有人传闻“圣旨即将颁布”,要张之洞入朝辅政。 这番闹剧终于传入湖广总督张之洞耳中,他原本不信,但情报细节过于真实且传言中涉及他本人,已影响政务,他立即派出私密探子前往现场核实。 不出一日,探子带回三件实物:黄龙绣被、玉质御印、内务府造的青花碗,张之洞眼见实物,意识到事态远超想象。 这不是普通冒名顶替,而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僭越,他密令捕拿该人,切断一切出城通道,并命城防营围住宅院。 捕人之夜,数十军卒悄然包围宅子,赵德兴发现异动,命仆人烧毁部分物品,但仍有御用品未能处理,崇福被捕时仍身穿明黄常服,坐于太师椅上,桌前摆着未饮完的茶。 赵德兴挣扎逃出后门,被城门军士当场擒获,张之洞命人连夜提审,亲自设堂询问,审讯过程十分简短,崇福面对铁证起初沉默寡言,赵德兴试图辩称“奉旨南下”,但在面对张之洞调来的宫中回信确认光绪仍在瀛台的证据后,两人情绪失控。 张之洞命人核查崇福身份,确认其乃京师某戏班艺人,曾以“演帝王像真”名声小有传播,赵德兴则确为前宫内司房太监,三年前被逐出宫。 御用品来源也有交待,大多为赵德兴潜藏未上缴之物,案件定性为“僭越谋诈”,依据清律,凡冒皇帝名号者,斩首不赦,张之洞不等朝廷批复,即定罪执行。 他在武昌草埠门设台当众行刑,公告城内,严禁议论,崇福被押赴刑场时神情麻木,赵德兴则不断喊冤求饶,声嘶力竭,行刑当日人山人海,围观者数千。 两人正午处斩,示众三日后焚尸,物品尽数销毁,档案封存,张之洞随后将全案梳理成卷,分送京师与周边各府,责令严查民间“异议聚会”“传言传播”。 京师接报后沉默未复,慈禧默许处理结果未追责,亦未奖赏,外界普遍认为张之洞办案得力,迅速稳定局势并压下风波。 此事过后,张之洞更严格控制地方治安,武昌府内多处茶楼被令关闭,民间文人集会遭严查,他心知冒充皇帝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社会动荡、朝政失衡下的裂缝体现。 他无权改变大局,但能维系表面秩序,他在武昌又坐镇十年,未再出现类似事件,崇福死后,其家人被驱逐出籍,不得进入州县户籍,赵德兴同伙亦被连坐查办。 此案在档案中定名为“假冒内监案”,但被内务府移入密卷,未公开流传,直到多年后,光绪驾崩于瀛台,世人才回想起那场闹剧,崇福一生戏子,最终将一场假戏演到了绝路。 赵德兴凭着几件旧物,撬动了武昌一城风声,却也没能带走任何真正的权力,张之洞作为守局者,用一场决断稳住地方,却也未能改变那个摇摇欲坠的王朝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