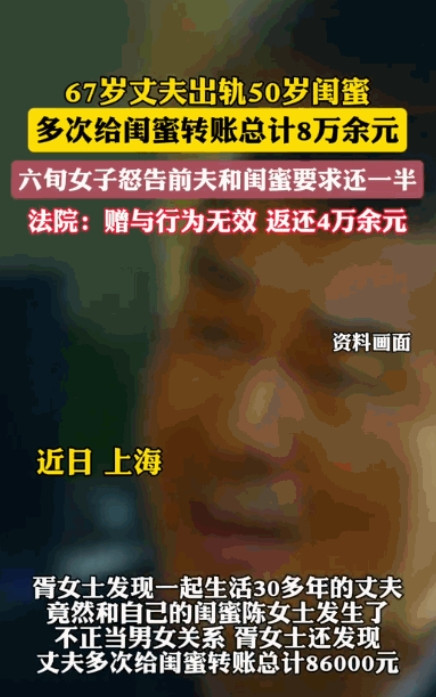1969年,上海知青张菊芬前往黑龙江讷河插队。临行前,她发现自己怀孕了。虽然她已经和男友分手,但她对他充满怨恨,更害怕家人知道这件事。为了逃避,她决定趁着插队的机会离开上海。 怀着身孕,离开上海的她没有勇气面对过去,也无法坦白家人,逃去讷河插队成为唯一选择。这条路既是逃避的出口,也埋下未来未知的伏笔。 1969年初春,张菊芬刚满十八岁。她出生在上海一个小康家庭,父母都是工人,从小接受红色教育,学习刻苦,成绩中上,却不算尖子。她有个男友,家境普通,两人关系稳定。 那个春天,她发现自己怀孕。这种消息在文革氛围下意味着彻底的破局。她知道家人对“有过关系”的死罪,她知道单位有“家丑不可外扬”观念,她知道学校干部们只接受“纯洁”的革命青年。 当她坐在镜子前抚摸小腹时,心里不是喜悦而是惊恐。朋友圈虽然有几个知己,但没有人能替她出主意,也没想过她会被怀念、被理解。这种愧疚和恐惧,让她连哭都没有机会。 家庭气氛在那天彻底崩塌。她隐约察觉母亲多次望向她的书桌抽屉,父亲的眉头越发深锁。家里有句话没明说,但足以让人窒息——“知青下乡”的名额不是给心怀叛逆者准备的。 张菊芬一咬牙,决定趁下乡之机离开。讷河,这个边远湿地小城,黑龙江南岸,和上海相比就像两个世界。那里没有人认识她,也没人会问起她的过去。 当知青队伍的号子在操场上响起,她揣着黑布包,打扮朴素,携带最少的私人物品。除了怀孕构成的隐秘,她仿佛一切都平静。 但没有谁能忘记那子宫里小小的胎动。那是她唯一的孩子,在外面一个月后,她们才认识到对方存在。弹跳、翻滚,像个生命在提醒她:阴影并没带走你。 第一站是镇区任务队。张菊芬被分配到稻田,春耕刚启,黑土地湿润发香,泥水淹过脚踝。寒风混合着河岸上凛冽的气息,空气质朴又刺骨。她要和当地青年一起支援犁田,插秧,晚餐吃的是粗粮粥、咸菜干。 在那里没人问她来历,没人提“上海哪个学校”。所有人先冷眼,再观察她是否干得过活。如果干得过活,也就有了立足资格。 她的肚子随着季节慢慢隆起,从起初的突兀到后来被稻田阳光遮藏。大伙不说话,但知道人分几类:有孩子的,没孩子的,看重家里的背景的,看重干活的。她属于最难的一类:没底牌,有秘密。 生活的节奏简单得像钟表。清晨天还没亮,她跟着喊声起床,抄过梦寐的情节,迎着露水上地。 午休时,她找地方躲着睡几个小时,累到连担心胎动都觉得奢侈。下午收工后,她背着工具回宿舍,一床被褥隔出两个世界:一侧放她买来的食盐和自带的洗衣皂,另一侧放宽松衣裤和藏在内袋的那本日记。 在宿舍里,她认识几个同样因家事入来的姑娘。没人关心她的怀孕,却对她吃得少、动作小心、脸色时好时差表示好奇。有人轻描淡写问一句:“腰疼吗?”她不答,只点头。别人没再问。 知青生活里每个动作都在磨时间:从分配地块,到点名,再到每个人相互借用火柴、啜饮草根茶。这些细节构成生活的全部。然而,张菊芬的视觉里,多了一条生命线——那肚皮的存在让她的步幅变短、呼吸更急,心跳更响。 不只是身体负担,更是心理重压。夜里她总在想着:生这个孩子,谁会管?奶粉从哪里来?给谁看病?打针要不要公费?她不想把孩子带回上海受辱,也懒得让家里猜你怀的确实是孩子。父母怕被抓走,学校怕被批判,单位怕被“污染”。一切都在沉默地斩断她对家的想象。 但即便这样,她依旧努力活着。她在田里尽量争气,多做活,拼着腹部疼也要完成指标。她知道只有自己撑住,才可能熬到挺入冬天。那个冬天,她要去县城医院检查胎位,要打几针什么补品——她没想得那么远,却不能退。 插队第一个月结束,她被评上勤学中队成员。没有表扬会场上的鞠躬,也没写什么先进事迹。只是在下发奖章时,队长轻声对她耳语:“你挺住。 ”那一瞬,她恨不得哭出声来,却忍住低头。奖章没有意义,但那是一剂药,提醒她至少现在活得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