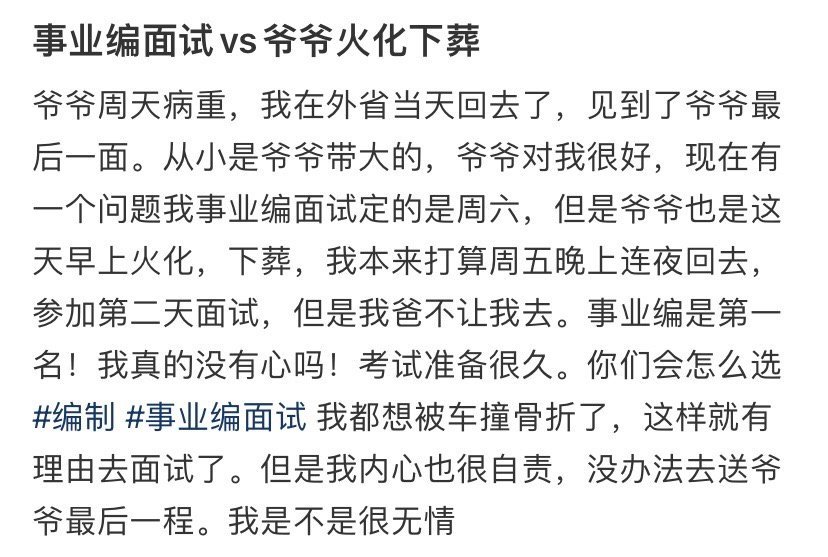孔子在15岁时,母亲便去世了,可是他却不给母亲下葬,就停放在马路边,行人看到后上前问他这是干什么?孔子说:“妈死了,不知道爹是谁,没法埋,”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公元前六世纪的鲁国,孔子以一个并不被看好的身份降生于世,他的姓氏“孔”源自祖上的封地,而名“丘”,取自他出生的山丘间,那时的鲁国,是一个礼崩乐坏、贵族凋敝的时代,而孔子,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夹缝中:父亲叔梁纥虽为鲁国的贵族后裔,但家道中落,年近古稀才得此一子;母亲颜徵在则出身寒微,身份上的悬殊让这段婚姻广被非议,孔子的降生既被视为“续香火”的希望,也被视为“逾礼”的产物。 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留下孤儿寡母在人情冷暖中自谋生计,叔梁纥的正妻与族人断然拒绝接纳这个“不合礼”的母子,将他们逐出家门,颜徵在带着年幼的孔子颠沛流离,最终落脚于曲阜的贫民街巷,生活的清苦几乎压垮了她,但她咬牙挺住,把全部的希望投注在这个孩子身上,为了生计,她靠浆洗缝补维持生活,孔子则在孩童时期便开始协助母亲,搬运水桶、劈柴烧饭,日子虽然困顿,却也在母亲沉默而坚定的教养中,逐渐孕育出一种超越贫贱的内在秩序。 在那个讲究“礼”的社会中,孔子的出身让他始终处于边缘,可正是这种边缘性,反而让他从小就对“礼”格外敏感——在别的孩子嬉戏打闹的时候,他却沉迷于模仿成人的祭祀仪式,甚至能准确地摆设祭品、辨认方位,六岁那年,他便能识六百字,邻里称奇,这份早慧并未被环境所湮没,反而在母亲的支持下得以延续,颜徵在明知家境拮据,仍坚持送他入学馆求学,那时的教育,重“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则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他不避身份低微,不耻下问,学问在不断积累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他与命运对抗的最有力武器。 然而命运似乎并未打算轻易放过他,十五岁那年,颜徵在积劳成疾,撒手人寰,对孔子而言,这是一次彻底的崩塌,他不仅失去了至亲,更陷入了一个无解的困局:母亲应葬何处?按照周礼,“祔葬”是合乎礼法的安排,即亡者应与配偶同穴合葬,然而孔子从未被允许知道父亲的墓地所在,族人亦不承认他的存在,一个贫寒少年,面对既不认亲也不认礼的家族,如何为母亲寻得一个体面的归宿? 孔子没有屈服,他将母亲的棺椁停放在曲阜的十字路口,日夜守灵,不顾他人非议,在那个讲究礼教的时代,这种行为几乎等同于对世俗的挑战,他以沉默与哀痛,唤起了世人的关注,纷纷议论之中,终于有一位年长者现身,指认出孔子父亲的葬地,孔子借此完成了母亲的遗愿,将其安葬于父墓旁,虽未获家族正式承认,却在精神上完成了孝道的终点,这一过程,不只是他对母亲的深情告别,更是他对“孝”与“礼”的一次自我实践——在无法依赖传统权威时,他以个人行动重塑了人伦秩序。 守丧三年后,孔子开始踏入社会,他并未立刻成为学问大师,而是在现实的泥淖中摸索前行,他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吏,也为人操办丧事婚礼,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他曾前往齐国寻求仕途机会,但因政局动荡与理念不合而失望而归,归国之后,他在自家院中设馆授徒,原本只是为了糊口维持生活,却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孔子从未设门槛,只要愿意学习,皆可入内,他提出“有教无类”的理念,打破了贵族垄断知识的传统,让平民子弟也有了受教育的可能。 教育成为他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也成为他实现理想的第一步,从教学中,他提炼出一套关于“仁、礼、义”的伦理体系,主张以德治国、以礼正俗,这些思想并非空中楼阁,而是他在现实苦难中锤炼得来的,他知道制度可以腐朽,人心可以冷漠,但只要人还有对“道”的追求,社会就有复兴的可能。 五十一岁那年,孔子终于担任了中都宰,相当于一县之长,他以严明的治理、礼法的推行使当地焕然一新,声名远播,然而,官场的复杂并非理想之地,政治斗争很快将他边缘化,甚至连家庭也不再是避风港,他与妻子亓官氏分道扬镳,终究未能守住这段婚姻,孔子毅然辞官,开始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之旅,试图向各国君主推行他的政治理想。 这段旅途注定坎坷,他在卫国受辱,在陈蔡之间几近饿死,时时被怀疑、时时被拒绝,但他始终坚信“道之将行”,哪怕只剩下一人守着这份信仰,弟子颜回的早逝、儿子孔鲤的去世,让他晚年愈发孤寂,但即便如此,他依旧每日讲学、整理典籍,将一生所学传诸后世。 公元前479年,孔子在鲁国辞世,他临终前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不是一个政治家的遗言,而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对世界最后的寄望,他一生未能实现宏图,却在教育与思想上留下了不朽的遗产,他所走的一路,是无数普通人曾走过的苦路,却被他踏出了文明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