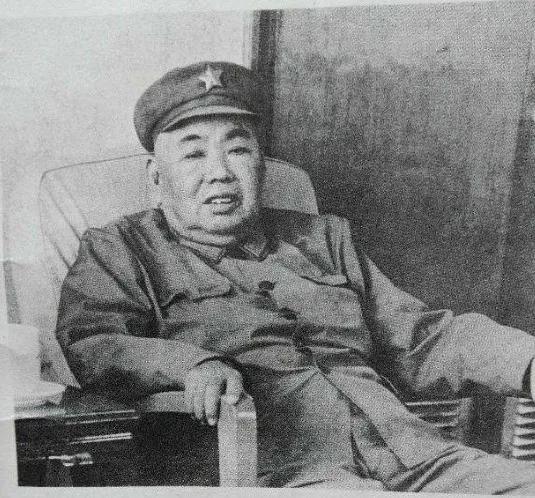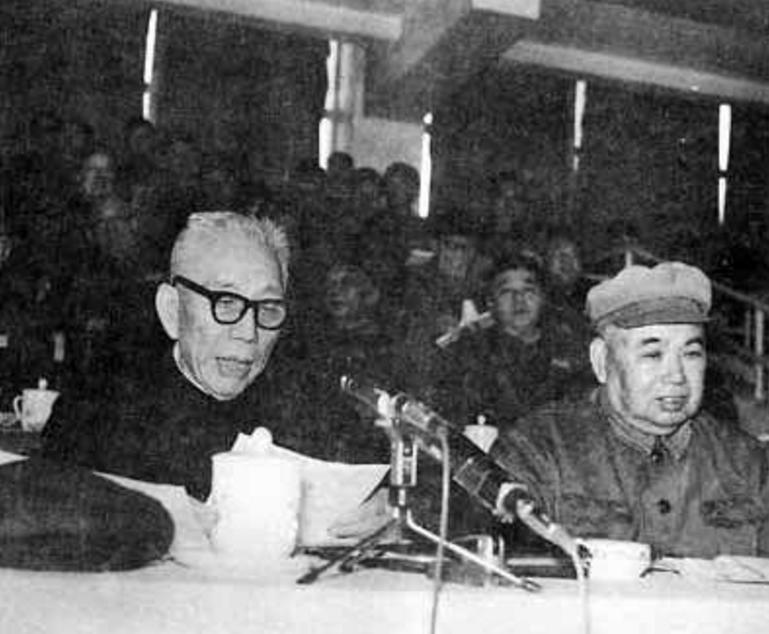许世友退居二线回老家,遭子女反对,许世友:脱下军装我还是农民 “1983年初春的凌晨四点,你真打算把户口迁回新县?”警卫员打着哈欠问。许世友挎着竹篮,边往里放种子边回一句:“我这把年纪,还能骗你?” 决定回乡不是心血来潮。1980年9月,中央军委通知他专任常委,按惯例应迁居北京。许世友回绝,说气候不合适,也说要写回忆录,实则惦记大别山的土地。报告递上去,一个月后批复到手,他哈哈大笑:“棉衣不用换了,南京离老家近。”自此,他走上“半隐居”之路。 往前倒二十多年,1960年代初,南京军区食堂缺菜,他一句话:“菜自己种,别把难处全推给地方。”很快,连队有菜地,师团搞农场,军里建养殖基地。内部供应改善了,南京市场上的鸡鸭鱼蛋也多了。老百姓评价:“许司令来了,白菜都硬气。”这股子务实劲,其实早在童年就埋下。 1905年,他生在鄂豫皖交界的新县。山高路陡,地少人多,成年男子一到青黄不接就外出谋生。母亲常念叨:“庄稼不负人,懒汉才丢脸。”许世友七岁割草,十岁放牛,练成一身腱子肉。后来闯少林、混旧军队,再到1926年参加农民运动,他始终记得家里那把锄头。参军不过换了件衣裳,身份没变。 抗日时期,1942年胶东大生产紧急展开。日军封锁,盐都成稀罕物。他在会议上掷地有声:“有盐同咸,无盐共淡。”随后司令部挑了块河滩荒地,他带头挖渠,战士们干得像抢高地一样拼。年底统计,开荒数千亩,省下口粮六十五万斤。许世友拍拍裤腿:“老百姓少交一升米,咱心里就踏实。” 生产能撑过饥荒,群众的情义却救过命。1943年,他在一次小规模突围中负伤,同从部队掉散。两位砍柴人把他扛进窑洞,用碎玉米面熬粥喂了五天。枪伤好转,他要给钱,对方摆手:“你当兵护咱们,我们出点力算啥!”这种情节,他后来多次提起,每次眼圈微红。 战争结束,军装上的星越来越多,但生活习惯没跟着“升级”。别人聚会把酒言欢,他一口白开水配几瓣蒜,大碗面条三下见底。客人纳闷,他自嘲:“胃口跟土地学的。”1971年军区农场丰收,他亲自拿二十斤大地瓜拍照寄北京,附条子:“主席,土里掏出来的,第一年试验就这么大。” 时间跳到1984年夏天,许世友真的动手把南京住所改造成“迷你乡村”。围墙花坛推平,起猪圈;西侧空地挖方塘,放草鱼鲢鱼;楼前菜畦一字排开,黄瓜豇豆辣椒全都自己侍弄。每天清晨,草帽草鞋,肩扛锄头,谁看都不像上将。警卫员说他“活得太省”,他一摆手:“省不省无所谓,图个爽快。” 家人却不买账。夫人田普先是沉默,后半玩笑半认真:“孩子大学工作都在城里,你弄这一套,他们回来住哪儿?”儿子许光直言:“爸,您辛苦一辈子,该享福。”许世友把烟锅往桌上一磕:“脱了衣服我还是农民,真要享福,地里刨食最舒服。”两代人观念冲撞,最后形成各过各的默契:孩子们留在大城市,他留在菜畦鱼塘。 位高权重者偏爱打猎并不稀奇,他却把打猎当农事延伸。1973年中央发文禁止随意开枪,他在批示栏勾一句:“猎兽停,打鸟可保庄稼。”文件照发,但他自觉收枪,只保留一支老猎枪当摆设。晚年偶有媒体想采访,他婉拒:“新瓶装旧酒没意思,让嘴巴歇歇。” 1985年10月,他病危,身边人提出送北京医治,他摇头:“回老家。”几天后病情恶化,无力再动。这位一辈子行动力惊人的硬汉,只留下简短嘱托:“把我埋在母亲旁边,多带点家乡土。”同年10月22日,许世友在南京去世,后安葬于新县,墓碑前常年摆放的,不是精致花篮,而是一筐新挖的红薯。 有意思的是,子女们渐渐理解父亲。1990年代,交通条件好了,他们常带孙辈回新县。田野边,村民指着稻穗聊天,小孩泥巴裹鞋不肯脱,许家长辈会心一笑:这景象,正是老人家想看到的。许世友说过,枪打完了,地才是根。如今根在,故事也在,风吹过大别山,依旧是熟悉的土腥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