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开枪!我是中国人,我带领 218 多名军人来投降。”1979 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冯增敏焦急地向越军喊话。他的钢盔歪在一边,军装上的血渍混着泥浆,像幅被揉皱的地图。 身后的 218 名士兵,有的拄着断枪,有的抱着受伤的战友,枪管在丛林里拖出沙沙的响 —— 那声音,比越军的机枪声更让他心头发紧。 三天前,448 团 3 营接到的命令是 “清剿残敌,掩护主力回撤”。 冯增敏在作战地图上圈出那片名叫 “朗庄” 的山林时,晨雾正从山谷里漫上来,像极了他老家四川盆地的早春。 出发前,炊事班长塞给他两个馒头,说 “连长,这是最后两袋面粉做的”。 他现在摸着怀里变硬的馒头,突然想起 1975 年新兵训练时,老班长说的 “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投降’两个字”。 可那时的老班长,没教过弹尽粮绝时,该怎么面对 200 多张年轻的脸。 包围圈收紧在第二天黄昏。越军的迫击炮弹落在炊事班的位置,炸起的泥土里混着面粉袋的碎片。 冯增敏看着卫生员把最后一块纱布缠在伤员腿上,那伤员才 18 岁,是家里的独苗,出发前还给他看过妹妹的照片。 “连长,拼了吧!” 副连长的步枪上了膛,枪栓拉动的声音在寂静的丛林里格外刺耳。 冯增敏却盯着指南针 —— 他们已经偏离预定路线 15 公里,电台在昨天的轰炸中报废,喊杀声从三个方向传来,像张越收越紧的网。 夜里下起了雨,伤员的呻吟声和雨声混在一起。冯增敏靠在树干上,摸出贴身的笔记本,上面记着全连的花名册。 他一个个划名字,划到一半突然停住 —— 每个名字后面,都标着籍贯和家庭情况: “王二柱,河北,父母务农”“李建国,湖南,烈士子弟”…… 这些是他上个月刚统计的,为了战后给家属寄立功喜报。现在雨水晕开了墨迹,那些名字变得模糊,像要从纸上漂走。 黎明时,最后的手榴弹被分发下去。冯增敏看着士兵们把拉环套在手指上,突然想起自己的入党申请书:“愿为国家和人民牺牲一切”。 可 “一切” 里,包不包括让这些孩子活着回家?他想起出发前,有个新兵的母亲来送站,往他兜里塞了包花生,说 “连长,多照看着点”。 那包花生,现在还在他背包最底层,壳已经被体温焐得发软。 喊话的那一刻,冯增敏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越军的翻译官用生硬的中文喊 “放下武器” 时,他第一个把步枪扔在地上。 枪托砸在石头上的闷响,让身后的士兵一阵骚动。有个新兵哭出声来:“连长,我们成汉奸了?” 他没回头,只是挺直了腰 —— 他知道,这一弯腰,这辈子都直不起来了,但至少,这些哭出声的孩子,还能有机会再哭给爹娘听。 越军把他们押往俘虏营的路上,要经过一条河。冯增敏看见水里漂着顶解放军的钢盔,上面的红五星被弹片刮掉了一半。 他想起 1978 年抗洪救灾时,就是戴着这样的钢盔,和战友们手拉手堵决口。 那时的河水是暖的,现在的河水却冰得刺骨,像要钻进骨头缝里。 有个越军踢了他一脚,骂着 “亡国奴”,他没吭声,只是把掉在地上的伤员往自己这边拉了拉。 军事法庭的灯光很亮,冯增敏看着公诉人念起诉书,每念一句,他就想起一个士兵的脸。 当法官问 “你认罪吗”,他沉默了很久,说 “我认,但求从轻处理我的士兵”。 旁听席上有家属在哭,他不敢抬头 —— 他知道,那些眼泪里,有恨,也有或许存在的、一丝说不清的感激。 10 年徒刑的判决下来那天,他要求见的最后一个人,是 448 团的团长。 他没为自己辩解,只是把那本浸了雨水的花名册递过去:“团长,告诉他们家里,孩子们…… 活着。” 1989 年冯增敏出狱时,四川老家的油菜花正开得金黄。他不敢去打听那些士兵的下落,只是在村口开了家小杂货铺。 有天来了个瘸腿的男人,买烟时盯着他看了半天,突然跪下:“连长,我是王二柱啊!” 冯增敏摸着他腿上的伤疤,那是当年在朗庄留下的。 男人说,他们这批俘虏在 1982 年被遣返,大部分回了老家,有的进了工厂,有的种了地。 “大家都念叨你,连长,要不是你……” 夕阳把两个男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冯增敏看着远处田埂上奔跑的孩子,突然想起那个 18 岁的独苗伤员。 王二柱说,那孩子后来当了小学老师,教孩子们唱《我是一个兵》。 杂货铺的收音机里,正播放着对越自卫反击战胜利 30 周年的报道,播音员的声音激昂,冯增敏却悄悄关掉了收音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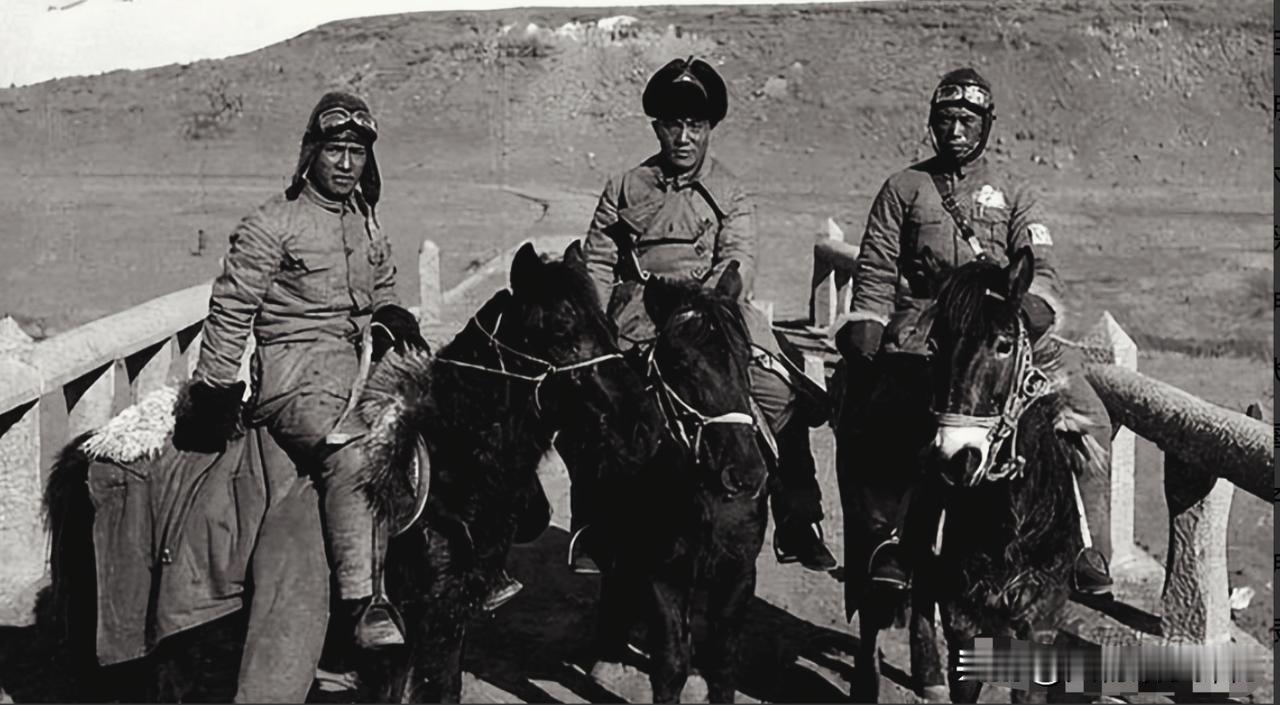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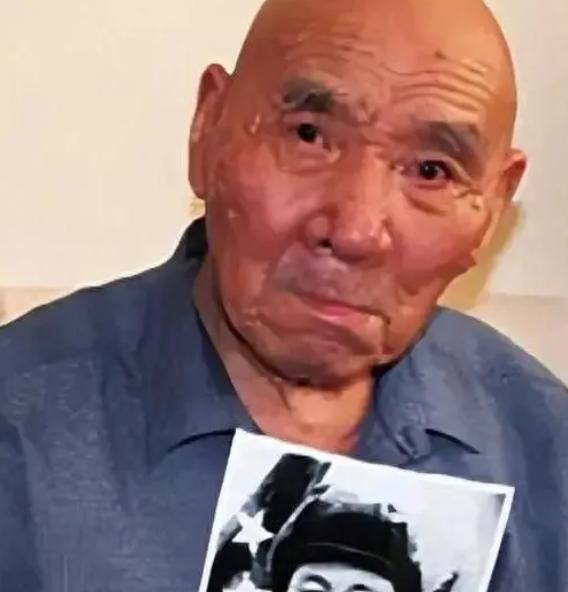




用户10xxx71
[点赞][点赞][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