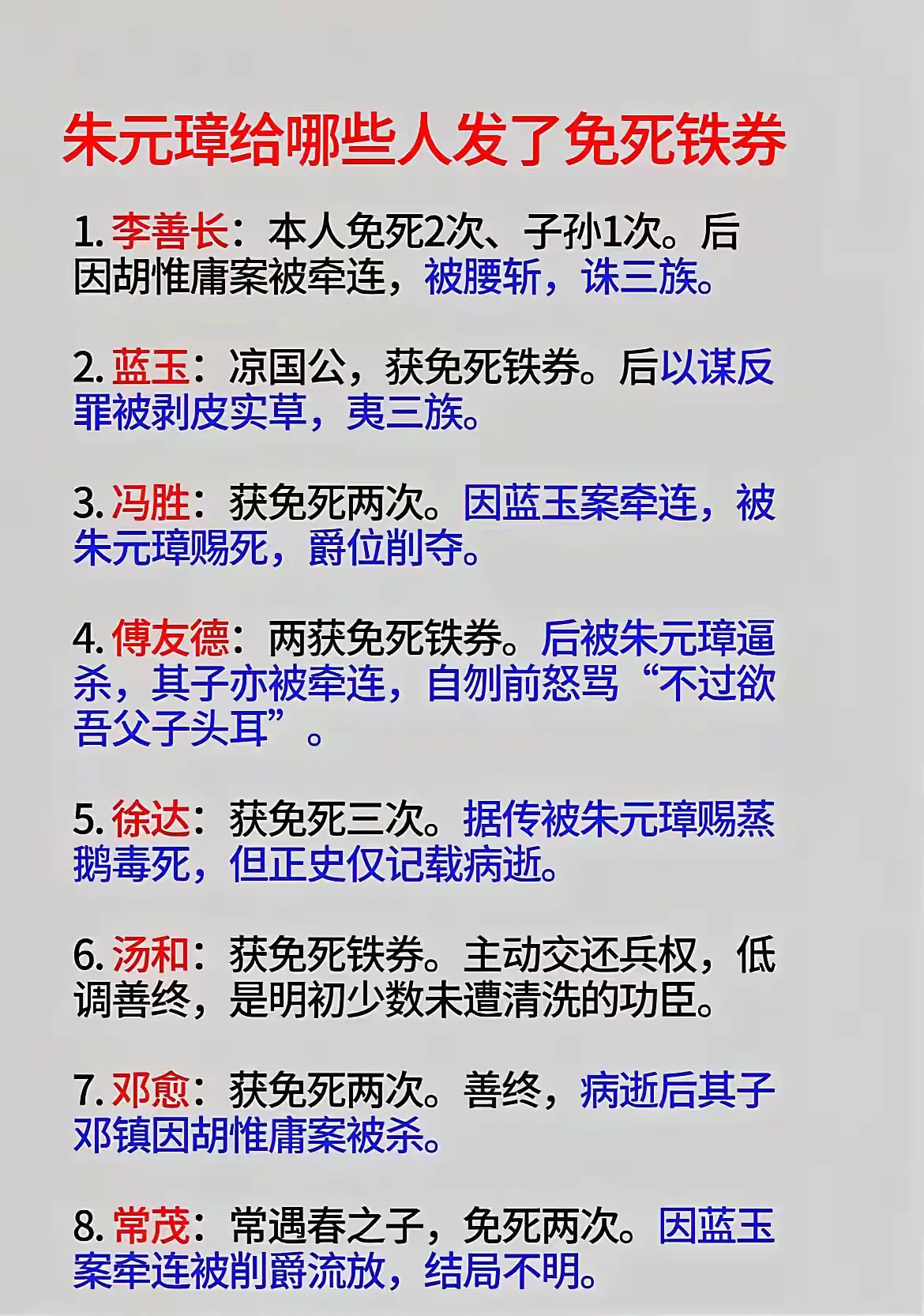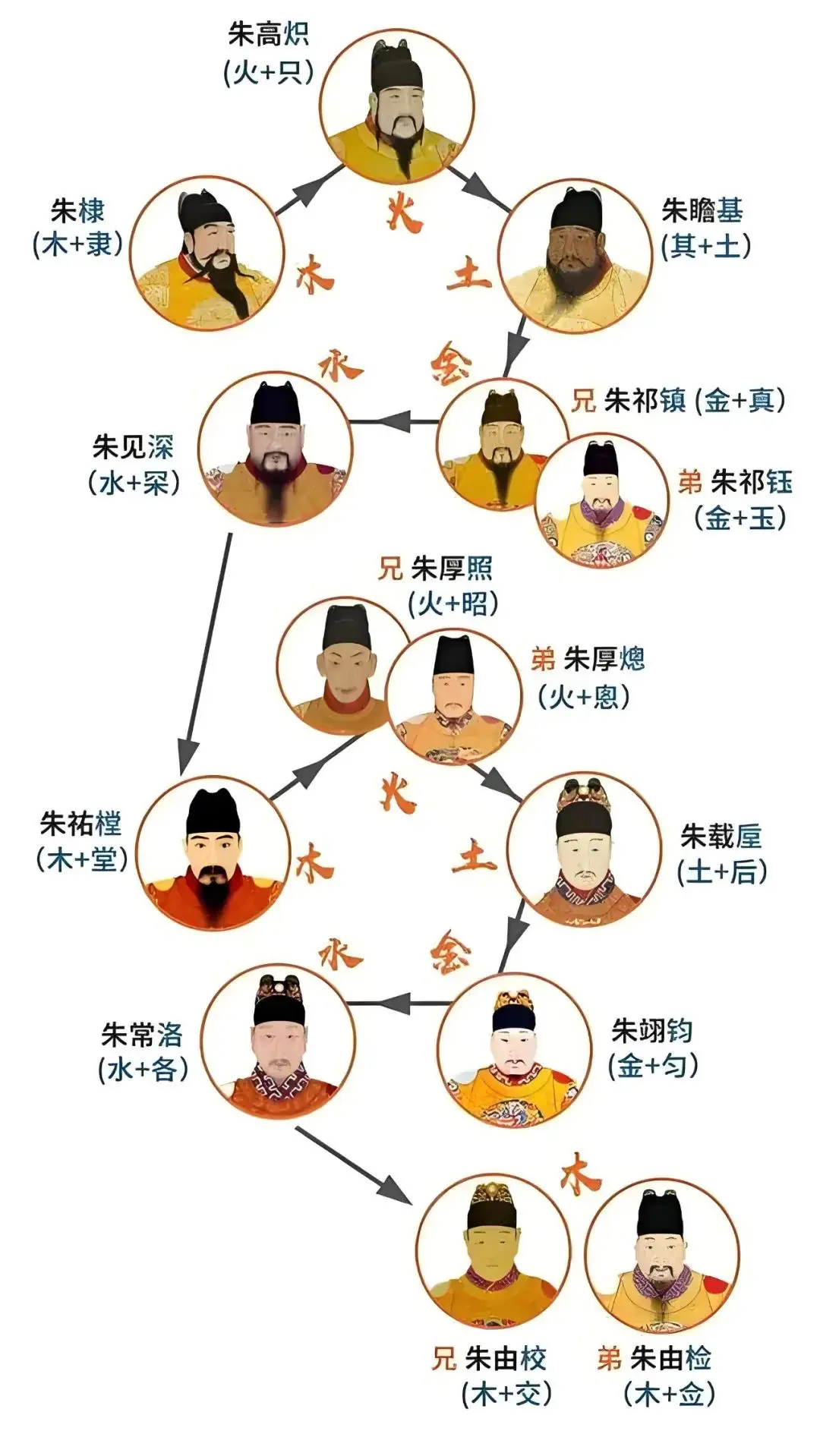从底层崛起的皇帝朱元璋,对任何损害民生、动摇统治根基的行为都抱有极高的警惕。 在位期间,他针对劣币流通问题的追查迅速展开,一批被认为在此事上失职、渎职乃至同流合污的地方官员,很快就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可能是生命的代价。 然而,仅仅处罚几个官员并不能根治问题,朱元璋也曾将目光投向更宏大的货币改革,尝试发行“大明宝钞”,试图用国家信用支撑的纸币来统一货币流通,并将铸币权牢牢收归中央。 可谁知,由于缺乏成熟的管理机制和有效的信用保障,加上超发滥印,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宝钞很快就经历了剧烈的通货膨胀,价值一落千丈,几乎沦为废纸。 这次纸币改革的失败,给了雄心勃勃的朱元璋一记响亮的耳光,但也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货币体系的建设远非一纸敕令那么简单,它需要更周密、更具操作性的制度设计。 纸币的跟头并未让这位铁腕帝王气馁,反而促使他调转方向,在传统的铜钱上寻找更务实的管理办法,一个看似简单却颇具巧思的念头浮现,何不让每一文钱前面都加上一个“籍贯”? 于是,“洪武通宝”的背面,开始出现了“北平”、“浙”、“粤”、“闽”等地铸钱局的简称,这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标记,更是一道责任的枷锁。 从此,每一枚铜钱都承载着其诞生地的信息,一旦市面上再出现劣质钱币,追根溯源便有了明确的线索,地方官员再想以“来源不明”来推诿塞责,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这无疑给各地负责铸币的官员戴上了一道无形的紧箍咒,迫使他们加强对铸造流程的监管,提升钱币质量。 这一措施,虽然未能彻底杜绝私铸和劣币,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地方官员的责任感,为稳定明初脆弱的货币金融体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钱币上的小修小补,远不足以扑灭帝国肌体深处熊熊燃烧的贪腐烈焰,真正让整个大明官场为之震动、为之胆寒的,是郭桓案的惊天炸雷。 时任户部侍郎的郭桓,被查出在征收全国赋税过程中,利用职权,上下其手,内外勾结,贪污侵吞的粮食等物资折合竟高达四千四百万石。 这个天文数字般的贪腐额度,不仅掏空了国库,更足以让任何习惯了朝堂之上歌舞升平的文武百官瞠目结舌,消息传出,朝野哗然,也彻底点燃了洪武皇帝胸中积郁已久的对贪官污吏的滔天怒火。 郭桓及其遍布全国的同党的伏法,绝不仅仅是一次常规的贪腐案件处理,这次案件的处理方式主要是酷烈的处死及其牵连之广,标志着大明王朝的反腐斗争,自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为严酷、更加不留情面的铁腕肃清阶段。 伴随着这场风暴呼啸而来的,是那条足以让所有官员,无论职位高低,都背脊发凉的冷酷铁律,凡贪赃枉法,受贿数额达到六十两白银以上者,一概处以极刑。 这道清晰而残酷的红线,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每一个官吏的头顶,成为朱元璋震慑贪欲、整饬吏治最直接、也最令人畏惧的武器。 只是,如此酷烈的刑罚,固然能在短期内对潜在的贪腐行为形成强大的威慑力,营造出一种“伸手必被捉,捉到必杀头”的高压氛围,但硬币总有另一面,过度依赖重刑,尤其是在缺乏完善的司法程序和有效辩护机制的情况下,也极有可能扩大打击面,造成冤假错案。 在“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极端思维驱动下,多少官员可能仅仅因为牵连、因为捕风捉影的告密,甚至是因为政敌的构陷而无辜丧命?历史的尘埃往往掩盖了细节,留给后人的,除了对贪腐的憎恶,或许还有对酷政下个体命运无常的深深叹息。 朱元璋的目光,不仅死死盯住官员们伸向钱粮的手,也落在了那些记录着帝国财政运转的账簿之上。 他深知许多贪污舞弊,正是通过在账目上做手脚来完成的,为此,他又颁布了一道看似与反腐关联不大,实则用心良苦的规定:所有官方机构的文书往来、财政收支以及商业活动的记账,都必须统一使用笔画繁复、结构复杂的“正体字”。 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其背后的逻辑其实相当直白,甚至可以说有些“刁钻”:繁体字笔画多,结构复杂,想要在账目上进行涂改、挖补、伪造,技术难度自然大大增加,也更容易留下破绽。 相较于笔画简单的字体,篡改繁体字账目需要更高超的技巧和更大的风险,这一措施,与钱币上刻铸造地简称的做法,可谓异曲同工,都是试图从技术细节层面入手,压缩贪腐行为的操作空间,是其构建清廉高效政府宏大蓝图中,一个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他期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帝国的财政脉络尽可能清晰、透明,难以被蛀虫们轻易侵蚀。 信源:大中通宝 中国古代钱币 信源: 大中通宝专题.华夏古泉网 2012-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