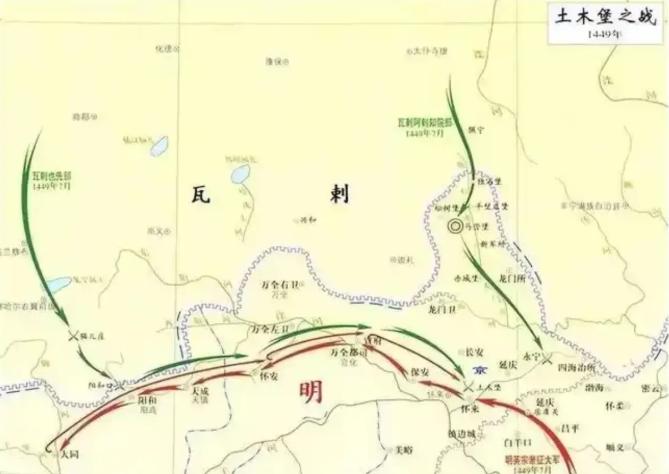1949年5月1日凌晨,黄海之上,国民党海军“永兴号”巡逻舰上突然爆发枪声。
一场早已策划的起义被打乱节奏,短短几个小时内,舰长被流弹击毙,起义者被毒气活活熏死在船舱里。
舰上的电讯室成了临时毒气室,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味与呕吐声,几名年轻海军兵拼命捶打铁门,无人回应。
“永兴号”是一艘美制PCE-842级巡逻舰,原先归属美军,战后作为援助移交给中华民国海军。
1946年它巡逻过南海,并因曾驶抵西沙的“永兴岛”而得名。
这艘舰在当时属于国民党海军的中坚战力,舰长陆维源是桂系重将桂永清的心腹,作风严厉,脾气暴躁,在舰上几乎一言堂。
早年他参与过台湾“二·二八事件”的镇压,在官兵中威信与恐惧并存。有人说他铁面无私,也有人私下叫他“疯狗”。
舰上的紧张气氛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
早在1948年,国民党海军已经人心浮动,频繁调防、物资短缺、军饷拖欠,士兵动辄几个月拿不到工资。
老兵盼退,少兵怕战,不少人偷偷收听大陆电台的“对海军广播”,听说解放军对投诚人员“有吃有穿”,甚至有人能调去学校继续深造。
这些话没人敢公开说,但夜里在甲板上抽烟的士兵都听得见彼此的牢骚。
航海军官陈万邦就在这个时候萌生了另谋出路的想法。
他是舟山人,早年受过一点新式教育,会英语,读过《星岛日报》和《大公报》,能看出局势的走向。
他对国民党早已心寒,尤其看不惯陆维源动不动打骂下属,还克扣军械津贴。他偷偷联系了军需官朱纪刚,还有几个信得过的操舵手和机工,一共不到十个人,开始秘密筹划起义。
他们的计划其实很简单:趁舰队夜巡,控制驾驶室,封锁通话系统,掌控轮机室,然后掉头向北驶向解放区,预计落脚点是山东沿海。
事情出在了那天夜里,起义原定在零点发动,陈万邦按计划带人进入驾驶舱控制舰桥,开关电路系统。
但就在刚开始行动的十分钟内,舰内的通话设备并没有完全被切断。
陆维源通过内部广播喊话:“驾驶舱出事,全员就地备战!”舰上其他官兵一时还搞不清状况,但熟悉陆维源的脾气,没人敢耽搁,很快就各就各位。
局势迅速失控。陈万邦和朱纪刚控制了船头,但轮机舱那边的人临时退缩了。
有个原本答应配合的机工反悔,还试图去报告舰长,结果被同伙用扳手砸晕。
副舰长彭广得知驾驶舱被占,立即带人封锁走廊,组织反击。
他原本在舰上没什么存在感,但这时候却表现得极其强硬,先调了两个轻机枪组压制驾驶舱,又带人封死电讯室和弹药库。
短暂的交火中,陆维源竟被误伤。
有人说是驾驶舱里的反击流弹,有人说是彭广的人误打,但当场他就倒在舱口,口鼻流血,临死前一句话都没说。
这一幕直接点燃了舰上剩余官兵的情绪。
朱纪刚在混乱中被击中胸口,当场毙命,驾驶舱内其余几人拼命反击,但火力明显不敌。
陈万邦中弹后跳海,试图游向附近海岛,有人看到他在水中挣扎几下就被甲板上的机关枪扫射击中,浮尸飘出两百多米才沉下去。
剩下的五个人退守电讯室,把门反锁,用桌椅顶住,舰上负责化学武器储备的军械兵奉命取来了催泪弹与浓烟弹,改装后朝电讯室通风管投入。
不久舱内便传出剧烈咳嗽声,有人用鞋子猛砸铁门,有人大喊“别放了!我们投降!”但没人理。
几分钟后再开门时,五具尸体倒在一地,眼睛睁着,嘴里都是血泡。
事后,为掩盖事件的恶劣影响,舰队司令部命令对此事严格封口,公开口径是“扑灭叛乱,歼匪数名”。
舰名也迅速更改为“维源号”,以纪念“忠烈舰长”陆维源,这种处理手法在当时其实并不稀奇。
早在“重庆号”起义那年,就有不少海军起义者被“失踪”或秘密枪决。
陈万邦的家属很长时间没收到任何正式通知,只在一本旧兵籍簿上,找到一句涂改后的批注:“殉职,海上暴乱”。
而那些曾参与镇压行动的军官,不久后纷纷升迁,副舰长彭广升为舰长,1950年参与金门补给任务,在炮击中负伤退役。
这起事件之后,舰队内部再也没人提起那天的事,甚至很多新兵根本不知道这艘船曾经改过名,更不知道电讯室曾被用作临时毒气舱。
1949年下半年,国共战局逆转,多数国民党海军舰艇开始“船上有人喊口号、下船就没人跟”的状态。
一些军官公开表态“只管开船,不掺政治”,而“永兴号”这样的事件,也成为了极少数以毒气方式“解决内乱”的案例。
1951年,“维源号”正式退役。有趣的是,它在1950年的料罗湾海战中,曾误击己方鱼雷艇,导致两艘小艇沉没,造成几十人伤亡。
有人私下评论说,“这船自带霉运”。舰尾原刻的“YONGXING”英文名牌早已锈迹斑斑,被人私下拆去换酒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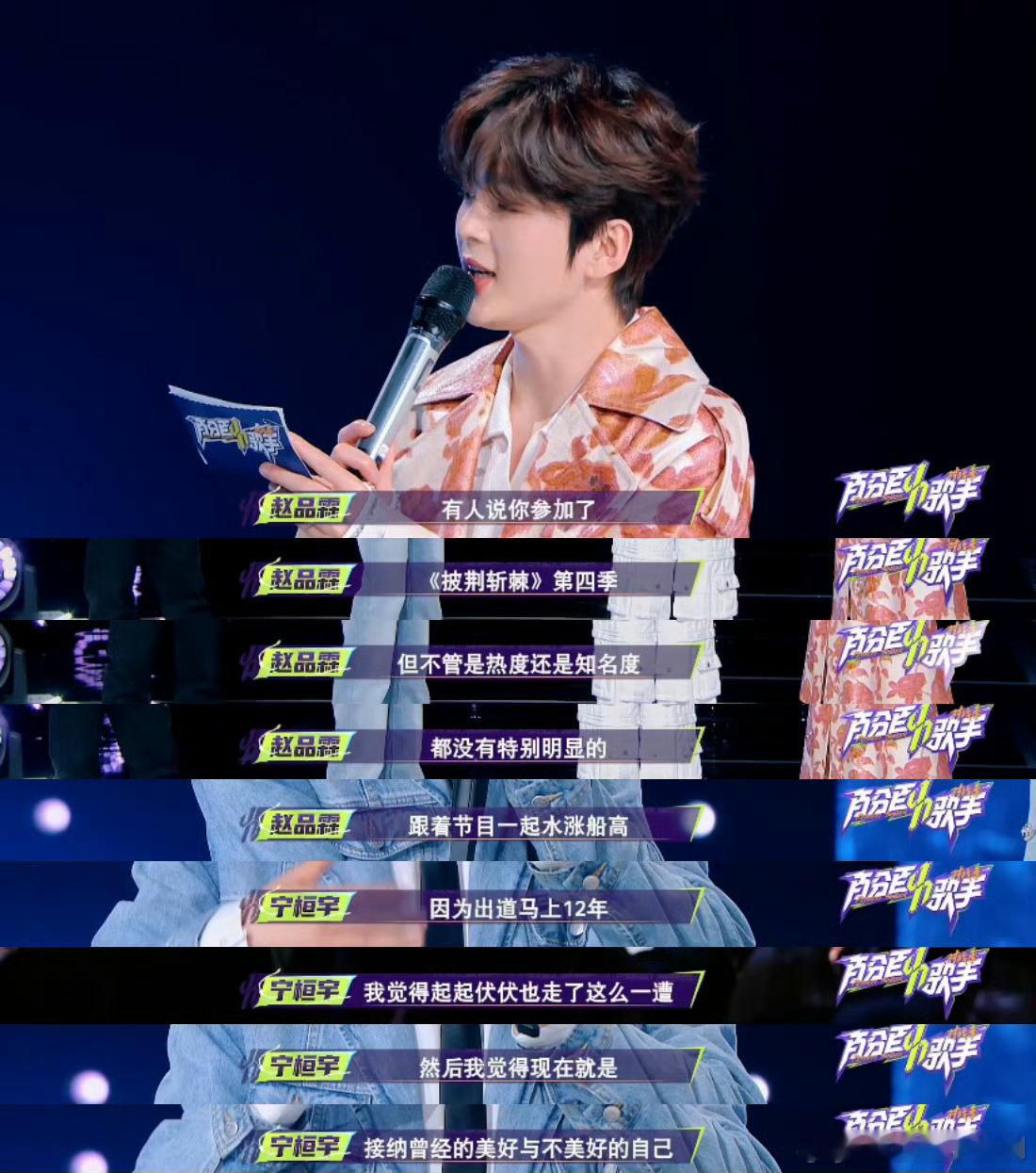
![古代有什么吊打现代的东西吗?[捂脸哭][捂脸哭][捂脸哭]](http://image.uczzd.cn/7249601790318641965.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