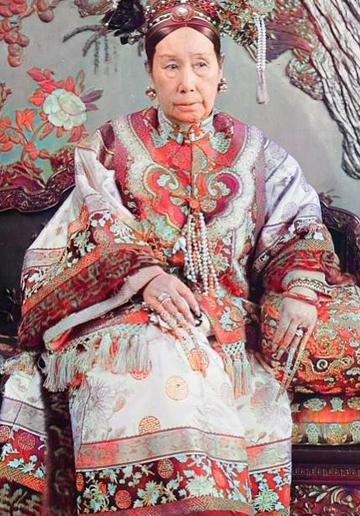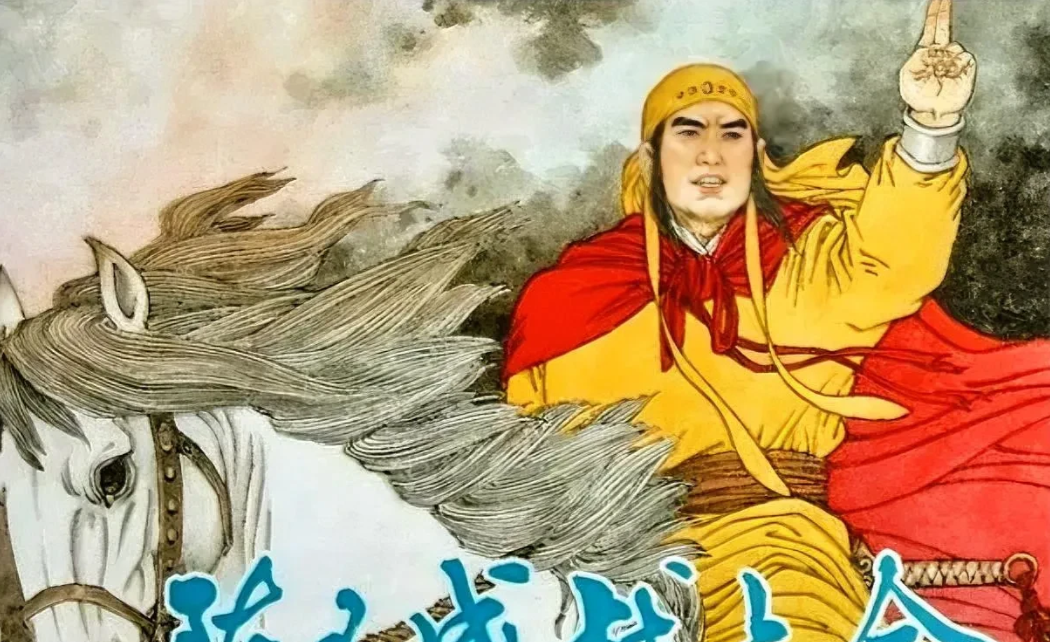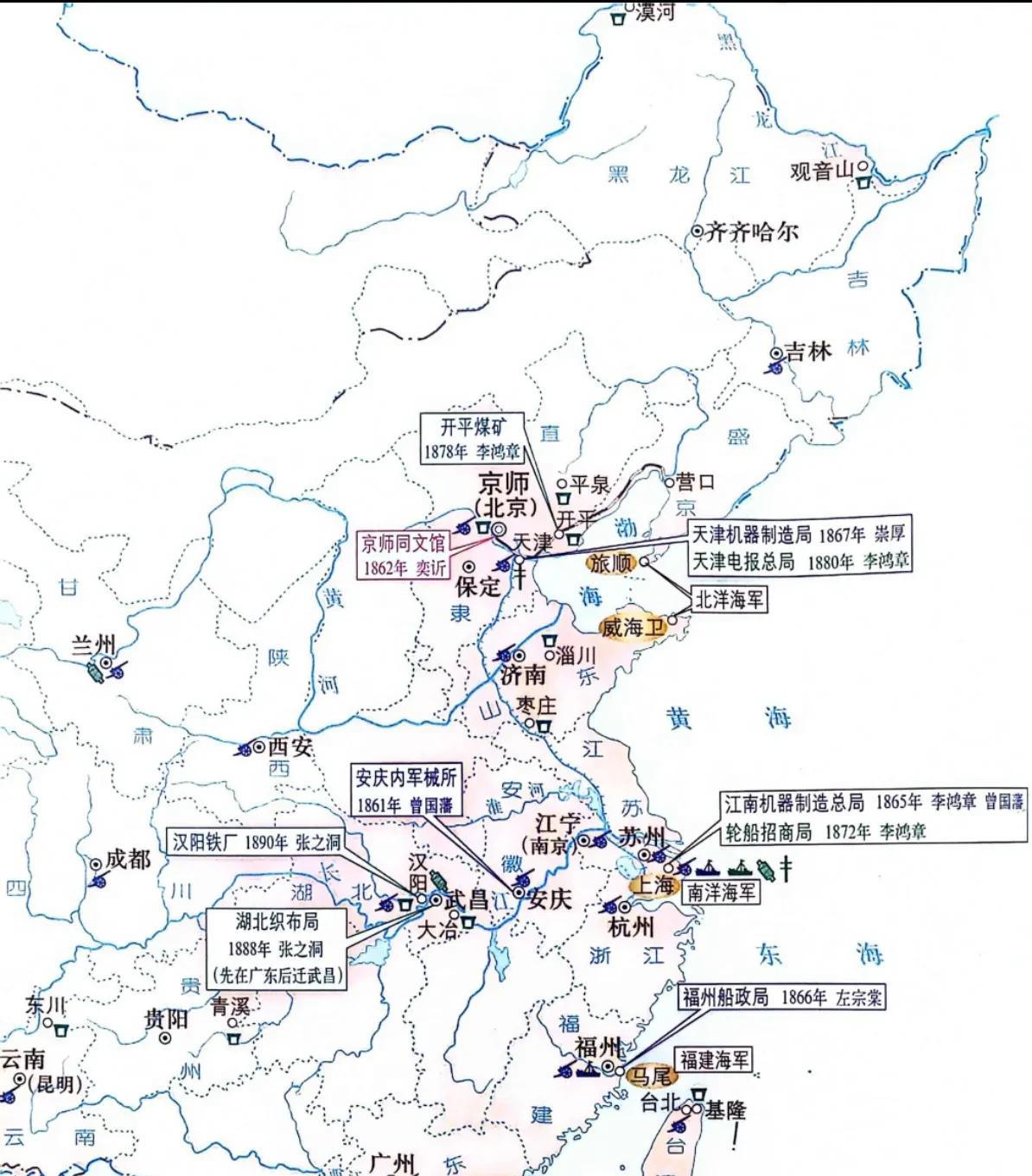清朝末年,一个底层佃农家庭的破产之路。 晚清四川仪陇,朱邦俊一家是典型的底层佃农。朱邦俊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九十岁了还下地干活,靠的就是一股子倔劲儿。他老婆潘氏管家有道,精打细算,儿媳钟氏勤快能干,带着一堆孩子撑起这个家。二十多口人挤在一块儿,靠种地过日子,苦是苦了点,但全家齐心还能凑合过。 他们家祖上分了七挑多田,外加一间老屋。搁以前兴许够用,可人口一多,这点地压根不够填肚子。没办法,朱邦俊把田和屋子典出去,换了三百吊钱,举家搬到李家湾,租了地主丁邱川八十挑田,每年得交五十担租粮。住的地方是丁邱川扔那儿不要的粮仓,破得四处漏风,屋顶还滴水,日子过得真叫一个艰难。 朱家的饭桌上没啥花样,豌豆红薯打底,白米饭是稀罕物,肉更是过年才能见一回。衣服全是粗布做的,补丁摞补丁,一件袍子全家轮着穿。丰收年还能添块新布,歉收年连补丁都没得补。省吃俭用是常态,每粒粮食都金贵得不得了。 全家老小都得干活。朱邦俊扛着锄头下地,潘氏在家管孩子喂猪,钟氏田里屋里两头跑。辛苦归辛苦,靠着这股子韧劲儿,日子总算能维持。1892年左右,仪陇开始种鸦片,朱家攒了1200个铜钱,咬牙送仨孩子去读书,想着兴许能翻身。可这点小希望,很快就没了影儿。 1895年,地主丁邱川冷不丁要加租,五十担租粮本来就够呛,再加一点朱家根本扛不住。大年三十晚上,丁邱川派人来赶他们走,连个喘气的机会都不给。朱家没办法,只能收拾东西搬走。那天晚上,北风吹得人发抖,一家子拖儿带女离开住了好几年的破粮仓,往后日子更不好过了。 搬走后,朱家一分两处,借钱把老屋和祖田赎回来。可老屋破得不成样,田地也荒了大半,收成少得可怜。借的钱没还上,利滚利越攒越多,债主三天两头上门催。朱邦俊老了,腿脚不利索还得下地,潘氏算计来算计去也填不上窟窿,钟氏带着孩子累死累活,日子还是越过越糟。 债务像座大山,压得朱家喘不过气。朱邦俊一把年纪还得干活,潘氏手都磨出血了,钟氏瘦得皮包骨,孩子也帮不上啥忙。债主不讲情面,上门把家里最后点东西都搬走,田地又没了,家底彻底空了。二十多口人四散开,有的出去讨饭,有的投靠亲戚,朱家就这么散了架。 朱家的故事,不是个例。那时候清朝末年,朝廷乱糟糟,税收重,地主狠,底层农民日子过得像刀尖上舔血。朱邦俊一家勤勤恳恳干了一辈子,到头来连个安稳窝都没保住。种地收成不好得饿肚子,收成好了地主加租,租子交不上就得滚蛋,滚蛋了还得借债,债还不下就家破人散。这循环,跟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谁都跑不掉。 为啥会这样?一是人口多,地少,祖上的田分到后来不够吃。二是地主剥削重,租子高得离谱还不算,动不动就加租,逼得佃农没活路。三是朝廷税多,地方官又贪,啥灾啥乱都往农民头上压。朱家攒的那点钱,送孩子读书是想搏一把,可地主一闹腾,全打了水漂。晚清这社会,底层想翻身,比登天还难。 再说说鸦片。1892年仪陇种鸦片,朱家靠这个多赚了点铜钱,还真有点盼头。可这东西救不了命,地主照样加租,朝廷照样收税,鸦片赚的那点钱,顶多是杯水车薪。朱家送孩子读书的梦没做多久,就被现实砸得粉碎。晚清种鸦片的多,但底层农民还是穷,钱都流到地主和官儿兜里了。 朱家借债赎田,是想着守住祖业翻身。可田地荒了,收成差,债越欠越多。晚清时候,田不是救命稻草,是催命符。地主丁邱川加租不讲理,债主催债更不留情,朱家这点田根本撑不起翻身的希望。赎回来没多久,又丢了,等于白忙活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