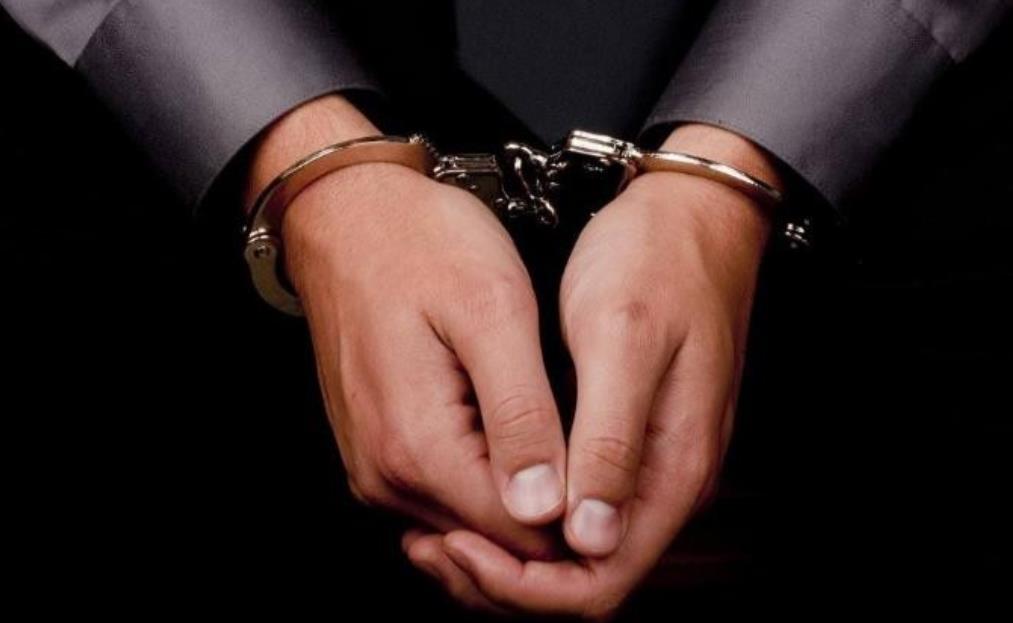河北,某派出所民警在调查一起蚶子盗窃案时,因急于破案,深夜对四名渔民拳打脚踢、强制“脚尖蹲地”体罚,致一人腹部重伤送医。然而,法院最终以“涉案人员非刑事犯罪嫌疑人”为由,判决民警无罪!原来,案件最初被定性为行政违法,民警施暴时尚未进入刑事侦查阶段。尽管渔民遍体鳞伤、医院诊断铁证如山,但因《刑法》规定“刑讯逼供仅限刑案嫌疑人”,暴力行为竟成“合法漏洞”。一纸判决引发哗然: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如何平衡?执法者的暴力红线究竟该划在何处? (案例来源:裁判文书网) 2013年12月,某派出所民警郭某(化名)在调查一起蚶子盗窃案时,因急于获取口供,对四名涉案渔民(刘某、潘某、岑某、黄某,均为化名)采取暴力手段。 据多名证人陈述,郭某在派出所食堂及走廊内对刘某拳击胸部、强制其"脚尖蹲地";对岑某踢打腰部臀部;对黄某脚踹腹部致其送医。 经医院诊断,黄某存在头外伤、多处软组织挫伤等症状。 案件最初由边防派出所以行政案件受理,次日移交海警支队转为刑事案件立案,但四名涉案人员最终未被定罪。 案件争议焦点有三个:一是,郭某的殴打行为是否发生在刑事侦查阶段? 二是,涉案人员是否属于《刑法》第247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 三是,行政案件调查中的暴力取证是否构成刑讯逼供罪? 检察机关认为,郭某作为司法工作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对嫌疑人使用暴力逼取口供,构成刑讯逼供罪。 但民警郭某及其辩护人则不认罪,提出如下抗辩: 其一,郭某的殴打行为发生于行政案件初查阶段,涉案人员仅为"违法嫌疑人"而非"犯罪嫌疑人"; 其二,案件移交海警支队后方转为刑事案件,但四名当事人始终未被刑事立案或采取强制措施; 其三,涉案人员不符合刑讯逼供罪的对象要件。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1、郭某的殴打行为是否发生在刑事侦查阶段? 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公安机关办案程序,刑事侦查阶段的启动以刑事立案为标志。 本案中,派出所于2013年12月2日接警后,所长刘某(化名)签署的《受案登记表》明确将该案定性为“行政案件”,并指派民警进行初查。 直至次日(12月3日),案件才移交海警支队并刑事立案。郭某的殴打行为集中于12月2日晚至次日凌晨,即在行政调查阶段实施。 公安机关对报案线索的初步审查,以判断是否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此阶段调查对象为“违法嫌疑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 立案后针对“犯罪嫌疑人”的调查,适用《刑事诉讼法》。 本案中,郭某的暴力行为发生在行政初查阶段,其目的是获取盗窃线索的口供,而非刑事立案后的取证。因此,其行为时间节点不符合刑讯逼供罪要求的“刑事侦查阶段”。 2、涉案人员是否属于《刑法》第247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 《刑法》第247条明确刑讯逼供罪的对象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2条,“犯罪嫌疑人”的法定身份始于刑事立案,且需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如拘留、逮捕)。 本案中,四名渔民(刘某1等)在派出所接受询问时,案件尚属行政调查,其身份为“行政违法嫌疑人”。 海警支队于12月3日刑事立案后,四人虽被带至海警审查,但无证据显示其被正式列为“犯罪嫌疑人”或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如刑事拘留通知书)。 本案中,四人在海警支队接受调查期间未被刑事拘留或逮捕,最终亦未被起诉,其身份始终未转化为“犯罪嫌疑人”。 综上,四人在被殴打时仅为行政违法嫌疑人,不符合刑讯逼供罪的对象要件。 3、行政案件中的暴力取证是否构成刑讯逼供罪? 《刑法》第247条将“刑讯逼供”限定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立法目的在于规范刑事司法权滥用。 行政调查中的取证行为受《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9条约束,暴力取证可能构成“滥用职权”或“故意伤害”,但不满足刑讯逼供罪的构成要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强调,刑讯逼供罪的成立需严格限定于刑事程序内。 本案中,郭某的暴力行为发生于行政初查阶段,其目的虽为获取口供,但因对象身份及案件性质不符,无法适用《刑法》第247条。 最终,法院以法律条款适用问题认定郭某不构成刑事犯罪,判决郭某无罪。 本案争议焦点的实质在于法律形式要件与实质正义的冲突。法院的判决严格遵循了刑法的明文规定,但亦揭示出行政执法程序中对暴力取证的规制不足。未来立法或可通过增设“行政暴力取证罪”填补空白,同时强化对执法行为的全程监督,以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统一。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