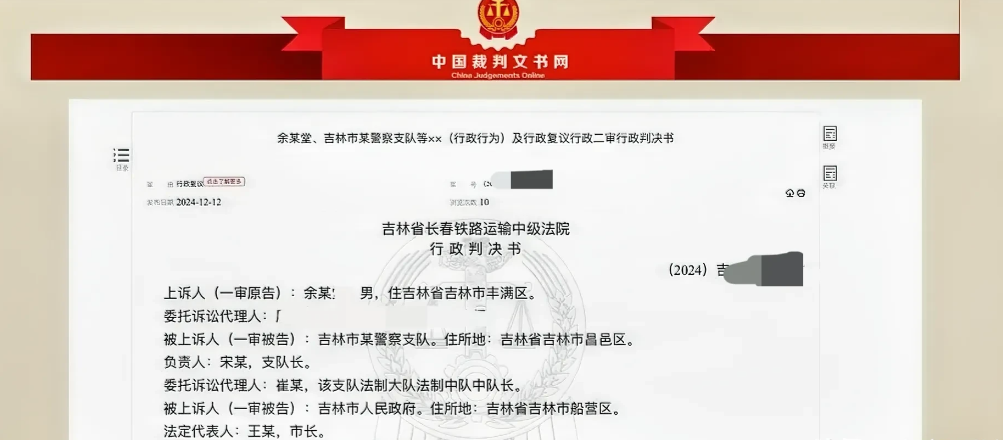吉林长春,男子凌晨驾车送86岁突发疾病的岳父去医院时,被确认血液酒精含量为21mg/100ml。交警确认情况属实后为男子找了代驾。但因男子属于再次酒驾的情形,交警对其处2千罚款、吊销驾照的行政处罚。男子不服并以岳父入院11天后就死亡,足以证明情况紧迫,其属于紧急避险为由,告上法庭。但法院这样判!
(来源:吉林长春铁路运输中院)
男子余某平时与妻子、86岁岳父王老伯共同生活。2024年2月26日,王老伯因咳嗽等身体疾病,曾住院接受治疗。
同年4月17日晚上,余某与朋友聚餐吃饭喝了一点酒。晚上23时40分,余某被妻子叫醒称,岳父有咳嗽、发热、呼吸困难等情况,而且不见好转,必须送医治疗。
余某想着自己喝酒已经过了那么长时间,应该不属于酒驾,于是就自己驾车与妻子一起送岳父到医院接受治疗。
可次日凌晨,余某驾车前往医院的路上却遇到在路上执勤的交警查酒驾。经酒精检测,持有B2驾驶证的余某血液酒精含量为21mg/100ml,属于饮酒驾驶机动车的。
因当时情况过于紧急,余某想都没想就签名确认并和交警说明实际情况。交警确认余某所言属实后,为其联系了代驾。
4月29日,余某的岳父经抢救无效去世。
5月4日,交警经查询后得知,余某曾于2018年因酒驾被处罚款18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行政处罚。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第1款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2千元罚款;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2千元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据此,因余某系属于再次酒驾的情形,故交警于5月20日,决定对其处2千元罚款、吊销驾照的行政处罚。
事后余某不服,并以系紧急避险为由,提起行攻复议。无果后,余某又告上法庭。
一审认为:
首先,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2款明确规定,饮酒后不得驾驶机动车。
余某堂曾于2018年因酒驾被交警行政处罚,其此次属于再次酒驾的情形,故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其次。酒驾对驾驶者本身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生命财产安全均构成较大的威胁,且事前无法确定。王老伯在出现咳嗽、发热、呼吸困难等情况后,余某对其实施救助的良好意愿值得肯定。
但余某应在理性判断能力范围内采取乘坐出租车或拨打120等方式救助,并非只能以危害公共安全为代价而选择酒驾施救。
最后,相较于不具备医疗专业知识的余某堂,120急救更大程度上能够为患者提供急救措施,但余某并未拨打120询问便径行采取酒驾方式将王老伯送医,其违法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紧急避险中“迫不得已”的条件。
即余某应当预见自身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危险性,其违法行为不构成紧急避险。
据此,一审驳回余某的诉求。
余某上诉时称:
第一,王老伯送医11天后就去世,由此可见,当时的情况有多紧急。
在危及老人生命的情况下,每一个人不可能作出完美的选择,更何况其当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挽救老人的性命。其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老人的生命免受危及生命的危险符合紧急避险的主客观条件。
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应当强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二)涉及抢险救灾、英烈保护、见义勇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助人为乐等,可能引发社会道德评价的案件。
其行为充分发挥了友善的正能量,其友善积极行为应当获得正面的肯定,因此,在其酒精含量仅为21mg/100ml、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险性,与老人的生命相比,应当获得肯定,至少不应吊销其驾照。
第三,《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23条规定,在作出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或较大数额罚款时,应当告知违法嫌疑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交警队在作出处罚决定前,未举行听证。违反法定程序,故应予撤销。
二审认为:
1、余某在交警队制作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对其询问是否要求听证,表示不要求听证并签字捺印。故确认交警在执法程序以及认定事实方面,符合法律规定。
2、紧急避险是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使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损害较小的另一方的合法权益,以保护较大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具体到本案,王老伯出现咳嗽、发热、呼吸困难等症状是否存在现实性暂且不论,即便威胁其人身权的现实性确已成就,但以具备一般理性人的常理分析,仍然存在比酒驾更具合法性和时效性的救济方式。
但余某未提出有效证据证明事发当时已无从选择其他救济方式,即余某酒驾救助王老伯具备紧迫性。
3、在案证据已然证明,余某被查获后,更多的是与交警的纠缠与说明,而非关心王老伯的病情,且余某已是第二次实施酒驾违法行为被查获的,因此,足见余某实施本案案涉违法行为具有主观上的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