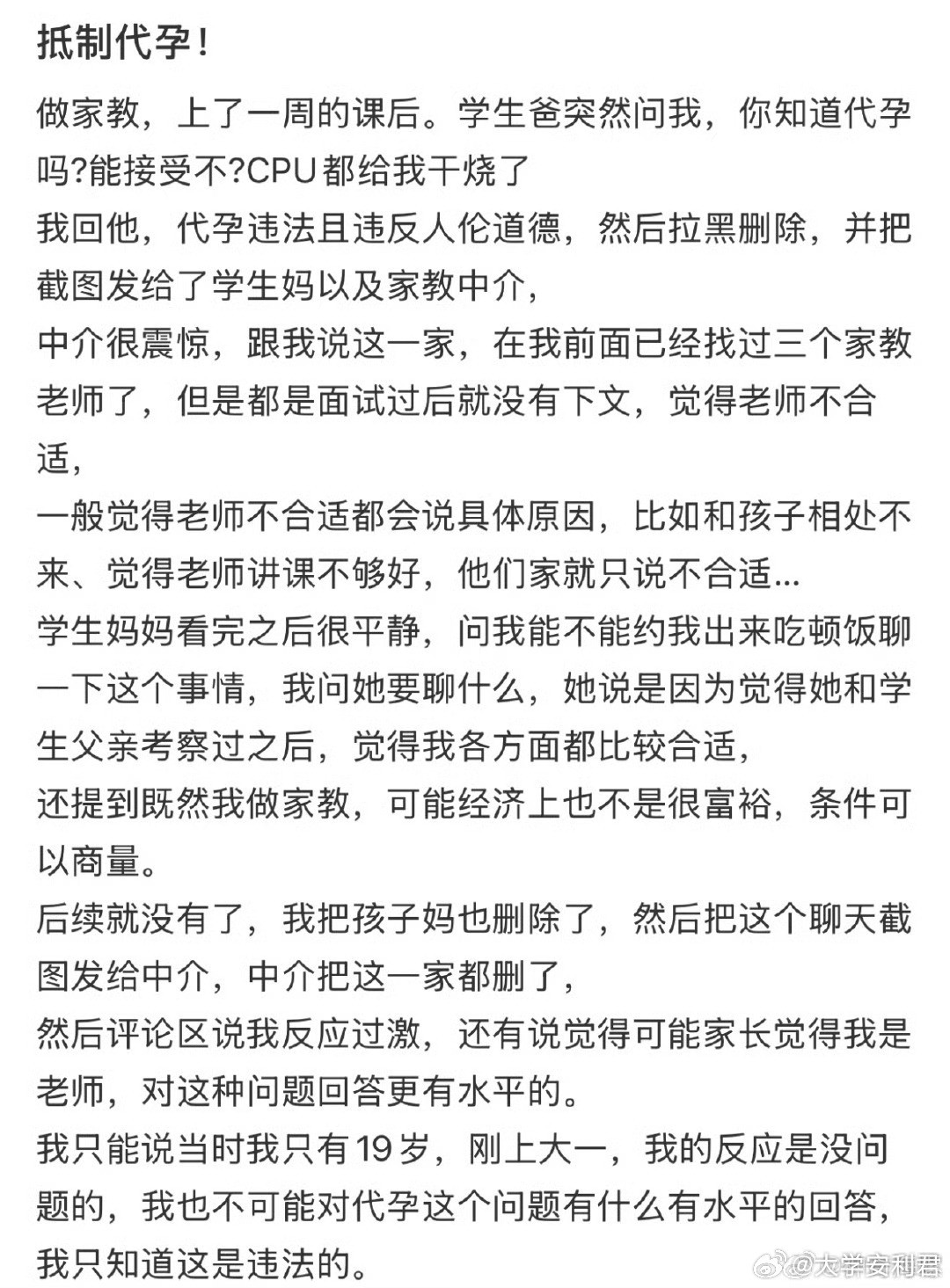陪娃写作业的第108天,我终于承认自己没那么坚强
夜里十点半,书房的台灯把我的影子钉在墙上,像张被揉皱又勉强展平的纸。儿子小宇趴在桌上,铅笔在数学练习册上戳出一个个墨点,
夜里十点半,书房的台灯把我的影子钉在墙上,像张被揉皱又勉强展平的纸。儿子小宇趴在桌上,铅笔在数学练习册上戳出一个个墨点,他的睫毛垂着,像两排打蔫的草。我盯着那道“鸡兔同笼”题,第三次讲解时,声音里的火苗还是没压住:“兔子有四条腿,鸡两条!你数清楚行不行?”
小宇肩膀一抖,铅笔“啪”地掉在地上。我猛地闭住嘴,看见他手背上的红印——那是刚才他自己掐的,说“这样就能记住了”。心像被什么东西攥住,疼得发闷。我弯腰捡铅笔,指尖触到冰凉的金属笔杆,突然想起白天在菜市场,卖菜阿姨说的那句:“你家娃真乖,放学就跟你回家写作业。”那时我还笑着应和,此刻才懂,这“乖”字背后,是两个灵魂在台灯下的互相消耗。
三个月前,我辞去做了十年的会计工作。老板找我谈时,我望着窗外写字楼的玻璃幕墙,说“孩子上三年级,得有人盯着”。话一出口,自己都愣了——当年那个在项目会上跟客户据理力争、熬夜做报表眼睛都不眨的人,怎么就成了“得盯着孩子”的妈妈?
最初的日子是新鲜的。我买了卡通闹钟,给小宇制定作息表,甚至在他的练习册封皮上画了只笑脸小熊。可现实很快露出獠牙。他背课文时盯着天花板发呆,写生字把“太”写成“大”,数学题算到一半突然问“宇宙外面是什么”。我从耐着性子教,到拍着桌子吼,最后坐在他对面掉眼泪。有天夜里,我听见他跟枕头里的奥特曼小声说:“妈妈是不是不喜欢我了?”我躲在门外,指甲掐进掌心,血腥味混着眼泪咽进肚子。
上周家长会,老师说小宇上课总走神,“好像有心事”。我攥着家长会通知单,上面的“请家长多关注孩子情绪”刺得眼睛疼。回家路上,看见小区里别的妈妈聚在一起聊瑜伽课和新出的口红,我插不上话——我的话题永远是“哪款橡皮擦得干净”“口算题卡哪家强”。路过便利店,鬼使神差买了罐啤酒,蹲在楼下喝。夜风把头发吹得乱七八糟,突然想起二十岁那年,我在大学图书馆里啃《税法》,阳光落在摊开的书上,那时的未来里,没有“陪孩子写作业”这一项。
今晚这道鸡兔同笼,小宇终于算对了。他抬头冲我笑,门牙缺了颗,像只刚偷吃完米的小松鼠。我摸了摸他的头,他头发里还带着白天操场的汗味。等他睡熟,我坐在书桌前翻他的作文本。最新一篇写《我的妈妈》,开头是“我妈妈以前爱笑,现在总皱着眉头”。后面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女人,手里举着铅笔,旁边标着“妈妈的魔法棒”。
台灯的光晕里,我对着那幅画发呆。原来孩子什么都懂。他知道我吼他时声音在发抖,知道我偷偷擦掉他作业本上的红叉重改,知道我半夜爬起来给他削铅笔。那些被作业磨掉的耐心,被焦虑偷走的笑容,他都看在眼里,却还是把我的怒气,当成了“魔法”。
窗外的月亮移过云层,照亮书桌上的药盒——医生说我肝火太旺,开了疏肝的药。我拿起笔,在小宇的作文本上画了个笑脸,比他画的那个圆一点。明天早上,他应该会发现吧。
其实哪有什么“孽”。不过是当年那个盼着快点长大的姑娘,如今成了那个盼着孩子慢点长大的妈妈。那些在台灯下爆发的脾气,摔过的笔,掉过的眼泪,说到底,都是怕啊——怕自己不够好,怕给不了他周全,怕这操蛋的作业,磨掉了他眼里的光。
夜深得像片海,我轻轻合上他的作业本。明天还要陪他背英语单词,还要跟他一起跟那道该死的应用题死磕。但此刻,看着他均匀的呼吸,突然觉得,这“孽”,我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