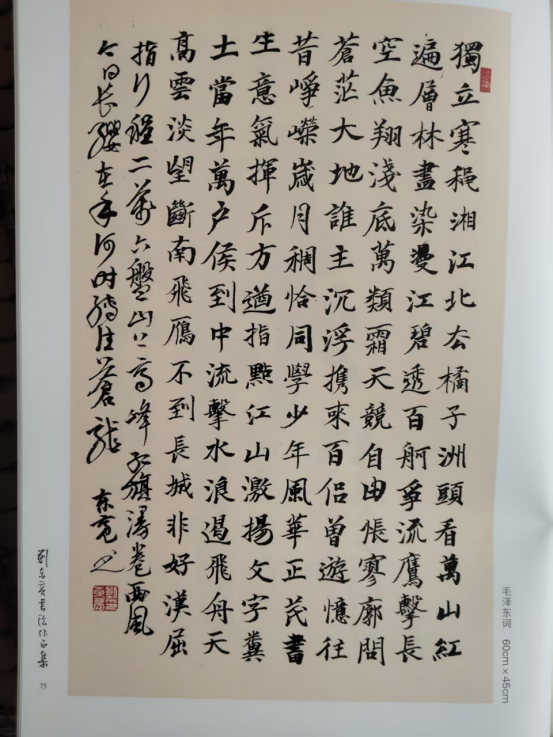在嵩山少林武术之乡的文化厚土上,刘东亮是一位以笔墨为舟、以自然为渡的书法行者。他生于 1948 年,以 “悟象斋” 为创

在嵩山少林武术之乡的文化厚土上,刘东亮是一位以笔墨为舟、以自然为渡的书法行者。他生于 1948 年,以 “悟象斋” 为创作栖居之所,身兼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嵩山草书研究社社长等数职,数十年深耕书法艺术,从唐楷的法度森严到草书的奔逸跌宕,从临帖的潜心研磨到创作的独树一帜,终成 “全国德艺双馨艺术家”。他的书法,不仅是笔墨技巧的极致展现,更是以 “悟象” 为钥,解锁自然与艺术深层联结的生动实践 —— 山间的流云、少林的拳势、石上的苔痕,皆在他的笔端化为线条的律动,让每一幅作品都成为书法与自然对话的鲜活注脚。
少年戏墨:自然启蒙里的艺术萌芽
刘东亮与书画的缘分,早在童年时便与自然悄然绑定。他出生于书香门第,舅舅的笔墨熏陶为他埋下艺术的种子,而真正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的,是一场雨后庭院里的 “墨戏”。彼时年幼的他,见父亲将墨汁倒入雨后积水的坑洼中,墨色随水纹扩散,或如远山含黛,或如流云舒卷,或如乱石铺阶,白纸轻覆其上,便印出满纸天然意趣。这偶然的场景,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童年,让他对 “墨与自然” 的结合产生了最初的好奇,此后常以树枝为笔、地面为纸,模仿着水坑里的墨痕 “乱画”,这份纯粹的热爱,成了他艺术之路的起点。
稍长后,刘东亮随父亲在新密就读小学,虽曾因贪玩逃学捕鱼,却始终没放下对 “画” 的执念。一次,他的舅爷让他画 “小鬼火判子”即钟馗,画绘好后挂在家里。看到自己的作品被珍视,他的心中涌起的不仅是喜悦,更是对 “笔墨能承载民俗意涵、留住生活与自然温度” 的朦胧认知,这份来自长辈的认可,也让他对书画的热爱多了一份笃定。

上初中后,他遇到了影响其书法生涯的第一位 “引路人”—— 校长王田园。这位在教育领域深耕多年的学者,不仅有着儒雅的风范与出众的书法造诣,更将 “高度重视下一代培养” 的理念融入日常教学的点滴之中。他偶然发现刘东亮常在课本边角勾勒花鸟、临摹字迹,便主动走近这个爱 “涂画” 的少年,不仅亲手为他标注欧阳询《九成宫》、柳公权《玄秘塔碑》的间架结构,还把重点笔画标注出来作为学习重点,更叮嘱他 “学书先学古,不能凭臆造,古人的笔墨里藏着自然的道理”。王田园校长常以自然为喻讲解书法:“横如千里阵云铺展,点如高峰坠石有力,撇如利剑斩风迅疾”,正是这些生动的比喻,让刘东亮第一次清晰意识到,汉字的每一笔画都与自然形态紧密相连,这份启蒙如同一把钥匙,为他日后 “以自然悟书法” 的艺术之路埋下了关键伏笔。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刘东亮的学业被迫中断,但他与笔墨的联结从未断裂。他也卷入了当时全国性的革命洪流之中,参与到写传单、贴大标语、办报刊专栏的宣传工作里。彼时,街头的墙面、单位的宣传栏成了他的 “大纸”,石灰水当墨,捆扎的扫帚为笔,“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等豪迈标语,在反复书写中不仅锤炼了他的笔力,更让他在毛泽东草书的奔放气势里,感受到 “笔墨可承载时代气魄与自然意象” 的力量。后来,他被派往基层参与劳动,因 “体力相对较弱”,很快被调至宣传组,负责写工地海报、画工地板报,山间的风、铁轨的直线、工友们挥汗时的动态,都成了他笔下的鲜活素材。下乡的几年他对书法学习没有间断,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让他懂得:自然从不是远在天边的风景,而是融入日常的点滴,哪怕是工地的一砖一瓦、风中摇曳的一草一木,都能成为笔墨创作的灵感来源。
临帖问道:传统笔墨中的自然密码
在刘东亮的书法生涯里,“临帖” 从来不是简单的 “模仿复刻”,而是在与古人笔墨对话的过程中,探寻藏在传统技法里的 “自然密码”。初中时,在王田园校长的悉心指导下,他开始系统临习唐楷,每天放学后都会对着《玄秘塔碑》揣摩许久 —— 柳公权笔下 “竖如万岁枯藤” 的遒劲,欧阳询 “险如孤峰之坠” 的结构,都让他深深着迷。他常常对着字帖观察半天,再走到庭院里,将笔画与自然景物对照:看院中的老藤,便想起柳体竖画的苍劲;望远处的山峰,便理解欧体结构的险峻。他渐渐发现,古人的笔法从不是凭空创造,每一笔都暗含着对自然形态的观察与提炼,这份 “以自然解帖” 的认知,让他的临帖之路多了一份自觉与通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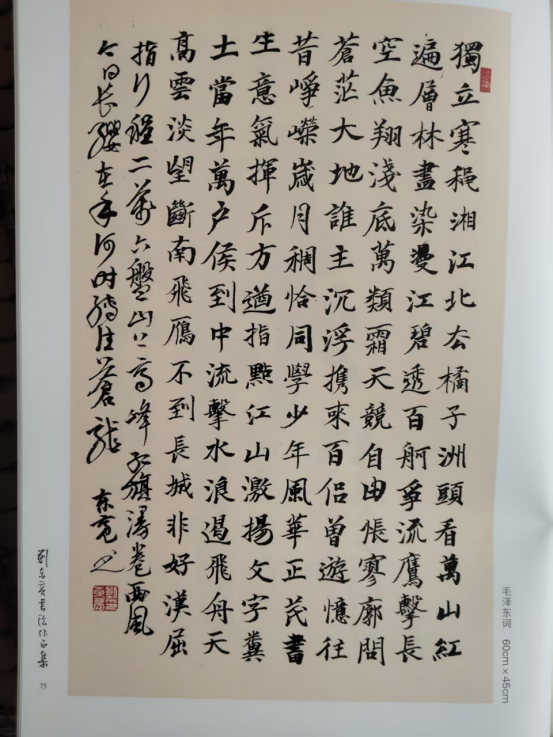
20 岁那年,他从一位同学手中借到一本《王羲之草诀歌》,翻开书页的瞬间,便被书中潇洒飞动的线条吸引,仿佛找到了 “失散多年的知己”。那些连绵的笔画,或如村边颍水蜿蜒流淌,或如草丛惊蛇灵活穿梭,让他对草书产生了难以言喻的热爱。为了练好草书,他把字帖贴身携带,走路时在心里 “空临” 笔画走势,吃饭时琢磨线条的转折衔接,甚至与人交谈时,目光也会不自觉追随窗外的树影,将枝叶的交错缠绕想象成草书的章法布局。后来,他又接触到张旭《古诗四帖》、怀素《自序帖》,更是日日心追神契 —— 张旭笔下 “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怀素 “骤雨旋风” 般的笔势,都让他深刻体会到:真正的草书,是将自然的动态与气势,完美融入笔墨的干湿浓淡、疾徐顿挫之中。
30 岁时,刘东亮遇到了书法生涯中的第二位 “贵人”—— 书法大家李刚田。彼时,他的行书已小有所成,常被身边人称赞,李刚田却在看过他的作品后点拨:“你的行书底子不错,但要想在草书上有所突破,可从明清大家的作品入手,汲取他们对笔墨气势的把控。” 这句指点,让他的临帖之路有了新的方向。他先后找来傅山、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的法帖细细揣摩,最终将目光锁定在王铎的草书上。王铎草书在 “二王” 与米芾基础上的创新,点画如 “老藤缠树” 般苍劲,结体如 “危石欲坠” 般险峻,那份 “恣肆开张” 的气势里,藏着对自然生命力的极致表达。为了吃透王铎的笔法,他把王铎的法帖拓片铺满案头,反复观察线条的粗细变化:浓墨处如嵩山乌云聚顶,枯笔处如崖壁老树虬枝,转折处如山涧溪流迂回,出锋处如高空鹰隼击空。他常常临帖到深夜,再起身走到窗边,看月光下的嵩山轮廓,将山的气势与笔的走势相互印证,渐渐悟出:王铎的草书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他把自然的 “势” 与 “态”,全然融入了笔墨的节奏与气韵里。

在临帖的漫长岁月里,刘东亮始终保持着 “以自然观帖” 的习惯。他常把历代名帖与嵩山的风景对应:临《张猛龙碑》,便想起嵩山的危峰峭壁,笔端多了几分刚劲;写《集王圣教序》,便念及颍水的潺潺流动,线条添了几分流畅;摹《祭侄文稿》,便联想到山间雷雨前的压抑氛围,墨色也随之沉郁。哪怕外出,他也总会随身携带字帖,一次去南方度假,他带着《集王圣教序》来到海边,看浪涛拍岸的起伏节奏,竟与字帖中行草的连绵气韵不谋而合。他曾在笔记中写道:“古人作书,以自然为师;今人学书,当以古人之帖为桥,再回到自然中寻根。” 正是这份对 “自然与传统” 的深刻理解,让他的临帖之路走得扎实而坚定,为日后的创作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嵩山悟象:天地之中的笔墨回响
1981 年,为了照顾家中年迈的爷爷奶奶,刘东亮主动申请从新密调回登封,回到了这片生他养他的嵩山脚下。站在熟悉的嵩山之巅,看云雾在山间流转聚散,听少林武校的孩子们喊着整齐的号子练拳,他忽然豁然开朗 —— 自己多年来追寻的 “书法与自然” 的深层联结,就在这片土地的一呼一吸里。也是从这时起,他把自己的创作室取名为 “悟象斋”,“悟” 的是嵩山的自然之象,“写” 的是心中的天地之境,他的书法创作,正式迈入 “以自然为师、以嵩山为魂” 的新阶段。

嵩山的少林武术,是刘东亮 “悟象” 之路上的重要灵感源泉。他常抽空坐在少林武校的操场边,静静观察孩子们练拳:“动如涛” 的连绵节奏,“快如风” 的迅疾姿态,“起如猿” 的灵活轻盈,“重如山” 的沉稳力道,少林拳术中 “意、气、力” 的相互配合,与书法创作中 “笔、墨、势” 的协调统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发现,少林拳 “拳打一条线,拳打一口气” 的要诀,恰好能解读书法的章法布局 —— 一幅好的行草书,也应如一套完整的拳法,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即便笔锋断开,内在的气韵也需连贯不绝。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孩子练习 “旋风腿”,身体旋转时的流畅与踢腿时的洒脱,让他突然悟到草书的 “缠绕与出锋”:旋转的姿态如笔锋的迂回缠绕,踢腿的劲道如线条的果断出锋,那份 “刚柔相济” 的力道,正是草书创作中需要的气韵。回到工作室后,他当即铺纸挥毫,将少林拳的 “势” 融入笔端,写出的草书线条如 “铁画银钩”,既有拳术的刚劲,又有自然的灵动,连他自己都忍不住感叹:“嵩山的一草一木、一拳一脚,都是我最好的书法老师。”
除了少林武术,嵩山的四季景致,更是他笔墨创作的 “直接素材库”。春日里,他会特意去山间看野花在石缝中绽放,那些不拘一格的生长姿态,让他在书法中大胆加入 “欹斜奇崛” 的结体;夏日的午后,他常坐在颍水岸边,听流水在山谷中奔涌向前,这份连绵不绝的动态,被他转化为笔下 “一气呵成” 的线条;秋日来临,他喜欢看落叶在风中盘旋飞舞,便在章法布局中设计 “疏密错落” 的排布,模拟落叶的自然之态;冬日的清晨,他会登上嵩山,观察寒松在崖壁上挺立的模样,那份坚韧不拔的风骨,成了他笔端 “遒劲苍老” 的笔力来源。他甚至会特意在雨后登山,看雨水在岩石上留下的痕迹 —— 或深或浅、或直或曲的水痕,都成了他墨法创作的参考:浓墨如积水深潭,淡墨如薄雾轻烟,涨墨如雨水漫过石面,枯笔如干旱龟裂的土地。有一次,他在中岳庙看到一棵千年古柏,树干扭曲如盘龙,枝桠如剑戟横空,那份历经岁月沉淀的苍劲与生机,让他久久驻足。回到家后,他反复琢磨这棵古柏的形态,最终创作出一幅草书作品,线条如古柏的枝干般盘迂回绕却不失劲道,结体如柏的根基般沉稳厚重又暗藏生机,这幅作品后来在全国书法展中获奖,评委在评语中写道:“墨中有嵩山之骨,笔端有古松之风。”

在 “悟象” 创作的过程中,刘东亮还总结出自己独有的创作心得:“开初无定式,辍笔才见结果。” 他认为,书法创作不应被预设的模式束缚,而应如自然万物的生长 —— 春天不会预设每一朵花的形状,河流不会预设每一段的流向,书法创作也应在书写过程中,随着情感的起伏与自然的启发 “随机生发”。他创作时,从不像旁人那样先打草稿,而是先静坐片刻,或回忆嵩山的某一处风景,或聆听窗外的风声鸟鸣,待心中有了清晰的 “自然之象”,便提笔挥毫:笔锋的疾徐,如风吹树叶时的动静变化;墨色的浓淡,如山间云雾的聚散流转;字形的大小,如岩石的高低错落排布。有一次,他在工作室创作时,窗外突然下起了暴雨,雷声轰鸣,雨水砸在窗棂上噼啪作响,原本计划写一幅平和的诗句,却被这突如其来的自然景象触动,顺势加快了笔速,墨色也愈发浓重。最终完成的作品,笔锋间的 “顿挫” 如雷声的短暂停顿,线条的 “飞白” 如雨水的飞溅姿态,成了一幅气势磅礴的草书佳作。后来,一位收藏家看到这幅作品,当即决定收藏,他说:“从这幅字里,我仿佛看到了嵩山暴雨倾泻时的壮观景象,这是笔墨与自然最真实的对话。”
融古创新:笔墨当随时代的自然表达
在刘东亮看来,“悟象” 并非对自然的简单复制,而是在继承传统笔墨的基础上,以时代的语言,表达对自然的当代理解。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李可染先生说‘用最大功力打进去,用最大勇气打出来’,‘打进去’是学古人、学自然,把根基扎稳;‘打出来’是跳出模仿,创作出属于自己的风格。” 多年来,他在临习历代书法大家作品的同时,始终在探索 “如何让传统笔墨与当代自然观相结合”,最终形成了 “奔逸跌宕、奇崛老辣” 的独特书风。

在草书创作上,刘东亮博采众长却不囿于一家。他从黄道周的作品中汲取 “跌宕” 之气,融入嵩山起伏的山势;从倪元璐的笔墨里借鉴 “峻峭” 之姿,对应悬崖壁立千仞的形态;将张瑞图的 “奇崛” 之感化为笔下如怪石横生的结体;把王铎的 “奔放” 之势比作大河奔涌的线条;再兼学傅山的 “盘桓” 之韵,如古藤缠绕的灵动。但他从不是简单地生搬硬套,而是将这些大家的笔法 “打碎重组”,以自己对嵩山自然的理解为 “黏合剂”,形成全新的艺术表达。比如他写 “山” 字,会借鉴王铎草书的 “恣肆”,但竖画的收尾处,会融入少林拳 “重如山” 的力道,让整个字既有传统草书的韵味,又带着嵩山的厚重感;写 “水” 字时,会参考怀素的 “流畅” 笔意,但笔画的迂回处,会加入颍水 “绕山而行” 的灵动,让线条在遵循古法的同时,多了几分当代的生动气息。
文化大革命进入后期,全国开始转向 “抓革命促生产”,毛泽东提出 “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 的号召,焦枝铁路的修建工程也随之启动,成为当时 “促生产” 的重要项目之一。彼时正处于上山下乡阶段的刘东亮,以知青代表的身份参与到这场浩大的铁路建设中。他因书画特长,很快被抽调至工地宣传组,负责书写大型宣传标语与制作宣传栏。这项工作远比想象中艰难:路基高达一两丈,要在上面书写一丈见方的大字,需与老主任姚伟默契配合 —— 两人先抬着长棍在路基上拉好线条定位,再用绑着棉布的长杆蘸取颜料,踩着脚手架小心书写;为了让字迹更持久醒目,部分标语写完后,还会用染色的石头沿着笔画轮廓堆砌,增强视觉效果。如今,焦枝铁路沿线仍有部分当年的字迹留存,成为那段特殊岁月的实物印记。这段经历不仅让他在大字书写中练就了把控整体气势的能力,更让他深刻理解了 “笔墨服务于时代、融入于生活” 的意义。
为了让 “自然之象” 的表达更加丰富多元,刘东亮在笔墨技巧上不断探索创新。他尝试用 “泼墨” 技法表现山间的云雾,让墨色在宣纸上自然晕染,如云雾在山谷中缓缓流动;用 “破锋” 笔法描绘岩石的纹理,故意将笔锋散开,让线条呈现出石面裂纹般的粗糙质感;用 “涨墨” 表现雨后的土地,让饱和的墨色在纸上微微晕开,模拟雨水浸润泥土的湿润感;用 “飞白” 展现风中的枯草,让干涩的笔锋拉出断续的线条,如草叶在风中摇曳的枯槁之态。这些技巧的运用,从不是为了 “炫技”,而是为了让笔墨更精准地 “对话自然”。有一次,他为登封一家少林武校题写 “武韵嵩山” 的匾额,“武” 字用 “破锋” 笔法,笔画如拳脚出击般凌厉;“韵” 字用 “涨墨”,墨色如山间云雾般温润;“嵩” 字的竖画如嵩山主峰般挺拔,“山” 字的撇捺如山坡般平缓舒展。这幅匾额挂在武校门口,既体现了少林武术的刚劲,又展现了嵩山的自然之美,成了当地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

除了专注创作,刘东亮还始终践行 “让书法回归生活、回归自然” 的理念,积极投身各类公益文化实践。他深度参与大禹文化之乡的建设工作,曾义务为祖家庄、五里庙等地书写两种碑刻 —— 将大禹治水的历史故事与嵩山的自然风貌融入碑文内容,用遒劲的笔墨赋予碑刻文化温度,全程自愿免费,分文不取。他常说:“书法是从生活里来的,也该回到生活里去。” 他多次走进登封的中小学,带着孩子们在校园的空地上,用树枝当笔、泥土当纸,教他们写 “横如小树苗,竖如电线杆”,让孩子们在游戏中感受书法与自然的紧密联系;每逢春节前,他都会参与 “文化下乡” 活动,带着笔墨纸砚来到田间地头,为农民朋友们书写春联,把 “五谷丰登” 的美好期盼与 “麦浪滚滚” 的自然意象融入笔端,让书法成为传递温暖的载体;他还曾在嵩山脚下举办 “书法与自然” 公益展览,将自己的书法作品与嵩山四季风光的摄影作品并置展出,让观众直观看到 “笔墨如何再现自然之美”,感受书法艺术与自然山水的深层共鸣。

鲜少有人知晓,刘东亮的艺术生涯其实始于绘画,而非书法。童年时的他,便对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常跟着身边擅长画画的长辈模仿创作,曾完成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绘画作品。成年后,尽管书法创作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但对绘画的热爱从未消减,尤其在花鸟画领域颇有造诣,梅兰竹菊是他最常描绘的题材 —— 他笔下的梅花,枝干苍劲,花瓣疏朗,透着傲骨之气;兰草则叶片修长,姿态清雅,尽显君子之风;竹子更是他的 “拿手好戏”,从青年时期开始,断断续续已画了三四十年,竹竿的挺拔、竹叶的疏密,都被他刻画得惟妙惟肖,当地不少人都知晓他 “善画竹” 的名声。他常说:“绘画与书法是相通的,画竹时对枝叶布局、竹竿劲挺的理解,能反过来滋养书法的章法与笔力;而书法对线条的精准把控,也让我在画花鸟时更能捕捉自然的灵动。” 这种 “书画互养” 的艺术状态,让他的笔墨表达更具层次感,也让他对书法 “自然之象” 的捕捉愈发敏锐。
2004 年,刘东亮凭借深厚的书法造诣,正式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这份认可的背后,是他多年来在全国书法赛事中的优异成绩 —— 在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书法展中,他先后斩获两次优秀奖、一次三等奖,另有一次入展经历,远超协会会员申报所需的 “一次获奖 + 一次入展” 标准。他家中珍藏的获奖证书、入展作品证书等荣誉材料,摞起来可达一米高,足足有两摞之多,每一份荣誉的背后,都是他对 “悟象” 之道的执着坚守。如今已年过七旬的刘东亮,依然保持着 “每日练字、时常登山” 的习惯:清晨登上嵩山,看朝阳染红山峰,听林间鸟鸣清脆;上午回到 “悟象斋”,铺纸研墨,将清晨所见的自然之象化为笔下线条;午后则会拿起画笔,勾勒几竿翠竹、几朵梅花,在书画互养中感受艺术的温度。

()从童年雨后的 “水坑戏墨”,到如今笔下的 “嵩山气象”,刘东亮的 “悟象” 之道,本质上是一条 “以自然为根、以传统为魂、以时代为脉” 的艺术之路。他用数十年的实践证明:真正的书法艺术,从不是闭门造车的技巧堆砌,而是对自然的敬畏、对传统的传承、对生活的热爱。而他笔下的每一幅作品,都是他与自然对话的生动见证,也是嵩山文化厚土上,一颗艺术初心始终鲜活的温暖绽放。(闫洧涛)